歌德晚年写下的一部自传题名为《诗与真》。歌德也不相信绝对真实的存在,即使那是为自己作传。但他却希望以饱满的诗情为舟楫摆渡到真实的彼岸,这可能吗?有人说,诗情只能离去真实更远;但也有人说,诗情达成的是一种更高的真实。
这个问题现在又摆放在青青为女作家萧红写下的传记《落红记》面前。这部30多万字的《落红记》,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它清新流畅,晶莹剔透,写的是民国旧事,又流露出作者的心向与才情。它因史实而丰蕴,因才情而灵动。据说关于萧红的传记如今已经出版了近70部,作传者不乏鸿儒大家,但青青的这部萧红传的面世,仍然让人眼前一亮。
传主与传者
文坛上曾提倡过所谓“零度写作”,要求作家在写作过程中保持思想与情感的中立,不带任何主观上的爱憎去书写对象。对于传记写作,这或许可以作为一个自成一说的尺度。因为传主端的是一个客观存在过的事实,如果真的能够“照本写真”下来,倒不失其文史价值。
青青写《落红记》不是这样,她不但没有“零度”写萧红的念头,反而恨不得以百度的高温与自己的传主贴在一起,融为一体。她说她与萧红的命运里都拥有一条河,自己童年的老家也有一座后园、一位老人,甚至自己还曾经暗恋过一位祖籍呼兰河、目如秋水的男子。为了写好萧红的这部传记,青青积数年之功勘察了凡是萧红驻留过的地方,她甚至还相信自己得到萧红的幽灵在冥冥中的护佑。写作常常陷入“我与萧红”亦真亦幻的境界。在众多的萧红传里,这样的写法应是无多,《落红记》于是显得自成一格。我读《落红记》就有些恍惚,有时觉得那是一位当代女记者在诉说一位民国年间老祖母的故事;更多的时候则像是一位宽容厚道的成熟女性在关爱体贴一位任性而又命运多舛的姊妹。在我读过的传记文学中,梁实秋写苏东坡多少与此相似,是将东坡引为知己同道的,仿佛写的就是自己身边亲近无比的师友,但也不如青青如此这般生死不渝的投入。这样的好处是情真意切、感同身受、文字灵动、布局活泛,给读者以更多的美的享受,这也正是《落红记》获得许多读者青睐的重要原因。但同时也就带来另一面,由于过多地倚重个人情绪的舒展与流转,对于历史纵深处的观照、对于人性纵深处的探究就显得用力不足了。还由于对萧红深深的挚爱,传者的手术刀也就不忍心往纵深处下手。就我自己的阅读情性而言,我欣赏青青的写法;若是从一个批评家的角度来看,这种写法又有着它的不足。
史实与诗情
确切地说,《落红记》是一部“传记文学”,横跨在“史实”与“诗情”之间。传记,最应该写出的是历史的真实还是文学的情愫,一直是存有争议的。有论者指出:《落红记》虽然从头至尾贯穿了作者强烈的情感及人生体验,甚至成了这本传记的主线,却并没有影响到“历史的真实”,原因在于有扎实的资料与详实的论据做支撑。这话若是说给正统的历史学家听,那注定是要碰钉子的。
如中国“新史学”的鼻祖梁启超及其后继者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钱基博一代学人,坚执史学的命根子就是史料的客观性、真实性、科学性。
时过不久,“新史学”便又遭遇到“新新史学”的扬弃。在欧美新崛起的一些史学家看来,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当然是曾经“客观”存在过的,但已无法重演,已经成了后来人的“知识性对象”与“话语主题”。于是历史的书写不能不是对这些“知识话语”的再度“建构”,这自始至终都不过是一个充满诸多想象与描述的修辞过程。美国当代史学家海登·怀特就曾强调指出:历史学注定蕴含着文学性,历史书写避不开诗
化的诱惑(前提是不要把文学书写当做胡编乱造)。对于这样一部传记文学来说,史料当然是重要的,但诗情更是必不可少,正是诗情使那些史料洋溢着生机与活力。
性爱与文学
两性之爱,在萧红的生活中无疑占据了显著地位。在她31岁的漂泊生涯中,不止与6位男性陷入情天恨海。对于萧红繁复而跌宕的两性关系,不乏有人站在道德高地上责骂她。青青则相反,她在《落红记》中对萧红在婚姻爱情中遭遇的不幸百般回护、万般同情。
但青青的辩护有时又显得如此苍白,比如她在访谈中说:萧红一生都在追寻爱与温暖,她不是追寻男人,她寻找的是灵魂的知己,是亲人般的宠爱与温暖。这实际上是女作家对于进一步谈论两性关系的回避,甚至是落逃。
青青另一解说是“所嫁非人”:命运待她不公,她遇到的男性,都不能算是“对”的人。那么对的人又在哪里?后来的史料说明,未婚夫汪恩甲也并非负心之人;第二任丈夫端木有些懦弱也仍旧是一个的好人;萧军毛病的确很多,但萧红临终前最信赖的还是他。
在爱的历程里,女性的困惑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
从今天的现实看来,两性关系中的政治性、经济性、技术性、计算性因素渐渐占据主导地位。于是,原本“最自然的关系”已经变成“最不自然”、“最难处置”的关系。真正的文学家,无一例外都是一些守护自己本真的人。民国年间,由郁达夫、沈从文、徐志摩、凌淑华、郭沫若、胡兰成、张爱玲、徐悲鸿、乃至鲁迅这些文学艺术家流传下的“绯闻”大抵如此,应验了一句老话:文人无行。
对于文学艺术家的“无行”,弗洛伊德作出的解释是:第一,他们的力比多(生命力)旺盛;第二,他们的道德伦理观念薄弱;第三,他们有足够的将性欲升华为诗歌与艺术的能力。
文学艺术家的职业,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就是“白日做梦”。更有甚者,总是错把白日当夜晚,错把梦幻当现实,追梦一生。
青青笔下的萧红,就是这样一个一生追梦的人。
这样的萧红,方才是一位自然天真、任情率性的文学家。
萧红是在青春时期死去的,留下来的似乎是一个更为纯粹的人生。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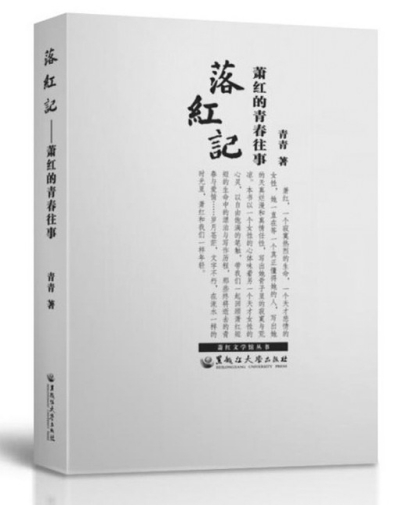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