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拟诸天象,是朝日方升未升、夕阳方下未下时的景象。这是天地间最壮丽的时刻。其原因正在于兼容与转换,不像正午和中夜,或者艳阳高照,或者皓月当空,美则美矣,缺少一点丰富与变化。不独天象,凡物皆然。像敦煌,因其边缘,遂成为汉文化与佛教文化相融合的璀璨结晶;像边区,因其远离中心,遂成为革命的发源地。至于各种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无不是新技术、新发明产生的渊薮。可以说,边缘产生灵感,边缘爆发革命。
在文学领域,也有一些处于边缘的人物。比如杨绛,就可谓是一位边缘人。她是小说家?翻译家?评论家?学者?都是,又都不是。对于杨绛来说,她既否认自己是一个小说家,也否认自己是一个学者。她一辈子最真切的感受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孟婆茶(胡思乱想,代序)》中,她写到:“一处是教师座,都满了,没我的位子;一处是作家座,也满了,没我的位子;一处是翻译者的座,标着英、法、德、日、西等国名,我找了几处,都没有我的位子。”最后,“他们在传送带的横侧放下一只凳子,请我坐下”。所谓“传送带的横侧”,即是边缘,坐在这一边缘的人,自然是边缘人了。因此,边缘人,是杨绛对自己一生的真确写照。
作为《杨绛,走在小说边上》的作者,慈江也堪称一位边缘人。其实“边缘人”一词,还是慈江当年初出茅庐、亮相文评诗评界时一个颇为自许的创见,后来却一语成谶,成了他自己一生的命运。他1997年出版的诗集《漂移的岸》是一个隐喻,因为“船一旦下水便注定一世漂泊”(《远行人》)。所以,无论是辞别故土求学异域,还是告别文学转战商海,抑或是在经济学与文学之间徘徊,其边缘的姿态和情绪随时光的流逝而日益彰显。边缘人,让人想起俄国文学中“多余的人”或“零余者”的形象,虽然被莱蒙托夫誉为“当代英雄”,但就其内涵,仍然具有一种漂泊不定和自我放逐的意味。
因此,同样的遭际和心境,在冥冥中便自然而然,产生了契合。我想,慈江之所以要选择杨绛作为研究对象,并积数年之功,撰写学界第一本杨绛研究专著《杨绛,走在小说边上》,正是他在杨绛那里,看见了自己的影像。然而,边缘意味着复杂、混沌、晦明不定。因此,走进杨绛的文学生涯,注定是一次历险,一次智识的较量和挣扎。因为,杨绛不但是学术大师钱锺书的夫人,而且作为留洋归国的才女,在创作、翻译、研究等方面的著述皆堪称可观。我想,提前20年,慈江不会去碰这个“硬钉子”,那只会将自己扎得满手是血。不过,已经人到中年的慈江,却也已远非昔日吴下阿蒙。他精通英文,修读过德、俄、拉丁等语言课程,编过《外国文学评论》,出过诗集和翻译作品,甚至出版过经济学著作。研究杨绛可以有很多视角,但是慈江却选择了从小说入手。小说,其实是杨绛文学生涯中一个薄弱环节,亦可称之为其文学活动的边缘地带,因为杨绛一向自认在小说创作上“只是一个业余作者”——这大概也正是慈江将著作命名为《杨绛,走在小说边上》的真意之所在。即使只是从创作而言,她的散文也胜于小说。她的散文如《干校六记》确已达到了“喜剧的外表,悲剧的内蕴”的高度。慈江认为,对于杨绛来说,“最难割舍是小说”。正因为小说是杨绛最倾心、最纠结,却又把握得最不好的领域,因而也就成了一窥其文学路径与文心的一个绝佳观察点。从杨绛与小说的纠结这里可以比较容易看见杨绛理论与创作的脉络、看见其才情与学识的发源,看见其文学活动的全部复杂性,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
我一直在想,作为和萧红同龄、大张爱玲九岁、小林徽因六岁的同代才女,杨绛的作品为什么总体上不如前三位的小说或诗歌那样更令人痴迷,那样更让人难以忘怀呢?除了政治环境之外,杨绛本人的文学观念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其小说的成就,因为她的文学观更多的是一种19世纪以前的古典主义文学观,有一种干净而清晰的理性特质——诚如慈江所言,总体而言是沿着“经典的清晰的脚踪规行矩步”。这与20世纪国人因苦难、抗争而产生的强烈的非理性情绪不相吻合,因而难以在更大范围内获得共鸣。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边缘,未必不是另一种中心!因为,边缘意味着结构的薄弱地带,意味着具有突破、转换,以及生成某种新秩序的可能。如果我们以边缘为中心,那么公众眼中的中心未必不是一种边缘。因此,我对慈江《杨绛,走在小说边上》一书末章的“走到人生边上”的“业余作者”的论述特别有同感。在这个时代,虽然不妨说我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的羁绊,但是我们又在更大的程度上跌入了商业的陷阱,跌入了专业主义等等陷阱。如果从“小说边上”看杨绛,把她视为一个作家、翻译家和学者的综合体,我们就会得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印象。
正如慈江所言,杨绛本人对于她的小说的优缺点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尤其到了晚年,更是超越了对于小说创作的纠结。这表现在她对于自己文学创作的态度,即认同文学创作的本质是“玩”。“玩”意味着一种自由的心态,意味着达观和超脱;“玩”也意味着,在杨绛这里,边缘与中心已然翻转,边缘可以是中心,中心也可以是边缘。当边缘成为中心之后,方能逃脱居于边缘的孤独、自卑与纠结,而得到心灵的解脱和大自在。因此,以边缘为中心,最终形成了杨绛文学观和创作观的内核。
当一种文学方式、一种生活方式已经僵化之后,从中心逃离,隐遁于边缘,应当是一种最为自然和惬意的选择。以边缘为中心,杨绛与于慈江的这种生活方式,为当代读书人提供了一个可供效法的范本,一种有意味的可能。其实,杨绛与于慈江所体味的这一边缘生活方式何尝不也是一种传统的回声。
或许,这才是慈江躲在闹市一角,孜孜矻矻埋首研究杨绛其人其作的初衷所在,也才是他的《杨绛,走在小说边上》一书的真正底色所在。
《杨绛,走在小说边上》,于慈江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10月,40.00元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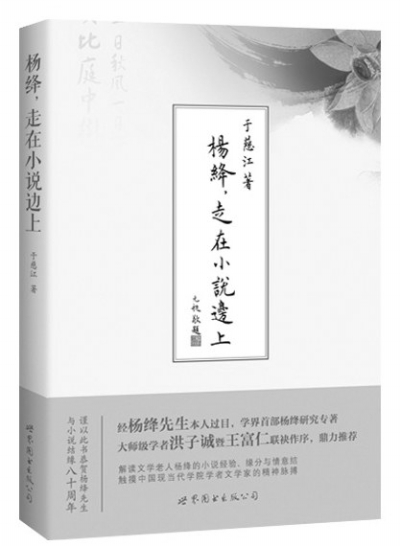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