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这个名字以及他独特的价值,因为那段特定的历史而在很长一段时间被遮蔽。近年来,有关这位传奇人物的那些并不算老的往事被逐渐开掘出来,即便只是流年碎影,但它折射出来的那种文化及人格力量,已足以穿越历史的尘烟,绽放一种耀眼的光芒,也温暖着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记忆。张伯驹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这是张伯驹一生遵循的收藏信念,他也用自己传奇的一生实践了这个诺言。
“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张伯驹
捐宝
1956年,故宫博物院收到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大礼: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及其夫人潘素将其30年所收藏的珍品——包括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以及黄庭坚《草书》等八幅书法,无偿捐献出来。
“张伯驹先生捐献的任何一件东西,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它的价值都不为过。”电视纪录片《故宫》的策划之一、紫禁城出版社社长章宏伟由衷地感慨。章宏伟说,为故宫做捐献的最顶尖的有两位,一位是捐瓷器的孙瀛洲,一位则是捐书画的张伯驹。故宫文物有150万件(套),能拿出来的有8000—10000件(套),但书画作品少之又少。其中陆机的《平复帖》,连同1952年同样由张伯驹捐赠的《游春图》,又是“极品中的极品”,至今仍被视为故宫博物院的“镇宅之宝”。
“稀世之宝”、“价值连城”这样的词汇,在张伯驹捐献的作品面前,仿佛一下子有了实实在在的意义。早于王羲之的《平复帖》,是现今传世墨迹中的“开山鼻祖”,虽长不足一尺,只有9行字,但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记,朱印累累,满纸生辉,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的《游春图》,距今1400多年,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用具体的数字概念来衡量这两件国宝的价值也许失之于轻薄,但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数字作为参考:2003年8月,为了购买晋代索靖书法作品《出师颂》,故宫博物院斥资2200万人民币。
“这几样东西父亲随便留给我们一件,就够我们几代人吃不完的,那不可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啊!”张伯驹与潘素唯一的女儿、73岁的张传綵老人笑眯眯地说。因为父亲在后海留下的唯一一所老宅因年久而修缮,她与老伴楼宇栋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一大早便冒雨搭公共汽车来约定地点接受采访。从外套后面不小心露出来的挂着月票的红绳,让人很难想象眼前这位衣着朴素的七旬老人,曾经是鼎盛时期在北京拥有数处院落、显赫而富有的张家大小姐。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睡觉前听父母讨论,说最后这一部分字画怎么办。我们那时年轻,也从来不过问父亲的事情。但知道他眼睛很厉害,收藏的东西都是精品中的精品。”1955年底,政府发行公债,号召人民踊跃购买。张伯驹也对这个新生的政府产生了信赖与热忱。“他跟我们说这个政府可不像国民党,我们应该要重视、要热爱。”一向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张伯驹还曾通过当时的统战部部长徐冰,把自己珍藏的李白真迹《上阳台帖》捐献给喜欢书法的毛泽东(1958年由毛泽东转给故宫收藏)。所以张伯驹从动员大会回来后就跟夫人潘素商量买公债之事。
“当时家里生活是没什么问题,但没有多少现钱,因为钱都买了字画,哪还有钱啊!”于是张伯驹与夫人商量,将30载所收藏的8件精品捐献出来,成为故宫的永世藏品。政府为此奖励的20万元,被张伯驹婉言谢绝。
“他说得很简单:‘我看的东西和收藏的东西相当多,跟过眼云烟一样,但是这些东西不一定要永远保留在我这里,我可以捐出来,使这件宝物永远保存在我们的国土上。’”张伯驹的女婿楼宇栋回忆。
“很多人不理解父亲,把好大一座房子卖了,换了一个帖子,再把这个帖子捐出去,到底为的是什么?但我能理解他,我真的能理解他。”张传綵老人很平静地说:“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爱国家的人,他认为这些文物首先是属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只要国家能留住他们,他付出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1956年7月,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为捐献8件国宝的张伯驹颁发了一个褒奖令,这张薄薄的纸片,被张家仔仔细细地保存着,它也见证了一个深爱中华文化的人为保存本民族文化遗产所做的伟大贡献。
“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张伯驹
收藏
“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张伯驹当年发自肺腑地说过。的确,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张伯驹试图以一己之力阻止许多珍贵文物流往国外,显得尤为悲壮。《平复帖》是其中最典型一例。
张伯驹最早是在湖北的一次赈灾书画会上见到《平复帖》的,当时归溥儒(溥心畲)所有。溥儒是道光皇帝的曾孙,恭亲王奕之孙。溥儒在1936年将所藏的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卷》卖予他人,后流于海外。这件事情让张伯驹久久不能释怀。据文物鉴赏家王世襄回忆,张伯驹深恐《平复帖》蹈此覆辙,因此委托琉璃厂的一位老板向溥儒请求出售。但溥儒索价20万元,张伯驹力不能胜而未果。第二年又请张大千也向溥儒求购,同样在20万的要价前止步。
一直对此念念不忘的张伯驹后来偶然得知溥儒最近丧母,急需钱财为母发丧,经藏书家傅沅叔斡旋,以四万元购得。张伯驹后来得知,另一位白姓字画商人听说此事后,也想拿到此帖卖给日本人,出价便是20万。庆幸的是,《平复帖》已在张伯驹手里。张伯驹后来写了篇小文,只淡淡地提及此事:“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在张伯驹眼里,这些蕴含了中国文化的字画的价值,甚至超过自己的生命。
1941年,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绑架案,被绑架者正是张伯驹。
“我父亲每个月都要到上海分行去开会,一早飞机下来以后,我们的车去接父亲。”像往常一样,一辆汽车开在前面,张伯驹乘坐的那辆车跟在后面。谁知一进胡同口,张伯驹很快被一辆黑色小汽车上下来的人带走。
绑架者的身份和底细也很快成了上海滩公开的秘密——他们是汪伪特工总部的“76号”特务组织,他们向张伯驹夫人潘素索要300万(伪币),否则撕票。
绑架者明显是冲着张伯驹的钱财来的,但张家的钱其实大部分都变成了那些珍贵的字画。“我父亲的叔叔跟我母亲到处借钱,因为家里没有钱,他们有钱都买了字画。”张传綵回忆,最简单可行的办法是变卖字画,拿钱赎人。潘素后来设法去看了张伯驹一次,丈夫却偷偷告诉她,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尤其那幅《平复帖》!
“父亲说:‘这是我的命,我死了不要紧,这个字画要留下来。’他还说:‘不要以为卖掉字画换钱来赎我,这样的话我不出去。’”如是僵持了近八个月,张伯驹宁可冒着随时被“撕票”的危险,也始终不肯答应变卖一件藏品。直到绑匪妥协,将赎金从300万降到40万,潘素与张家人多方筹借,才将张伯驹救出。
张伯驹很快离开上海,取道南京、河南来到西安,潘素将年幼的张传?托给西安的一位友人,自己一人先回北京。后来的几年里,张传綵只记得父母亲一次次往返于北京和西安之间,长大后才知道那时候北京已经沦陷,母亲潘素为了不让《平复帖》等国宝级的字画出任何意外,将它们偷偷缝在被子里,一路担惊受怕地带出北京。
张伯驹与《游春图》,是另一段值得被永远铭记的佳话。
20世纪30年代溥仪到东北当“伪满洲国”皇帝时,带走故宫1200件珍贵文物。1945年,随着日本的战败,一些珍贵字画开始流于市面。“吾人即建议故宫博物院两项办法:第一,所有赏溥杰单内者,不论真赝,统由故宫博物院作价收回;第二,选精品经过审查价购收回。”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张伯驹认为,那批文物中有价值的精品约四五百件,按当时价格,不需太多经费,便可大部收回。而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并未着手进行,遂使许多文物落于商贾之手。
1946年,北平古玩界传出消息:琉璃厂一位叫马霁川的老板正为一幅古画寻找买主,这幅古画正是稀世珍宝《游春图》。张伯驹原本建议故宫博物院出面买下,并表示如果经费不够,自己“愿代周转”,但故宫方面仍未有回应,无奈之下张伯驹决心个人出面。
琉璃厂墨宝斋掌柜马保山后来回忆,张伯驹与马霁川接洽在先,但马霁川索价800两黄金,“因马要价太高,先生不便再谈,于是转而请我从中周旋”,张伯驹最大的担心是《游春图》这样重要的国宝被唯利是图的文物商转手售至国外,“伯驹先生和我商谈时特别强调这一点”。马保山回忆:“当时我为先生如此尽力维护国家尊严,保护文物的精神所感动,决心倾全力以成全此事。”
经马保山斡旋,几次来回谈判,终于以220两黄金谈定。
但那个时候这个数字对张伯驹来说已显吃力。十几年里,他手里的钱几乎都买了古书古画,万贯家财已经用尽。在此之前,他刚刚以110两黄金收购了范仲淹的《道服帖》。当年一掷千金的富公子,现在连几十两金子都拿不出来了。
那时候,张伯驹一家住在弓弦胡同一处宅院,当年的那座豪宅占地15亩,富丽无比,在张伯驹住进来之前,它的主人是晚清大太监李莲英。“那里有四五个院子,花、果树、芍药、牡丹都有啊,好几个会客厅、长廊。”张传綵回忆,追求雅致生活的张伯驹十分喜爱这个院子,但为了购买《游春图》,张伯驹变卖了这处自己最爱的住宅。
成交之日,卖方找人来鉴定黄金成色,“那个商人说这个金子成色不好,要240两,就又加了20两。但是他说:‘你老岳父财力确实是不行了,最后那20两拿不出来了。何苦呢?这是倾家荡产啊,为了这么一幅画。’”楼字栋回忆。这幅几乎让张伯驹“倾家荡产”的画,在1952年被捐给国家。
“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
——张伯驹
传奇
“张伯驹”这个名字以及他独特的价值,因为那段特定的历史而在很长一段时间被遮蔽。近年来,有关这位传奇人物的那些并不算老的往事被逐渐开掘出来,即便只是流年碎影,但它折射出来的那种文化及人格力量,已足以穿越历史的尘烟,绽放一种耀眼的光芒,也温暖着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记忆。
1898年,一个叫张家骐的男孩出生于河南项城,他是张锦芳的长子。因为兄长张镇芳一直没有男孩,按照当时的习俗,张家骐被过继给大伯张镇芳,他便是后来闻名一时的张伯驹。
张镇芳曾出任晚清最大的盐官——长芦盐运使,以擅长理财而出名,后来还曾署理过直隶总督转任河南都督。张镇芳创办的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盐业银行,成为当时的四大银行之一。
张家的显赫,也与民国时期另一位重要人物袁世凯密不可分。“张家与袁世凯都是河南项城人,袁世凯的嫂子是张家的姐妹。”张传綵说。据与张伯驹有世交之谊的孙曜东老先生介绍,张伯驹与袁克文、袁克定等自小在一起厮混。张伯驹虽然在政治上不赞同一心鼓捣父亲做皇帝的袁世凯长子袁克定,说他是“赖家伙”,但在袁家潦倒以后,他一直接济袁克定的生活,直到1958年袁克定在张伯驹家去世。
“爷爷为父亲设计的路在军界、政界或商界发展。但父亲偏偏对这些丝毫不感兴趣。”张伯驹虽然也按照家庭意愿,学成于袁世凯兼任团长的“中央陆军混成模范团骑兵团”,但军阀混战以及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反而使张伯驹更有了远离这一切的决心。张伯驹后来在盐业银行挂了一个总稽核的空名,“但父亲说:‘我讨厌银行,我不是干一行的。’”而整日埋头于他的书画收藏和京剧、诗词。张伯驹与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溥仪的族弟溥侗被人并称为“民国四大公子”。
“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张伯驹在《丛碧书画录序》中自述。张伯驹似乎是注定为收藏而生的。收藏有两大要件:一为财,二为才。前者自不必提,至于后者,天生聪慧的张伯驹有令人惊叹的过目不忘的本领。他自己曾回忆,在友人家里偶翻一书,过若干天后,还能将其中诗句背诵下来,而持有此书的友人却毫无印象。
有人曾经描写他所见到的张伯驹,面庞白皙,身材颀长,肃立在那里,平静如水,清淡如云,举手投足间,不沾一丝一毫的烟火气。张伯驹那时所经历的生活,被人形容为中国现代最后的名士生活圈。而对世俗生活相当淡漠的张伯驹,好像也一直悠然自得地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孙曜东回忆,虽然拥有偌大一份家业,但张伯驹在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得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车轮而且能转就行了,丝毫不讲派头。”但对看中的文物,张伯驹却是一掷千金。“那时很多字画商人都喜欢和他打交道,因为人家开出的价,他从来不还。”张传綵说。
对于张伯驹散淡的个性,著名红学家周汝昌曾有很传神的描述:“我到了张先生那里,去熟了以后,我不理张先生,张先生也不理我,我要回学校了,我也不告辞,我出了门就走,摆脱俗念,我们那个关系没人理解。”
1945年,王世襄参与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的工作,得以与张伯驹结交。王世襄后来回忆,他一直想研究《平复帖》,但想到东西实在太珍贵了,他小心翼翼地提出能否在张家看上一两次。
“没想到我一说,他就说:‘你拿回家看去。’这下倒给我添了负担了……到家之后,腾空了一只樟木小箱,放在床头,白棉布铺垫平整,再用高丽纸把已有锦袱的《平复帖》包好,放入箱中。每次不得已而出门,回来都要开锁启箱,看它安然无恙才放心。观看时要等天气晴朗,把桌子搬到贴近南窗,光线好而无日晒处,铺好白毡子和高丽纸,洗净手,戴上白手套,才静心屏息地打开手卷。”王世襄回忆自己拿到这幅“稀世之宝”时的心情。“《平复帖》在我家放了一个多月才毕恭毕敬地捧还给伯驹先生,一时顿觉轻松愉快,如释重负。”
“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漠,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果酱,小碟黄油二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四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
——黄永玉
沉浮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张伯驹将国宝献于国家后的第二年,他就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陈毅知道我父亲打成‘右派’后,有一次要请我父亲吃饭,陈老总说像你这样一个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都捐给国家的人,还能是‘右派’吗,我想不出,我向你道歉。”20年后,教育家刘海粟也向张伯驹问及被打成“右派”后有何感想。张伯驹则坦诚回答:“此事太出我意料……不过我告诉自己,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给我一顶帽子呢?”
在建国初的一次文物展览会上,陈毅与张伯驹一见如故。1962年,经陈毅介绍,张伯驹夫妇来到长春,张伯驹出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四年后,张伯驹将自己所剩的书画收藏共计30多件又捐献给吉林博物馆。其中一幅是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被认为是我国绘画史上保存下来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张伯驹曾经这样表达过:“我终生以书画为伴,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但这样一件被他视为最后的精神慰藉的作品,最终也捐了出去。
但张伯驹的命运继续向下滑落。1967年,张伯驹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隔离审查了八个月后,被迫从吉林省博物馆退职,送往吉林舒兰县插队。但公社拒绝收下这个已经快70岁、不会劳动还要靠公社养着的老头。在一个雪天里,被拒绝落户的张伯驹夫妇离开舒兰,返回北京。
“回到北京,原来的地方已经被别人占上了,只留了一间,就是一间十平方米的屋子,一间里头大概分了两间,外头放了一个桌子,父亲在那整天写什么,里头屋子用来睡觉。”
曾经拥有稀世宝物的张伯驹,一下子成了生活无着的落魄老头。一无粮票,二无户口的张伯驹老两口,靠亲戚朋友的接济,勉强过了一年多。
楼宇栋说,张家生活好时,曾有大大小小十位管家,负责中餐、西餐的四位大厨,但这样的生活落差好像并没有让张伯驹有多大困扰,“在1969年到1972年最困难的三年,我曾几次去看望他。除了年龄增长,他的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王世襄回忆。忆及父亲,女儿张传綵还是不免酸楚:一辈子手不经钱的张伯驹那时也学会带点零钱,出门为家里买点零用品,“即便那样,也从来没听他抱怨过什么”。
像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张伯驹的命运也因一个偶然之机而突然转变。1972年,患难之交陈毅逝世。悲痛的张伯驹要求前去吊唁,但由于他的政治身份,最终不能如愿。他挥泪写了这样一副挽联: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这副被悬挂在灵堂中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的挽联,突然被穿着睡衣、临时赶来参加追悼会的毛泽东捕捉到了。他连声说写得好,询问陈毅夫人张茜,撰联者为何人。张茜趁机将张伯驹的近况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马上交代让周恩来总理解决此事。于是,“黑”了三年的张伯驹才正式落户口于北京。
待1978年平反,张伯驹已是位八旬老人了。而80岁以后,是张伯驹一生最忙的时候。他频频参加各种戏曲、诗词、书画研讨会,想为他挚爱的中华文化尽最后一点力量。但留给他的时间并不算很长。1982年正月,参加宴会归来的张伯驹突患感冒,被送进北大医院,因级别不够不能住双人病房或单人病房,张伯驹和七八位病人挤在一个病房,不时有重病号抬进来,死的人被拉出去,心绪不安的老人闹着要回家。2月26日,等到女儿终于拿到同意调换医院的批令时,张伯驹却刚刚离开人世。
1995年5月黄永玉先生出版画册,其中有一幅《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1982年初,黄永玉携妻儿在莫斯科餐厅吃饭,“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漠,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果酱,小碟黄油二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四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王世襄也感慨:实在使人难以想象,曾用现大洋四万块购买《平复帖》、黄金220两易得《游春图》,并于1956年将八件国之重宝捐赠给国家的张伯驹先生、夫人竟一贫到如此地步。他十分赞颂黄永玉为张伯驹下的论断——“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张伯驹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这是张伯驹一生遵循的收藏信念,他也用自己传奇的一生实践了这个诺言。
(本文摘自《走出历史的烟尘》,李菁/著,人民东方出版传媒东方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定价:36.00元)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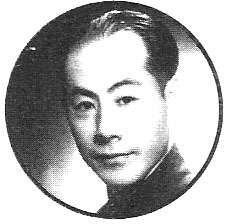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