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达先生为中国著名植物分类学家,以研究金缕梅科、山茶科闻名于世。先生生于1914年,已是百岁老人。1935年8月张宏达考入中山大学理科生物系,1939年毕业,留校任教并从事研究,此后未曾离开该校,仅两度转至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工作,但为时均不长久。余作《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史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之撰写,对张宏达与该所之关系,所得材料甚少。当获悉广州中医药大学之李剑、张晓红合著《张宏达传》,先后于2011年5月和2013年5月在“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目之有关会议上,遇见两位作者,曾主动询问相关事项,未得确切,私下以为他们于此也知之不多。2014年1月拙著出版之后,得读他们合著的《张宏达传》,始知该书还是记载不少张宏达与农林植物所事,惜未能及早购置,以致错过引入拙著之机会,今作此文,或为补充。
中大农林植物所设立之初隶属于农学院,1937年陈焕镛在主持该所之同时,曾兼任中大理学院院长、生物系主任。其时,正是抗战军兴,陈焕镛在转移农林植物所标本图书至香港时,也将生物系之重要标本图书一同转移,而在香港设立农林植物所香港办事处,而生物系随中山大学迁往云南澂江,陈焕镛随即辞去理学院院长和生物系主任职务。此后,理学院及生物系对陈焕镛有极大意见,生物系主任董爽秋公开指责陈焕镛对生物系标本予以巧取豪夺。此时,张宏达为生物系学生,其毕业论文《澂江之植物》正是在董爽秋指导之下完成。张宏达视董爽秋为恩师,对乃师指责陈焕镛抱支持态度,“年轻气盛的张宏达还和陈焕镛发生过争执”(《张宏达传》第67页)。
张宏达与农林植物所直接发生关联是在1942年9月。此时,中山大学已自云南澂江迁往粤北坪石,张宏达先在中大师范学院任助教,因参加驱逐院长活动,而未获得续聘,即由理学院生物系主任“任国荣将他推荐给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院长崔载阳,为他谋得研究院农林植物学部助教一职”。(《张宏达传》,第56页)。农林植物学部乃源于1935年中大成立研究院后,将农学院土壤研究所和农林植物研究所合称为农科研究所,其下再分别名之为土壤学部和农林植物学部。其实农林植物所与农林植物学部基本上属于一个机构两个名称而已。1941年12月在香港即将沦陷之时,蒋英离开香港,前来坪石,依靠中大,在极为艰难条件下,另组农林植物研究所。拙著记载了张宏达加入研究所,但对加入之原因,则有未知,此可补其缺。
《张宏达传》载:“张宏达在农林植物学部任助教期间,主要工作是协助蒋英鉴定标本,并代蒋英上农学院的课,张宏达说:‘当时老头——蒋英蒋先生,他讲的是上海话,学生听不懂,只好让我去教。’”(第58页)张宏达称前辈蒋英为“老头”,似有不敬,不知何故,难道是蒋英两次派遣张宏达单独外出考察,使其处于危险境地所致。“在植物学部工作期间,蒋英两次布置张宏达单独一人出差采集标本,一次是莽山,一次是衡山。1942年9月,张宏达进入宜章莽山,恰逢秋雨连绵,又罹患痢疾,被迫下山。1944年6月,张宏达第二次到衡山考察,先后宿广济寺和方广寺,才得标本200余号。6月底,日寇进陷长沙,窥伺衡阳,张宏达幸得南岳农校校长张农教授通知,仓促下山。当时日军活动频繁,张宏达昼伏夜行,两天后才返回坪石。”(第58页)一般而言,植物学家野外采集,很少单独行事,即使一人而往,亦会在当地请向导相伴。拙著注意对野外考察事件,并予以记录,于1942年9月之考察有云:“1942年九、十两月,由植物所与研究院农林植物学部联合组队,再往莽山调查。调查队分成两队,一由梁宝汉、张宏达、梁仕康、冯云组成;一由李鹏飞、陈少卿、游万里、虞元章、黄荣华组成。得标本1,436号,12,000份。”(第126页),可见此次采集非张宏达独自一人前往。至于1944年6月赴衡山,未见材料,没有记录,待查。张宏达与蒋英之间存有距离,当属事实,其由者何,尚希考证。张宏达返回坪石后不久,即离开农林植物所,回到中大理学院生物系任教。至于何种原因,《张宏达传》未作交代。
抗战胜利,中山大学复员,农学院将陈焕镛此前自香港迁回广州之农林植物所与蒋英在坪石设立之农林植物所合并,继续名之为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旋因中大理学院控诉陈焕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依靠伪广东省教育厅将植物所从香港迁回广州,属汉奸行径,得中大校长支持,获广东省高等法院受理。继而中山大学将植物所改为中山大学理学院植物研究所,任命生物系之吴印禅为所长,此时在生物系任教之张宏达又成为植物所之一员。指控陈焕镛有力者,有任国荣,而此时张宏达正与任国荣之妹由恋爱而结婚。陈焕镛当然对理学院之控告有极大之不满,在广东省高等法院作出免于起诉判决后,而以领导广西大学经济植物所为由,其本人主要在桂林工作,直至1954年将植物所改隶于中国科学院而成立华南植物研究所为止。期间陈焕镛偶尔回广州,张宏达有请教机会,《张宏达传》如此记述:
刚到研究所工作时,张宏达没有方向,他征求陈焕镛的意见,陈焕镛对他说:“你就搞金缕梅,你的老师董爽秋就是在德国搞金缕梅,他现在不搞了,你就跟上去。”张宏达认为陈焕镛的这个建议对他的帮助特别大。
开展对金缕梅科的研究工作后,很快,张宏达发现了该科的一个新属。他十分激动地告诉陈焕镛,陈焕镛兴奋底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真是走运,因为这个标本陈焕镛自己用过,但他没有发现。张宏达想跟陈焕镛一起发表,陈焕镛说:“你发现的,当然你发表。”张宏达便把这个新属命名为陈琼木属(Chunia,即山铜材属),以此来表达对陈焕镛的崇敬之情。
张宏达说,他在跟随陈焕镛从事分类学研究后,发表过好几个新种,陈焕镛不跟他争,因为陈焕镛已经成名成家,他更乐于把机会让给学生。关于金缕梅科的研究,张宏达所撰写的论文AddittionstotheHamamel⁃idaceousFloueofChina(《金缕梅科植物补遗》),是陈焕镛亲自为他修改英文句子和拉丁文名词,让他把论文发表在Sunyatsenia上。
现在年事已高的张宏达,有很多往事已经淡忘了,但他对陈焕镛的感激之情从未磨灭,在采访中,他说“我就是陈老(的学生),陈老也愿意把我当作学生……”一语未尽,已哽咽难言。(第67-69页)
张宏达将自己认定为陈焕镛之学生,但余在陈焕镛档案中却未见陈焕镛将张宏达看作是自己门人。即使在“文革”期间,大量揭发批判材料,均是陈焕镛亲近之人所写,但没有张宏达所写;所写内容也几乎没有涉及张宏达,故据此断定彼此交往并不深切。在中大植物所历史中,张宏达也不占多少地位,故在植物所改隶中科院后不久,张宏达即回到中大,而没有留在华南植物所。我们当然不怀疑张宏达所述为真实,也不怀疑其感情之诚挚;只是怀疑期间还有一些际遇未能说清说透。阅读《张宏达传》已知传主在求学成长过程中,有多位老师与其有知遇之恩,如董爽秋、如任国荣,为何仅在回忆陈焕镛时,而不能自已,此中必有原委,惜传记作者未曾追问,我们也就无从说起。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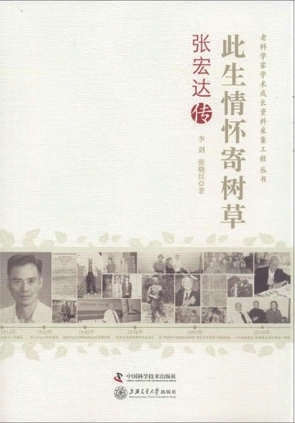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