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脸之书》可以让大陆的读者看到另外一种台北。其实我是宅男,没那么多认识外界的机会,也没有长期稳定的工作,更没有像莫言啊贾平凹啊那样的乡村生活经历,我的家庭也不是大家庭,所以我这些方面的经历很单薄。我特别想要成为像赫拉巴尔那样的作家,写出《底层的珍珠》,像一个城市人类学的采集者。
十年前,不到四十岁的台湾作家骆以军已经写出了《红字团》、《月球姓氏》、《遣悲怀》等为文坛注目又获读者认同、奖项肯定的作品。他对小说写作心怀虔敬,几乎是不管不顾地全情投入,写作之于他是非常辛苦又如此享受的神圣之事。就在那时,或为稻粱谋,他接了《壹周刊》的专栏,以每周一篇的频率写台北芸芸众生的故事,这一写就写到今年被停掉为止。
新近在大陆面世的《脸之书》即源自这些专栏文章,这些篇章经骆以军精选,以两本书的体量呈现。虽然不同于他的代表作《西夏旅馆》那样在主题、篇幅、结构和气势上才情洋溢、野心勃发,但书中出没在台北的那些形形色色面孔,连同他们五味杂陈的人生,以或现实或魔幻的方式,被讲述或评议,有着生动、鲜明而独特的意味。
对于很多作家来说,写小说特别是写长篇小说才是要紧事,至于写专栏文章,更像是写小说写得太劳神费力后的某种调剂,看轻专栏写作者不乏其人。骆以军也听到过文学前辈或同侪对其写专栏的告诫,诸如这样会把文学手感写坏、浪费素材等等。可他从未以敷衍之心去对待那每周笔下的两三千字,反而将小说写作中的“较真”带过来,费心搜罗、耳闻目睹,从一个侧面观察他生活着的城市以及城市中的人,像做拼图一样,一篇篇勾勒出台北的众生相。
骆以军对本报记者谈及《脸之书》的写作,坦言其中有为生计的成分,但他对这部作品相当看重。他说这个主题的写作受到本雅明《单向街》的启发,他想要像赫拉巴尔那样写出属于他自己的“《底层的珍珠》”,也期望读者能从这些文章中读出有别于张大春、朱天心、舒国治笔下的骆以军的台北来。
读书报:四年前采访你时你说会为了生计接一些写广告文案或专栏的活,当时有前辈作家还为此告诫你,不过你认为写专栏是种锻炼。《脸之书》是专栏结集,虽然是一个个短篇构成却有不输给长篇小说的独特魅力,这似乎印证了你对专栏写作的看法。
骆以军:《脸之书》来自我在《壹周刊》上写了十年的专栏。不过这个专栏今年被停掉了,我就比较惨,得要一直去接外头的活。之前我也没怎么存钱,都是靠这个专栏的收入。可是你看,在西方,像是福克纳这样的作家也是一直在为经济所困。
我觉得《脸之书》的写作对我是有意义的,书里的内容是我从比较晚近的专栏中筛选出来的。早期的专栏结集出了《我们》,那个我也蛮喜欢,那时三十出头,有种每一篇都是把青春时期的真实经历写成个故事的感觉。写这些专栏的过程中确实有长辈或好友劝我,叫我别那么奢侈地把这么多的故事、素材随便用在专栏文章里,至少留着写短篇小说用。可是他们不知我的处境,我心目中认定的写作肯定也还是写长篇,但我生活在台北,又有小孩,需要维持基本的生存。我很感激写专栏的机会,我没有用书评、时论和游戏文章去敷衍。几乎每一篇专栏我都当做是文字的素描练习。
写完《西夏旅馆》之后,我有蛮长的低潮时间。2008年我在台湾出版了《西夏旅馆》,今天离那时已经很久了,可是我到大陆来还是跟我谈《西夏旅馆》。如果我是个对自己的创作很严格的作家,就应该花大力气把《西夏旅馆》在我心里洗掉。幸运的是我已经写完了一部长篇《女儿》,这部作品从文字到视觉设定到剧场打开般不断趋近的结构,都跟《西夏旅馆》完全不一样。
读书报:据说《脸之书》书名由Facebook(脸书)而来,“脸书”这样的网络交流方式一方面打破了人与人交流的空间阻隔,另一方面未必不是加剧了现代人的孤独感。从你书中所写的这些人和他们的故事里,能读出一种伤感和悲悯。
骆以军:也不光是对现代人这种交流方式的悲悯。这里我想提一下本雅明的《单向街》(大陆译本为《单行道》),他在写《单向街》时充满感伤和怀念,他不是小说家,写作模式是怀着古典教养的哲思短篇,作品中满是发着灵光的艺术气质,是人们对真实时光中发生过的事情的珍惜。记得那里边有一篇叫《全景幻灯》,记录他一趟穿越欧洲的旅行。而这一整本书的结构就是用全景幻灯的概念。他那个时代没有脸书也没有微博,他试图在作品中呈现这样一种观看方式——放在游乐场的长椭圆形机台,每个机台有很多窗洞,里面循环放幻灯片,这些幻灯组成完整的故事。你或许不是从第一张开始看,但看到最后你会有默契。最终每个观看者都看了完整的幻灯片,可是每个人观看的次序不同,脑中对故事全貌就会有不同的理解。我当然没有能力做到本雅明那样,不过《脸之书》中的一些想象是受《单向街》的启发。
读书报:既然《脸之书》中的文章绝无敷衍之作,那么写得好好的专栏为什么停掉?
骆以军:《脸之书》中的这些篇章是《西夏旅馆》之后写的。写《西夏旅馆》时感觉太爽了,对文字的那种动员简直是激爽。可是当时每个礼拜要交一篇专栏,我就从写好的长篇小说中“切一段”发过去。那时有前辈觉得我是用专栏拼贴成《西夏旅馆》,其实我是写完了《西夏旅馆》再切成专栏交出去,哈哈。后来他们发现我的专栏在周刊读者中的阅读率特别低,加上我写《女儿》时又犯了老毛病,那时我写得力气耗尽,就把其中的若干部分拿去发专栏,他们不开心,专栏就停掉了。
我不知道台湾的小说家和大陆的小说家是否各有各的苦处,在台湾,即使你成为小说写作这个行业里拔尖的,也还是免不了“餐风露宿”。这有个好处,不会担心被圈养在一种舒服的状况里。基本上,作家免不了强迫去撕裂自己,跟这个世界持续搏击。我不能说,哦,我已经练了《西夏旅馆》的功夫,就此形成自己的小宇宙。我得用这一套再衍生出我观看世界的方式,重建,对我来讲特别痛苦。
读书报:《脸之书》的腰封和宣传文案上都提到这是“台北一千零一夜”,我反而觉得你的这些短篇更像现代都市版的《聊斋志异》,那种市井气,小人物的卑微与困境,那种现实生活中的超现实一面,乃至那种笑中带泪的讽喻意味,都和《聊斋志异》相似。
骆以军:哈哈我好喜欢你这个比喻。
读书报:我知道你有在咖啡馆、小旅馆写作的习惯,书里这些故事是从那些地方听来的还是来自“脸书”?你不会像传说中蒲松龄那样专门摆个茶摊引人来提供故事吧?
骆以军:哈哈,不是不是。我是打工型的文字侦探,不是开茶馆的私家侦探。这些故事是我很辛苦很好奇地“偷来”再拼装的。没办法,我每个礼拜都要卖文为生,得去找这些故事。
这些年很多个人风格很强大的台湾作者到大陆,比如舒国治。我现在发觉在台北,常混那一区的小文青心目中的台北就是舒国治的台北。也有之前朱天心的《古都》里的台北地图甚至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里的台北。我希望《脸之书》可以让大陆的读者看到另外一种台北。其实我是宅男,没那么多认识外界的机会,也没有长期稳定的工作,更没有像莫言啊贾平凹啊那样的乡村生活经历,我的家庭也不是大家庭,所以我这些方面的经历很单薄。我特别想要成为像赫拉巴尔那样的作家,写出《底层的珍珠》,像一个城市人类学的采集者。
读书报:很多时候,一个地方或者一座城市与一位作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赫拉巴尔和他的捷克小城,比如莫言和他的高密。而你在《脸之书》中写了那么多台北形形色色的人和故事,也有不少对这个城市的描述,你怎么看待你和台北的关系?
骆以军:对我来讲,台北很像是在阴阳界、换日线。到了我这个年纪,我的左眼看着过去右眼看着未来。左眼看的和朱天心、本雅明他们比较类似,我在永和长大,那里不是大城市,小时候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大家挤公车。那里有日本留下的规划得不怎么好的小巷弄、小栋房,挤在一起像迷宫像十二指肠,发生火灾时消防车都进不去。我从三十八九岁住到台北市区,租房子,家很小,书房乱得完全没有风水,没办法写稿。十年来我写稿都是打游击战,背个书包,里面装着纸和笔,我有能力专心地进入写作状态,旁边再吵,我都能写。
我重翻《脸之书》,会觉得里面的很多篇都像是在做很纯粹的小说的发动,它像我自己的一个练功谱。如果有晚辈看到这本书,里面有很多个两千字三千字,已经是一部短篇小说的发动,可是我不把它发动完,点到为止。
读书报:《脸之书》里那篇《丢弃难》让我印象深刻,文章中记录的那位前辈作家,向你讲述他到各地活动时对如何处置收到的很多作者赠书深感为难,特别是你在文章中那个关于来自大街小巷彼此无关的书哗啦啦飞进一个异地人的旅馆房间的意象。面对互联网上海量的文字,面对诚品书店里满坑满谷的新书,作为作家,你是否有过写作上的幻灭感?
骆以军:那篇里那位前辈作家就是写张大春啊,他特别逗。台湾印刻出版公司的老板初安民有一次跟我讲,他决不让作者去看他存书的仓库。那些作者以为他们的作品都放在大书店里,实际上大批的书堆在仓库,真实的结局是被压成纸浆。我光听到就觉得死也不要去看,那会让我瞬间崩溃,再也不想写了。大约十五年前,我去敦南诚品,那时我已经出了三本书。去诚品翻翻,不止是我刚出了两个礼拜的一本书那里没有,整个诚品的书架上也没有我任何一本书,可是我已经为此写了十年。(本报记者 丁杨)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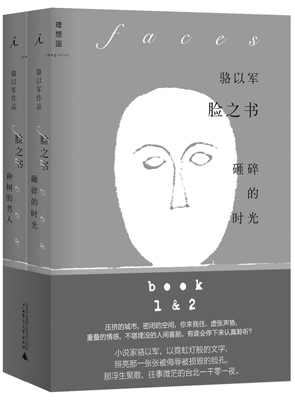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