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南的一次民间问卷调查中,作家韩少功和亚龙湾等名胜一起,并列为热爱海南的12种理由。1988年,韩少功携妻将女来到海南时,大概不会预料,此后他的名字和海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成为海南的一个标志性的文化符号。
也许知情人很容易从韩少功的很多作品里辨出经历、感受、语言等方面的海南元素,哪怕是写湖南,海南也构成了他重要的参照系,成为作品中隐形的“主角”。
是的,在海南的二十多年,他没有学会闽南语,对海南的深度了解也有限,这是他的遗憾。可是,这并不意味他在海南的二十多年是空白。恰恰相反。韩少功说:“海南是我的成熟期和成熟之地。”
1988年,韩少功从湖南至海南,主办《海南纪实》《天涯》杂志,主张“摆事实不讲道理,雅事俗说和俗事雅说”,创下《海南纪实》发行过百万的纪录;1996年他担任海南省作协主席,后担任省文联主席和党组书记。15年后,他离任时海南文艺界的同事们动了感情,不少人掉了眼泪。
“我多次说过,我感谢海南,感谢这个清洁和美丽的岛。”韩少功说。很凑巧,在他60岁生日之后,似乎是为了海南书博会的献礼,他完成了新长篇《日夜书》(上海文艺出版社),这时,距他的上一部长篇小说《暗示》已经过去了十年。
读书报:您的很多作品,都是缘自知青。“知青”似乎对您而言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您怎么看待知青那段经历对自己的影响?和自己的创作又有怎样的渊源?
韩少功:一个人的少年时代是一张白纸,留下的痕迹较为清晰,对日后的影响可能很大。但日后的岁月是显影剂,是变焦的镜片,可以改写少年的记忆。所以仅有知青一段是不够的,即便是写知青,后来的经历和感受会决定你是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比如《飞过蓝天》《西望茅草地》同是写知青,但与《日夜书》一比,显然就不是一回事,可见记忆是有各种升级版本的。
读书报:《日夜书》的写作,从知青时代写起,同时关注了他们后来的命运轨迹。通过这样的回顾与梳理,您有怎样的收获?以知青为题材的作品,各种体裁不胜枚举。但是您的作品,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当然《日夜书》中的人物不尽然都是知青。您怎么看《日夜书》对于自己、对于知青文学的意义?
韩少功:写知青有各种各样的角度,我的角度不可能取代他人的角度。而且“知青”只是一个身份,一个载体,承载的是人性,与其他身份承载的内容没有太大区别,因此一般来说我从不用“知青文学”这一类概念,就像我从不用“工业文学”“农村文学”“改革文学”这些概念。托尔斯泰的《复活》不能归类到“言情文学”吧?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也不好归类为“乡土文学”吧?从出版目录到网络栏目,中国现在搞出了好多小说类别,搞得我十分困惑。我觉得这本书就是一本叙事,一本读物,有兴趣的读者看看就好,别管它可以划入哪一类。
读书报:在《日夜书》的写作中,听编辑说您反复修改多次。修改是针对哪方面?
韩少功:大的架构变更有过一次,其余都是小修小补,相当于围棋终局的收官。这些小修小补在读者受益之前,首先是作者自己的享受。我是个贪图享受的人,有时候会一改再改,好像永无定稿。一个句子改顺了,更生动了,更精粹了,更有力量和光彩了,心境快乐无比。写作最大的乐趣其实就在这里,在于心手相应,无中生有。
读书报:您在一系列小说文本中塑造了鲜明生动的知青群像。有知青上山下乡时理想与现实的悖离,也有知青回城后的多彩人生。您希望以这种叙事表达对知青群体怎样的认识?这次写作和过去的知青写作心态有何不同?
韩少功:我的这些同辈人经历了“文革”和改革,是中国几千来社会变化最为剧烈的一段,构成了坎坷、震荡、裂变、悲欣交集的一个巨大总和。在国外与西方朋友们聊起来,他们从家庭到学校,从学校到机构,几十年的还贷和纳税,公式化的人生轨迹几乎千篇一律,我们随便说一两段往事,他们都会觉得惊讶不已。但这样一大片经验资源,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沉淀、消化以及回应。我们到底做过了些什么?我们到底有哪些得和哪些失?如果与儿孙辈交谈起来,我们能提供哪一些人生教训?……这就是我写作中经常遇到的疑问。事情毕竟过去这么多年,我希望自己尽可能克服情绪化,多一些冷静求实。
读书报:从成名作《西望茅草地》到寻根文学的扛鼎之作《爸爸爸》,再到引发文学界激烈争鸣的《马桥词典》和《暗示》,以及获得首届萧红文学奖的《赶马的老三》,您的风格多变总是带给文坛新的思想和形式的冲击。每位作家都在寻求突破和创新,为什么您的创新格外引起大家的关注?
韩少功:迄今为止我一直不是畅销作家,说不上格外的关注吧?我比较害怕重复,流水线式的生产,有点“喜新厌旧”,如果能得到他人谅解,已经心存感激。
读书报:《想不明白》集中了您的各种风格。能否谈谈《想不明白》一书对您,或者对文坛而言有怎样的价值?
韩少功:你说的这一本,是思想随笔或文化随笔的集子。我喜欢叙事,也喜欢思辨,就像上一顿吃了萝卜,下一顿想吃白菜,没有任何法条规定我不能吃白菜吧?小品演员可以客串唱歌,主持人可以客串唱戏,我当然也可以客串编辑,客串翻译,客串学者的活儿。这是我的个人权利,或者说是不妨碍别人的个人癖好。至于你说到这本书的价值,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打分。也许这个裁判权属于读者。
读书报:您自称是进行“文体破坏”的创新之作,但是也能够隐约看出很多作品与魏晋的笔记小说《搜神记》、《世说新语》的体式的接近——有这方面的因素吗?能不能理解为,您的“创新”也是有根脉和传统的?
韩少功:没错,我早就如实招供过,我一直想把散文元素引入小说,想在小说与非小说之间搞点杂交和混搭。欧洲传统小说是从戏剧脱胎的,而中国传统小说是从散文脱胎的。这是钱穆老先生的明见。俄国文学传统只区分“散文”与“韵文”,在这一点上似乎也接近中国。如果我们在大力引入欧洲体裁资源的同时,对中、俄的传统文学经验也予以重视和利用,尝试小说的多种可能性,这不正是文学之福?
读书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对80年代的中国文坛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西学思潮的裹挟,给您的创作带来什么影响?为什么您能在80年代就提出“寻根文学”?“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在民族文化传统的土壤中,根不深。则叶难茂。”——并非所有作家都能在当时清醒地意识到,不只是中国文学,所有文学的成长与成熟必须扎根于民族的土壤。“根”的意识和寻根的追求几乎贯穿了您的创作始终,您觉得呢?
韩少功:全球化肯定不是同质化。这在全球化的“后半场”一定可以看得更清楚。多重的、多样的、多元的全球化,或者说同质化与异质化交织并行的全球化,正在各个领域激烈地重组,文学也不例外。在这个意义上,重视本土文化之“根”当然是必要的。我向青年朋友们推荐过王洛宾,推荐过杨丽萍……这比国外的例子更容易理解。如果把他们与全球无处不在的三流RAP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艺术的大道在哪里。只是要提醒,决定艺术成败的因素太多了,“寻根”也不是灵丹妙药。把“寻根”变成一味的恋旧、做旧、搞收藏、装神弄鬼、民情风俗三日游,也就是一般的商业策略了,流于皮相而已。有些外国汉学家经常把“中国的马尔克斯”或“中国的卡夫卡”当作奖赏桂冠,但我想莫言、贾平凹等等肯定是不满意的,不甘心的。
读书报:上世纪80年代的两部中篇小说《爸爸爸》《女女女》,最近被西方艺术家改编为音乐剧上演。荷兰知名导演哥力尔和音乐家克拉斯导演作曲。中国当代小说好像很少有被改编成音乐剧的,这个改编中间有何契机?
韩少功:我没有参与改编,不了解具体情况。听说音乐素材的很大一部分来自韩国,这恐怕也不奇怪。中西文化交流,以程度不同的“误解”为“理解”的常态,中国人对西方大多也是这样。百分之百的理解对接,几乎不可能。我们读司汤达,读福楼拜,肯定与很多西方人的感受差之甚远。我们得经常提醒自己这一点。
读书报:90年代以后,您的小说越来越少,散文相对丰富,而且相继几部长篇小说也呈现出明显散文化的倾向。有人认为这是“韩少功遭遇创作危机的表征。”您怎么看?有创作遇到瓶颈的原因吗?如何理解您创作上的这种文体倾向?
韩少功:我从未远离过“创作危机”,从一开始就这样,经常觉得自己写不动了,写不好了,写不下去了,自己对自己不满意。“瓶颈”几乎是接二连三,十面埋伏。但把“散文”与文学创作撇得那么干净有点奇怪,相信很多散文家要同他们急,鲁迅、沈从文等也会不同意。他们还不如说对我的小说失望,就像这本《日夜书》,有的网友大呼过瘾,但也有网友说读着读着就睡了。这完全正常。我会尊重和注意读者们的批评。
读书报:您的小说想象奇丽,文体多变。您觉得这种风格是否受到民族传统文化和巫楚乡俗文化的影响?
韩少功:我在湖南生活多年,肯定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不过,任何地域文化都会有奇丽的一面,只是有时候深藏不露罢了。前几天我在海南看“公祺”,民间庙会祭祀。在一个偏僻的村落里,几千人一起呼啸,一大群男人突然抓狂,吃了摇头丸一般“神灵附体”,其狂野气氛,比那些迪厅场面更厉害,比拉美、非洲、欧洲某些节日更惊人。说起来,农耕民族在一般人眼里,都是比较温和、内敛、世俗的,你怎么可以想象他们突然间变得这样疯魔?你怎么可以想象,这种传统的巫俗与摩托车、可口可乐、电子流行音乐可以并行不悖?我的意思是,文化与生活本身就是这样奇丽多变,问题是我们可能视而不见,我们的文学无端地变得中规中矩乖头乖脑。(本报记者 舒晋瑜)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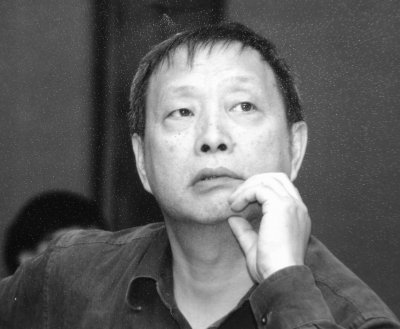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