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美国儿童图书服务协会将纽伯瑞金奖授予了《蝎子之屋》,这本书也和《记忆传授人》等一起成为纽伯瑞奖中为数不多的科幻儿童文学作品队伍的一员。科幻小说在以前并不轻易入评委会的法眼,甚至在很长时间里文学领域并不将科幻小说视为文学读物。有人分析道,这和《哈利·波特》等崇尚幻想的小说广受欢迎不无关系,这本《蝎子之屋》也确实没有让出版社失望,出版不到一年,已被译成十八种文字,风靡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不论是纽伯瑞儿童小说,还是世界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很多作家愿意选择“少年成长”或者“少女成长”等来呈现,比如《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蓝色海豚岛》、《少女进化史》等,我们可以将它们归入“成长小说”,成长中儿童要经历的生理和心理的破茧成蝶,其中确有可以让作家纸上生乾坤的戏剧性。类似于马克吐温,作者南希·法默擅长处理这种类型的文学作品,让她笔下的小主人公们经历一次冒险之旅,在旅行中成长。她的第一部纽伯瑞获奖小说《The Ear, The Eye, The Arm》讲述了津巴布韦三个具有冒险精神的孩子从他们父母的大宅子逃出去探索危险世界的故事。而第二部纽伯瑞获奖小说《A Girl Named Disaster》中的女孩当她知道自己要嫁给一个有三个妻子的冷酷男人时,便坚决要逃亡,就乘小舟从莫桑比克去往津巴布韦,她要去那儿找她的父亲。一路上遇到很多艰难险阻,也给予了她勇气和力量。《蝎子之屋》也不例外,呈现了一个男孩在“蝎子之屋”成长的故事,并为它安排了迥异于其他小说的年龄分段:青年(0~6岁)、中年(7~11岁)、老年(12~14岁)、十四岁、新生。之所以如此安排,与主人公的身份不无关系,这个男孩是从母牛肚子里反刍出来的克隆人。
所以,作者想要刻画的不仅是一个成长的男孩,还是一个“异类”克隆人,使纽伯瑞奖获奖作品中首次出现了克隆人题材。中国科幻前辈叶永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有一篇评论,戏称科幻小说里有三种人——机器人、外星人和克隆人。可见很早科幻作家就将眼光投向了克隆人,但是进入儿童文学视野少之又少。吴岩主编的《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中提到:“克隆科幻小说从一开始就是从技术和伦理两个角度进行构思的。”虽然《蝎子之屋》中也涉及了克隆技术、全息投影、控制技术、人机合体等技术,但是作者只是将它们作为未来空间的结构要素,她用这些技术点缀在搭建的未来时空中,是为了伦理道德图景的展开提供平台。
怎样处理克隆人的身份?克隆人到底是不是“人”?怎样讲述克隆人的成长?主人公怎样应对自我认同危机?主人公所处的环境以及环境中的人怎样看待他?从对他的态度上要展示哪几类道德观?克隆人到底能不能拥有智慧和爱情?这些问题都需要作家重新考虑,也同样给读者以最初的阅读动力。
读者的阅读动力如果仅仅是这些问题那就体现不出作者的功力了,要持久地激发读者的好奇心,悬念是必备的要素。小说第一章便以一个医生的视角来看显微镜,“开始时一共三十六滴,三十六滴生命是那么渺小,艾得瓦尔多只能在显微镜下才能看见它们。在黑暗的房间里,他急切而又专注地观察着它们。”第一章结束时唯一活下来并且没有被打针的孩子就是小主人公,他是书中最大的权威毒枭阿尔帕特隆的克隆人——马特。第二章开始一直到故事结束,采用的一直是马特的叙述视角,作者要展现马特的心灵成长史,展现马特心灵世界的开阔和纵深度,应用马特的叙述视角是必然之路,然后呢?就像罗伯特麦基说的:“作家就是心灵虫,写作者要潜入人物心灵中,发现他的各个方面,他的潜能,然后创作出一个符合他本性的事件——激励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本身必须能够把他送上一条求索之路,令他达到生存的极限。”马特的命运从他出生便注定——为阿尔帕特隆提供心脏,让143岁的阿尔帕特隆继续活下去。这个限定的威胁中马特要展开顽强的活动,这种命运限定与个人意愿所造成的戏剧性张力使《蝎子之屋》主题意义深化。对于马特来说,如何看清并面对他作为克隆人的命运是《蝎子之屋》最大的悬念。
为了完成最大悬念的消释,完成马特的成长,作者设计了两个时空,一个是马特十四岁之前生活的阿尔帕特隆的“蝎子之屋”庄园,另一个是十四岁新生后生活的“蝎子之屋”浮游动物工厂。在作者的设定下,老阿尔·帕特隆有着怀旧情结,他的庄园刻意保持一百多年前的样子,这便产生了未来时空中植入历史的效果。而这两座“蝎子之屋”具有象征的意义,本身蝎子在《圣经》中就象征着仇敌环伺的恶劣处境,它们实现了某种同构。蝎子,是人们眼中狠毒、冷酷、无情的符号。蝎子是背叛,死亡,危险,痛苦,邪恶,仇恨和魔鬼的象征。这一切都是因为它致命性的尾巴。尤其是对于小动物和老弱病残的人来说就更可怕了。整个世界关于蝎子的传说都是和它那个长着毒刺,用于防卫的尾巴有关。在西藏和埃及,蝎子的护身符适用于避邪的。埃及的自然女神伊希斯就用一个巨型蝎子做保镖。通常,在古代,蝎子是用于看守通向冥界的大门的。单一只蝎子便如此黑暗,如果是一座蝎子之屋呢?“蝎子之屋”是困住人心、危险的象征,阿尔帕特隆是“蝎子”,蝎子之屋里所有视马特为牲畜的人是“蝎子”,浮游动物工厂的看守们是“蝎子”,那么马特呢?作为阿尔帕特隆的替代品,在一定境遇下也会表露出“蝎子之性”,比如他恶狠狠地向玛利亚索吻,他想向汤姆、罗萨、看守们报复的念头,但是正如情感意义上的“父亲”塔姆林告诉马特的那样:“当你小的时候,你能选择往什么方向成长,如果你善良正派,你就会成为一个善良正派的人。”这便清晰了,作者要与读者探讨的是“外表可以复制,灵魂不可复制”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是有宗教意味的塞利亚、玛利亚以及塔姆林帮助马特逃离了“蝎子之屋”,逃离了自己原来的命运,树立了“人”的概念,而不是变成一只“蝎子”。
如果说在“蝎子之屋”庄园马特还带着“命运”的紧箍咒,那么在翻越过阿约山之后,马特开始真正要一个人面对阔大、复杂、甚至有些危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完成“人”的确立。依然,他是被困在浮游动物工厂这个“蝎子之屋”里的。不像在“蝎子之屋”庄园,马特面临的危机是肉体的“心脏”随时要被拿走,在浮游动物工厂,马特精神上的“心”或者说“独立思考的能力”每天都在被侵蚀——被要求背诵“致力于国家繁荣昌盛是每个上进公民的美德”“资源产品的有序和人民大众的利益息息相关”“天道酬勤”等,马特上演了一场“肖申克的救赎”,解救自己的思想也解救其他童工的思想,完成自身的启蒙和他人的启蒙。当其中一个并置时空中的“蝎子之屋”被捣碎时,作家还牵挂另一个,所以她“派”马特回到“蝎子之屋”庄园,去“解放”那里的呆瓜,完成这个大团圆的结局。《蝎子之屋》的“归家——离家——归家”的框架结构也最终搭建完成。
作者的野心很大,想在《蝎子之屋》里展现出自己强大的结构布置、情节波折的能力,如果马特“新生”前,情节的跌宕起伏还让人充满期待的话,那后半部分因为要重新布置人物等,便常常产生情节快速起落的破碎节奏感,让人怀疑是不是作者最后急于脱稿,所以后面情节急转直下,才让整个故事草草结束。
在儿童文学领域,克隆人题材并不常出现,但是在成人文学那里,克隆人早已是“宠儿”。如果你读过不少克隆题材的科幻小说,会发现南希·法默的故事并未有多少新意。比如“外表可以复制,但灵魂不能复制”的主题早已在艾拉·莱文的小说《巴西来的男孩》(又名《九十四个小希特勒》)里有探讨。泰国作家维蒙·赛尼暖的科幻小说《克隆人》获得了2000年东盟文学奖,内容为亿万富翁坡楼敏和西方科学家斯宾塞合作,在自己的壮年时代,利用自己的体细胞,培育出克隆人启万和傲拉春,在自己衰老后,移植他们的器官来保持青春,这简直和《蝎子之屋》阿尔帕特隆的想法如出一辙。小说中的克隆人和正常人一样生活、恋爱、信教……但却被当作实验用的动物一般对待,这与马特的境遇也颇为相似。电影《逃出克隆岛》当林肯6-E明白自己的生活其实一个巨大的谎言,他们都是被克隆组织控制的克隆人,他们存在的意义只是为本体提供新鲜健康的器官时,他选择逃离克隆岛,并救出克隆岛上的所有居民,这与《蝎子之屋》的结构也有类似之处。克隆题材特别吸引女性科幻作家的兴趣。有分析说这可能和妇女一直执行着生育过程有关。相比男性作家,女性作家更喜欢讨论伦理道德问题,男性作家的克隆小说则较少伦理思考,他们主要是用这种题材丰富作品的惊险性和刺激性。
在纽伯瑞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中,《蝎子之屋》毕竟开拓出自己的一条“克隆人”题材的道路,让克隆人马特在充满敌意同时又喧嚣纷乱的世界里努力探求生存的权益和自我的价值。作家成为主人公的“心灵虫”,让小读者们看得过瘾,不能自拔,跑到南希·法默的官网上与她讨论情节与人物,还有什么比这个还能让作者高兴呢?作为大读者,我对作者仍有更多期待——《蝎子之屋》在艺术上并不完美,在结构和情节上跌宕起伏不能过度,把握好讲故事的节奏,让故事更加自然。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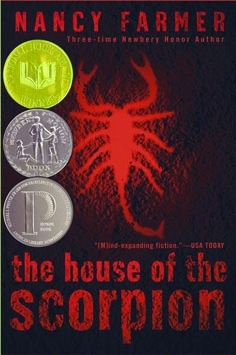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