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之大——西南联大与士人精神》聚焦中国远征军中西南联大学子的身影,展现联大教授议政参政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精神,厘清联大教授与各党派的关系和纠葛:穆旦翻越野人山,闻一多喋血西仓坡,张伯苓晚景凄凉,钱端升神情落寞……历史困境中的西南联大人,最后的命运令人唏嘘不已。
西南联大“学二代”
在两次入缅作战的热潮中,联大教授的“学二代”也纷纷参军,或当译员或任驾驶兵。联大三位常委正在读大学的儿子都率先做出了榜样:张伯苓之子张锡祜早已成为空军飞行员;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和蒋梦麟之子蒋仁渊都志愿去参战部队当军事译员。不仅如此,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之子查瑞传,任参战汽车部队驾驶兵。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之子冯钟辽,去参战部队当军事译员。
联大教授在讲坛上是大学教授,在家庭中,是儿女的父亲。我们从下面两个细微的生活场景来看父子两代联大人。
据李钟湘回忆,联大外文系助教杨西昆抱着儿子教大一英文,非常叫座。联大教授李继侗任生物系主任,他的儿子也在生物系求学,但是有一次,他的儿子参加年度考试,李继侗批卷给他一个不及格,让他补考。
冯友兰书赠时在云南大学执教的施蛰存一条幅:“鸭绿桑乾尽汉天,传烽自合过祁连;功名在子何殊我,惟恨无人先着鞭。”这首诗言明陆游“扫胡尘”、“靖国难”抗击侵略者之心曲,书录给好友,寄寓了冯友兰对抗日的爱国之情,也代表了联大教授的心声。当战时形势危急需要联大“学二代”从军时,他们又毫不犹豫地把儿子送到前线和战场。
不仅联大的“学二代”,当时整个文化学术界的“学二代”,大多有从军的经历。联大哲学系的熊秉明是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的公子,后来成为国际著名的美术家和艺术学家、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当时他也弃学从军。联大学子陶渝生,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陶孟和的公子,当时也和同学一起当军事译员,他的母亲沈性仁在抗战期间因为疾病得不到治疗而病逝,联大教授金岳霖曾写文章悼念。
梅贻琦四个女儿中,除了长女出嫁,四女尚幼外,在联大读书的二女、三女都在1944年“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从军运动中报了名,他们的带头作用在西南联大一时传为佳话。
联大学子从军,不仅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也亲身体验到政治的腐败。军委会外事局昆明办事处赖某私刻图章,冒领译员薪津70余万元,亏空公款 30余万元,致使西南联大到远征军做译员的同学不得不向美军朋友借钱。
联大历史系刘崇鋐教授也送子参军,但获悉天之骄子在军队中的遭遇时,同情以致泪下。据1946年出版的《联大八年》记载:
刘崇鋐先生,前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待人和蔼可亲,教西洋近代史,他的参考书目中有《联共党史》,这也许在旁人会引为奇怪的。刘先生热忱爱国,昆明有什么关于政局的讲演,是他常去听的。前次知识青年从军,刘先生送了自己的孩子去入营。可是后来在欢迎从军同学返昆席上,刘先生致词,当他说到这批青年人所受到政府的待遇时,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尽管目睹和体验到军队中的黑暗,但联大学子依旧投笔从戎,为抗战做出的贡献,彪炳史册。
美国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战区的战绩,美国总统于1945年7月6日预立指令(1946年5月14日公布),授给做出卓越功绩的人员以铜质自由勋章(由于当时通讯不畅,很多人未能收到勋章和证书),名单共有三百余人,上自傅作义等高级将领,下至军官和技术人员和军事翻译员。在52名受奖的翻译官中,有西南联大学生16人:钟香驹、冯钟辽、许芥昱、林龙铁、卢飞白、马维周、程道声、李乃纲、李益琛、刘厚醇、梅祖彦、蔡国谟、邹国奎、左永泗、王蜀龙、姚元。他们代表着西南联大所有从事翻译员工作的同学获得了这项荣誉,这也说明了军事翻译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作用。
获得铜质自由勋章的联大学子,后到美国留学,有不少在美国定居,成为各个领域的专家、教授。冯钟辽于1945年西南联大肄业后,到美国留学并长期旅居,成为工业锅炉方面的专家。许芥昱、卢飞白等将联大的诗韵带到美国,他们两人都在美国著名的高校执教。
近年来,以远征军为题材的文学和影视作品颇受关注。一段湮灭在烟云中的历史被钩沉出来,在历史教科书中不曾记载的中国远征军,渐渐浮现在今人的视野。有不少人去滇西和缅甸寻访远征军的足迹,当一轮明月当空照之时,凭吊战场,在战争的铁与血之间,伫立着联大“学二代”的身影。
驼峰“生死线”
从地上来的,从地上打回去!
从海上来的,从海上打回去!
从天上来的,从天上打回去!
这是咱们中国人的土地!
这是咱们中国人的海洋!
这是咱们中国人的天空!
——赵瑞蕻在《一九四零年春:昆明一画像——赠诗人穆旦》
2010年,台湾女作家齐邦媛的回忆录《巨流河》,成为各大媒体评出的年度图书。在这部反映中国近代苦难的家族记忆史中,齐邦媛的恋人、空军飞行员张大飞在抗战胜利前夕牺牲,以身殉国。怀着保家卫国之志飞上蓝天的张大飞战功卓著,然而,他却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的来临。1945年,张大飞自陕西安康出击河南信阳日本空军,与敌驱逐机遭遇,在空战中中弹阵亡,年仅28岁。这位感动无数读者的军人,代表了抗日战争期间空军的形象。像他这样的空军飞行员,西南联大也有不少。
1938年9月13日,联大学子初次在美丽的春城听到了凄厉的空袭警报声。9月28日,九架敌机对准昆明疯狂地投下了炸弹,联大租来作为教职员和学生宿舍的昆华师范学校被轰炸。正如联大诗人赵瑞蕻在《一九四零年春:昆明一画像》一诗描述的:
绮梦破碎了!轰炸!轰炸!
敌机飞临头上了!——
昆明在颤抖,在燃烧,
不知从哪里冒出浓烟,乌黑的,
仿佛末日幽灵;叫喊声,
哭声,血肉模糊——
轰炸!炸死脆弱的诗句吧!
联大诗人发出愤怒的呐喊,“从天上来的,从天上打回去!”于是,在 1939年至1942年,西南联大有一股报考空军飞行员的热潮。当时,日寇占尽空军优势,我国空军飞行员牺牲者甚重,当局决定在大学生中招考飞行员。许多联大学生勇赴国难,踊跃报考,有12人被录取:1941年录取戴荣钜等 11人,1943年录取1人。他们走进昆明巫家坝空军航校大门时,大门两侧的对联写道:“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被录取的联大同学们都清楚地意识到,这将是他们英勇报国的开始。
经过短期飞行训练后,联大出身的飞行员又先后到美国继续接受各种飞行训练,包括初、中、高级的教练机飞行训练,和毕业后的作战飞机训练,为期不到一年(学习七个月,见习三个月)。
戴荣钜等人在美国受训期间,他在美国写的一封家书,可以知道这批联大出身的空军飞行员的所思所想:“九日起开始飞P-40。一千二百马力之大飞机,我也能飞翔自如,我自己都不会想到。今生不虚。三个月见习完了,我希望能尽快回国。”飞行员在美国受训,花费不菲,“平均每人(不失事)之教育费约美金十万。如失事,赔偿照算。如此数万万美金的贷借需要多少桶桐油、钨砂、生丝、茶叶来抵还哪。”当时国民政府靠出口桐油、钨砂、生丝、茶叶来换取美金,此项协议是由中国驻美国大使胡适签订。戴荣钜觉得花费了国家大量的资金,于心不忍,更加激发出责任感,“非努力奋发不可”。在美国,感受到工业的发达,意识到祖国的差距,受训的飞行员们更是“卧薪尝胆,闻鸡起舞”。从这封战时的家书中,可见联大出身的飞行员的家国情怀和爱国精神。
他们经过国内外训练后分批回国参战,和美国盟军飞虎队一起痛击日寇陆空军。12人中牺牲者有5人:
戴荣钜,1939年考入地质物理气象系,受训归来编制在湖南芷江的空军第五大队,1944年6月在长沙与敌机作战时殉国。
王文,1941年考入机械系,受训归来编制在陕西安康的空军第三大队,1944年8月在保卫衡阳战役中与敌机作战时殉国。
吴坚,1939年考入联大先修班,1940年入航空系,受训归来编制在陕西安康的空军第三大队,1945年初在陕西与日寇飞机作战时殉国。
崔明川,1941年考入机械系,1943年在美国受飞行训练时,失事撞山殉国。
李嘉禾,1940年转学入物理系二年级,1943年在美国受飞行训练时,不幸失事殉国。
据马豫《缅怀在抗日空战中牺牲的联大人》一文载,戴荣钜牺牲后,他所在的空军中队给其兄发来抚恤公函,大队长也给烈士家属写了慰问信。抚恤函全文云:
荣钺先生伟鉴:
抗战军兴群情奋发,令弟荣钜爱国热忱,投效空军服务本大队,其志殊为可嘉。不幸于本年六月随队出发,在长沙空战,壮烈殉国,实属痛惜。除报请航委会从优抚恤外,特函唁慰。希转达令翁勿以过悲为盼。
戴荣钜、王文、吴坚三人的名字没有刻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从军学生名单中,但他们的姓名、出生年月和牺牲地点,锈刻在了张爱萍将军题名的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纪念碑上。
在1944年应届毕业生被征调时,外文系彭国涛去美国十四航空队,经济系熊中煜去史迪威炮兵司令部,电机系孙永明去缅甸孙立人军中当翻译。中国航空公司(CNAC)招考飞行员,西南联大学生应考被录取者有11人。他们经过短期训练后,即参加举世闻名的飞越驼峰航线的运输任务,担任副驾驶员穿梭来往于中印之间。中国航空公司的主驾驶员多为“飞虎队”的飞行员转过来的,所以中国航空公司被称为驼峰航线上的“飞虎队”。
驼峰航线的运输线沿线气候条件恶劣,并且为避开缅北日机的袭击,不得不在没有无线电导航台和明显地标的航线上进行夜间飞行,因此飞机常常失事。联大学生朱晦吾和沈宗进就由此因公牺牲。
朱晦吾,1940年考取西南联大外语系,但申请休学,1942年始入学,1944年征调考入中航公司为副驾驶员,开始在“驼峰航线”担任空运飞行,在“驼峰航线”上遇难牺牲。
沈宗进,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机械系,1944年征调考入中航公司为副驾驶员,开始在“驼峰航线”担任空运飞行,在“驼峰航线”上遇难牺牲。
此外,据戈叔亚和王春琪撰写的《驼峰航线上的中国航空公司》文,并参照《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其他九位出身联大的中国航空公司飞行员如下:
华人杰(1922--2001),生于江苏省无锡,抗战时期在重庆南开中学就学,1944级西南联大机械系毕业生。1945年,中国航空公司急需驾驶员,从事“驼峰空运”工作后加入中国航空公司,担任副驾驶,在“驼峰”上飞了96个来回。
周炳,1920年生人,籍贯湖南长沙。战争爆发后考入浙江大学,后转入昆明的西南联大政治系。1944年报考中航公司,担任运输机飞行员。在“驼峰航线”运输空中物资一百三十多个来回。战后在中航开国际航线,后参加“两航起义”。
邓汤美(邓庆泉),原来西南联大1944级外语系学生,后考入中航公司为副驾驶员,长期驾驶道格拉斯公司生产的两台活塞式双速坛压航空发动机的DC-2、DC-3客机和C-47货机,在“驼峰航线”担任空运飞行。1945年留美,1947年回国继续在中航公司飞行并参加“两航起义”。
萧福霈,抗战初期在省立杭州高中就读,然后考入西南联大化工系,1944年级,后考入中航公司为副驾驶员,开始在“驼峰航线”担任空运飞行。
陈仁炱,原来西南联大1944级机械系学生,后考入中航公司为副驾驶员,开始在“驼峰航线”担任空运飞行。
陈启蕃,原来西南联大1944级航空系学生,后考入中航公司为副驾驶员,开始在“驼峰航线”担任空运飞行。
冯少才,原来西南联大1944级土木系学生,后考入中航公司为副驾驶员,开始在“驼峰航线”担任空运飞行。
罗道生,原来西南联大1944级机械系学生,后考入中航公司为副驾驶员,开始在“驼峰航线”担任空运飞行。
谭申禄,原来西南联大1944级机械系学生,后考入中航公司为副驾驶员,开始在“驼峰航线”担任空运飞行。
联大的屋顶是低矮的,但培育出了众多大师,也培养了冲向蓝天翱翔的飞行员。有的牺牲殉国,英烈碧血洒长空,有的成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骨干。我们不应忘记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赤胆忠魂,功昭日月,永励后人。
远征军的非人生活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穆旦《森林之歌——祭野人山死难的兵士》
穆旦,原名查良铮,出身于浙江海宁查氏名门,生于天津,与联大教授查良钊、现代武侠小说大家金庸(查良镛)是同族兄弟。他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就有文章发表,后考入清华大学,随校南迁至长沙,又至昆明。
1940年8月,穆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留校担任外文系助教。是年7月,日本侵略者侵占安南,原来是大后方的云南一下子成为前线。
1941年3月初,24岁的穆旦胸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志,参加中国远征军,任远征军副司令部杜聿明的随军翻译,出征缅甸抗日战场。
穆旦放弃西南联大的教席而从军行,并非冲动之举。他在联大毕业之初,就对一位同学说过“国难日亟,国亡无日,不抗战无法解决问题,不打日本鬼子无法消除心头之恨。”穆旦从军的动机还有个人方面的因素:“校中教英文无成绩,感觉不宜教书;想作诗人,学校生活太沉寂,没有刺激,不如去军队体验生活。”
进入缅甸不久,远征军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仅率一个团在仁安羌与七倍于己的日军作战,成功救出被困的7000名英军以及500名传教士、记者,英国朝野为之震动。
可惜,仁安羌大捷后,盟军内部出现了矛盾,战区总指挥官美国的史迪威将军与远征军副总司令杜聿明为指挥权争执不休。而此时,曾导演了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英军统帅亚历山大又自作主张向印度方向撤退。盟军在贻误战机,而日军五十六师团(日军精锐师团,是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在几天之内完成了迂回缅北的千里奔袭,切断了盟军的退路。
见通往中国的退路已断,史迪威随英军撤往印度,而蒋介石为保全实力则令杜聿明带队回国。此时杜手下有6万大军,日军不到1万人,杜聿明听从蒋介石指示,没有殊死一搏,也没有向更有利的印度方向撤退,而是带着部队向日军未设防的胡康河谷、野人山一带撤退。
此时,穆旦已被编入了二O七师,做师长罗又伦的随身翻译,而二O七师也参加了自杀性的殿后作战。子弹、炮火和死亡早已让穆旦忘却了诗歌,他的战马被炮火轰倒,传令官也中弹身亡。日军像发疯的野兽一样地追击他们,神秘、凶险、前途莫测的原始森林,埋伏着重重危机,仿佛在说:“欢迎你来,把血肉脱尽。”穆旦虽然在日军的追击下逃脱,但前方等着他的却是一片人间地狱。
战事失利后,随军从野人山撤往印度的女战士李明华,在回忆录《野人山余生记》中写道:
自从(民国)三十一年5月初,在缅北一个不知名的大村落中,全体官兵,奉军部命令,毁掉全部重武器、装备和车辆,开始徒步进入布满原始森林的山区,从此补记全部中断,全凭个人谋生。初时队伍还能像蚂蚁队伍一般,一个接一个前进,几天后,渐渐分散,成为三三两两的散兵游勇了。断粮半个多月,人人饥饿疲惫不堪……很多官兵因饥不择食,吃了有毒的野菜而丧生。
除了饥饿,还有更大的威胁——缅甸的雨季。在原始森林行军,暴雨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杜聿明写过一篇《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记录了惨痛的经历:
各部队所经之处,都是崇山峻岭,山峦重叠。野人山及高黎贡山,森林蔽天,蚊子成群,人烟稀少,给养因难……自六月一日至七月中,缅甸雨水特大,整天倾盆大雨,原来旱季作为交通道路的河沟小渠,此时洪水汹涌,既不能渡河,也无法架桥摆渡,我工兵扎制的无数木筏,皆被洪水冲走,有的连人也冲没。加以原始森林内潮湿特甚,蚂蝗、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爬虫到处都是。蚂蟥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一个发高烧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蟥吸血,蚂蚁啃啮,大雨侵蚀冲洗,数小时内即变成白骨。官兵死亡累累,前后相继,沿途白骨遍野,惨绝人寰。
在热带的暴雨下,在阴暗死寂的胡康河谷,穆旦迷了路,和部队失去了联系。那一刻,死亡的阴影时刻笼罩着这位联大的诗人,已经接二连三目睹战友倒下之后变成白骨,对死亡的恐惧渐渐麻木。渺小的个人,身陷原始森林中,只剩下生的本能。他的腿肿了,全身疲劳,随时都可能倒下,但求生的意志告诉他,只要倒下,他就成为森林中野兽和蚊虫的食物。更可怕的是,穆旦患上了疟疾,好在他手中有杜聿明撤退前给他的两颗药片。凭着这两颗宝贵的药片,穆旦以强大的意志,慢慢逼退了死神的阴影。可是,随之而来的是令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达八天之久,但是这个生命力极其顽强的年轻人,这位在联大受人尊重的诗人,在他失踪了两个多月之后,居然从“地狱中生还”。瘦弱的诗人穆旦走到了队伍的集结地印度。
在印度,穆旦又差一点死去;长久的饥饿,使得吃得过饱也足以致命。经历如此严峻的考验,经历过野人山九死一生的煎熬,战争在这个诗人的心灵上留下了永远的创伤,也播下诗歌的种子。从此之后,穆旦就像换了一个人,变得沉默寡言。开朗的笑容,像昆明灿烂阳光一样的笑容,在他脸上消失。联大好友相聚,很多人都非常佩服他翻越野人山的经历,“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但他从不开口谈。据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只有一次,被朋友们逼得没有办法了,他才说了一点。而就是那次,他也只说到他对大地的惧怕,原始的雨,森林里奇异的,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长,而在繁茂的绿叶之间却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腐烂的尸身,也许就是他的朋友的。还有一次,穆旦无意中曾跟人提及,他亲眼看到一位军人的尸体,只剩下一堆白骨,但是脚上仍穿着一双完整的军靴。
这是怎样的非人间的经历啊,我们无法得知。穆旦经过多少次的噩梦,经过多少次的遗忘,试图摆脱野人山的苦难历程,但这些记忆仿佛在他的思想里扎了根。在一个无法入眠的夜晚,穆旦饱蘸着一腔热血、满怀对死者的哀悼,写下了惊世之作《森林之歌——祭野人山死难的兵士》(后改名为《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于1945年发表,收录在《穆旦诗集(1939— 1945)》。这首“直面战争与死亡,歌颂生命与永恒的代表作”,一诞生就是经典。隔着六十多年的时光,我们仍能感受到诗人燃烧的灵感,带来灼热的温度,令人灵魂震颤。这首诗歌埋藏着一个时代青春与死亡的秘密,是联大学子从军这段历史的见证,是战争年代死去的和活着的人的哀歌,也是一个民族在战争烈焰中浴火重生的精神。
1977年春节之后,穆旦将饱含了后半生心血的译作和诗作,交给女儿,让她妥善保管,他觉得自己在有生之年看不到自己的作品出版了。“文革”结束,粉碎“四人帮”后,穆旦打算做骨折手术,却被告知一些手术工具好久没有使用过,还要整理。心情沉重的穆旦突发心肌梗塞,死在了手术台上。
1977年2月26日(农历正月初九)凌晨3时50分,在早春黎明前的黑暗中,中国失去了诗人穆旦。“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诗人一直穿行在无边的冬季,在改革开放的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刻,他的生命终止。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穆旦在生前肯定不会料到,他的身后赢得了无穷的赞誉和荣光,“一颗星亮在天边”,他的成就被得到公允的评价,他的译作和诗集被出版,在青年中广为流传。有了这些成就,不知饮恨而死的穆旦能否含笑九泉?
(本文摘自《大师之大——西南联大与士人精神》,刘宜庆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第一版,定价:32.80元)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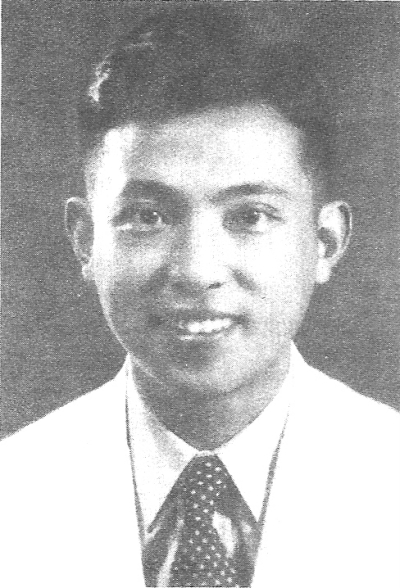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