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见美国在唱歌……”每一次读到惠特曼的诗,陆天明总会追问自己:你倾听中国在歌唱吗?你听见中国的歌唱了吗?你明白中国的歌声里所包含的那全部的感伤和沉重、幽思和期待吗?
他还喜欢惠特曼的另一首诗:“一只沉默而耐心的蜘蛛,/我注意它孤立地站在小小的海岬上。/注意它怎样勘测周围的茫茫空虚,/它射出了丝,丝,丝,以它自己之小,/不断地从纱绽放丝,不倦地加快速率。”陆天明说:“我愿意做这样一只文学的‘小蜘蛛’,去网罗、描画并放大‘中国的歌声’。”
陆天明曾在小学三年级里的作文《我的理想》中,表达过自己“要当作家”的志向。这个志向在此后的60年岁月里,从来没有动摇过。为此,他走过许多弯路,也真诚地放弃过自我,又曾极其痛苦地去寻回那文学创作中绝对不可或缺的“自我”。他也曾经受过许多质疑,甚至屈辱。但是,他仍然以一个“热血青年”的面貌出现在中国文坛,仍然无比真切地关注并全身心地融入这个时代。
今年1月,花山文艺出版社推出《陆天明反腐四部曲》精装珍藏版,包括读者所熟悉的《省委书记》、《苍天在上》、《大雪无痕》、《高纬度战栗》。他始终认为,一个作家和一个民族的文学创作,真正成熟的标志应该是既被自己的人民认可,又在文学史的进程中有创造性的突破。中国的文学产生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又要让它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它能够发挥也应该发挥的作用,就不能回避大众的阅读接受程度。这套书的再版,再次证明和时代紧密结合、替老百姓说话的文学,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当然,前提是它一定得是“文学的”。
读书报:《苍天在上》等作品出版这么多年,依然有读者喜爱。您认为作品具有生命力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陆天明:原因很多。但作品本身关注了时代、社会、历史的发展,尤其比较真切地表达了社会时代和人民的需求是最主要的。“真切表达”这四个字,本身就有艺术含量,同时有社会认知的含量。很多伟大的作家干预社会,参与变革。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还有狄更斯、陀斯托耶夫……所有伟大的小说都关注社会、时代和民众,并且有很高的文学含金量。当时写反腐败小说的时候,我也没想到20年后这仍然会是中国的重大问题,而且越来越重要。中国要发展,还要在反腐败上扎扎实实走一步,抓住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问题,表达人们要过好日子的基本愿望。另外,我的作品之所以在这么多反腐小说里还有一席之地,就是有一股正气,除了文学的因素外,有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上世纪80年代到1995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黄金十年,但不能否认的是,它又强烈地受到西方所谓的现代或后现代文学理论的影响,觉得文学不能和社会政治挂钩,小说只要一涉及社会问题便不可能是好小说。有些人更认为文学只能关注自我,只能向作家的内心走,甚至有一段时间,文学还只强调形式美,在语言表达上体现小说自身价值。不再注重写什么,只关注怎么写,这就本末倒置了。再比如说,大学里出现“后现代”、“解构”,中国连现代都不是,正在结构,怎么能适用这个理论?生搬硬套西方的创作理论势必影响到本土的创作思想,主观愿望是要纠正文革遗留的极左文艺思潮,强调作家找回自我,强调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和人性化,这是非常必要的。但在某些人那儿,泼脏水的时候把小孩子一起泼掉了,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把文学与社会和时代完全隔离。提倡只面对自我,而不再关注社会和现实,把文学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自我圈子里,远远地脱离开社会和时代,这样的写作不可能走远。为此,一些作家写到四五十岁就枯竭了,再也不出好作品了。所以我曾经说过,作家和文学回归自我是非常必要的,但在实现这第一次回归后,还得进行第二次回归,那就是回归到一个包孕天下、实践匹夫之责的大我上去,对一个作家来说,是更加重要的事。
读书报:您后来转向“反腐小说”的写作,是出于怎样的原因?
陆天明:我曾经两次上山下乡,应该是最早写知青题材的作家。四幕话剧《扬帆万里》是文革开始最早的知青题材,后来的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被国外研究知青文学的专家评价为是“中国知青文学的第四块里程碑式的作品”,描写了知青理想的泯灭,很尖锐。而那时候,我想走所谓的“纯文学”的路子,并不是一开始就意识到作家还应该有贴近现实的使命。那时候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北京电视台拍了几部反映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编辑部的故事》等,都打响了,我当时所在的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便也想搞一部现实题材的作品。我当时就意识到反腐败是很重要的题材,就报了上去。但那会儿,没有故事也没有人物,也没有梗概,但是题目有了,就是“苍天在上”。当时就想替老百姓呐喊一声,这是多年来埋在心里的。
《苍天在上》出版后,立即火了,据说全国各地书店去上海文艺出版社要书的人,把柜台都挤倒了。同名电视剧播出后,收视率最高时达39%,每集电视剧播完,我家的电话铃声就响了,各地观众来电话和我讨论剧情。天天如此。这强烈地触动了我,让我感触到,如果你替百姓说话,百姓会给你回报,文学就是要当百姓的传声筒。
读书报:这些作品在当时都是非常敏感的题材,出版是否出遇到一些困难?
陆天明:当然要遇到各种困难。要闯禁区。比如,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能不能呼唤苍天?单是“苍天在上”这个题目就有争论;反面人物能不能写到副省级?一号英雄人物能不能有不好的结局?等等。这其中的幺蛾子太多了。《苍天在上》写了五个半月,为该不该拍摄,却争论了五个半月。过程中差一点被禁了……最后争取到顺利播出,才松了一口气。像《苍天在上》和《大雪无痕》的电视剧在播出前没有人为它做任何一点宣传和炒作,都是默默地播出,完全是在播出过程中火的,是靠观众的嘴和心把它们炒火的。这一点,现在来说,既让我自豪,也仍有一点心酸。
读书报:同样是写官场,您的作品称为“主旋律”被大力弘扬,但是也有很多被贴上“封条”。
陆天明:实事求是地说,有人说它是“主旋律”,但基本没有人大力弘扬它们。评论界一直保持沉默。“大力弘扬”它们的只有读者和观众。对于主旋律,有人质疑,也有人蔑视。主旋律是一种客观存在,任何历史阶段都有其主要的历史使命。表现一个民族和人民为实现这个历史使命和主要生存状态的作品就是我们所说的“主旋律”了。每个历史阶段都应该有这样主调式的作品,比如在抗日时期,当然不能只有沈从文张爱玲式的作品,必须要有《黄河大合唱》那样的主调和主旋律。现在有反腐作品,也有一种叫官场小说的作品。反腐小说和官场小说质的区别在于是不是“反”腐。严格说,一个是写怎么反腐的,一个是写怎么腐败的。我历来认为,反腐或揭黑题材的作品都能成为很好的小说。关键看作品里到底有多少精到的文学元素。
读书报:写反腐小说,好像很少有人像您这样还深入生活去采访。
陆天明:写《苍天在上》时没敢下生活,担心被采访者会对号入座。偏偏这部作品有一个大的巧合,书中描写的案子和陈希同的案子相似。这大概也是这部作品当时会轰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多人问我是否事先知道陈希同要出事?我当然不知道。也不可能让我知道。之所以相似,完全是因为对平时积累的生活素材进行了分析和提取。《大雪无痕》和《省委书记》写得更艰难,这两部作品是下生活写的。因为题材敏感,下生活就受到阻力。甚至很大的阻力。但你要贴近现实,就得下去生活,把握生活的脉络,感受社会和人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也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习惯:每每写完一部作品,就要看几本书,找机会到生活中去走一走,呼吸“新鲜空气”。
真正的作家伟大的作家一定要参与到国家民族的变革中去。不参与进去,凭什么要人民尊奉你为作家?否则就只是文字匠。90年代中期后中国文学一度出现萎软苍白的根本原因,就是那会儿文学越来越脱离人民了。
读书报:一方面,读者希望读到您的作品,但是我也在考虑,毕竟有些是20年前的作品,当时描写的腐败现象和现在是否有很大的差别?现在重版,还能说是贴近现实吗?
陆天明:不能狭隘理解文学艺术的“贴近现实”。文学艺术不是新闻报导。不可能只写昨天发生的事。它的贴近,是本质上的,不只时间上的“近”。腐败手法和反腐手段一定会有变化,但我们写反腐小说,主要不是靠腐败和反腐的手段来吸引读者。也不应该只靠这些东西来卖钱。文学作品不是反腐报告。作家应该提供给读者对人物形象和对社会深刻剖析的优秀作品,有独到的语言表达和思想亮点。这些对于一部反腐作品才是最重要的。
读书报:相对于作品的影响,评论界的关注似乎不够。您介意吗?能否告诉读者,您要写的作品是什么?
陆天明:说完全不介意是假的。但真的无所谓了。评论界不关注优秀的反腐文学创作,只能说明他们不称职,他们的苍白。再说,评论界不关注又能影响什么呢?现在又有多少人会关注中国的当代评论呢?有一位政治家对我说过:天明,你的创作只要对得起历史对得起人民就足矣。时间将证明一切。我现在只有一种紧迫之感,还没有写出自己最满意的东西,还不能放下笔。我想写“中国三部曲”,写出中国人这三十年的生存感受。我希望在文学上总结自己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教训,总结九部长篇的心得,也把我这一生的社会纠结、挣扎和体验写进去,最好能够写出十三亿人的生存感受。我现在只想问自己:陆天明,你能做得到这一点吗?趁你还干得动的时候,好好干吧!(本报记者 舒晋瑜)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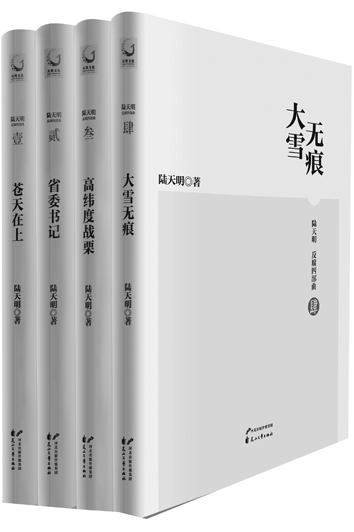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