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传记固然要尊重相关史料,就此加以生发铺叙,同时也可以有些虚构的故事和人物语言;否则仅仅罗列碎片,就不成其为传记,可读性也差,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发挥不了太大作用了。
问题在于,这里虚构的尺寸不宜太大,过大就成为小说,而非传记了。传记和小说写法大不相同,让我们举例来说明之。
关于曹植和他的嫂子甄氏之间有无恋情一事,有一个古老的传说,略谓:
魏东阿王(按指曹植)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缕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时已为郭后谗死,帝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赉植。植还,度轘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遂用荐枕席。欢情交集,岂常辞能具?为郭后以糠塞口,今披发,羞将此形貌重睹君王尔。”言迄遂不复见。所在遣人献珠于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文选·洛神赋》李善注引《记》)
后来论及《洛神赋》时,颇有学者认为洛神就是影射甄氏。此事虽查无实据,而事出有因,足备一说。所以,到《曹植传》(王玫著,中华书局2012年第一版)一书中大写曹植与甄氏感情瓜葛的来龙去脉,起伏跌宕,艳丽多姿,虽然大有爱情故事之意,却是传记文体可以允许的。人是真人,故事亦渊源有自,且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所以不妨如此这般。
《三国志演义》是家喻户晓的历史小说,其中虚构的尺度就相当大了,例子举不胜举,即以后来又改编为戏剧的蒋干盗书来说,就同历史记载完全不同。
历史上的蒋幹完全是一个正面的形象,绝无跑到老同学那里去盗窃机密文件之事。《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载:
初曹公(操)闻(周)瑜年少有美才,谓可游说动也,乃密下扬州,遣九江蒋幹往见瑜。幹有仪容,以才辩见称,独步江、淮之间,莫与为对。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诣瑜。瑜出迎之,立谓幹曰:“子翼良苦,远涉江湖为曹氏作说客耶?”幹曰:“吾与足下州里,中间别隔,遥闻芳烈,故来叙阔,并观雅规,而云说客,无乃逆诈乎?”瑜曰:“吾虽不及夔、旷,闻弦赏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为设酒食。毕,遣之曰:“适吾有密事,且出就馆,事了,别自相请。”后三日,瑜请幹与周观营中,行视仓库军资器仗訖,还宴饮,示之侍者服饰珍玩之物,因谓幹曰:“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假使苏、张更生,郦叟复出,犹抚其背而折其辞,岂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终无所言。幹还,称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间。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
真实的蒋幹与读者观众相当熟悉的那个自作聪明、业余充当间谍的小丑相去绝远,他来见周瑜确实是当说客的,但当他发现对方“非言辞所间”,就“终无所言”,回去复命——他知其不可而不为,不失名士风流,声誉丝毫不受影响。这同《三国志演义》以及三国戏里的那个鼠窃狗偷而中了圈套的小丑蒋幹几乎毫不相干,所以“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三国志演义》作者的想象力和叙事技巧非常值得佩服,他是在写小说;如果写传记,就绝不能这样处理。
王著《曹植传》引出了不少曹植的诗歌,其中给这些作品安排的写作背景,有些是没有直接的史料依据的,但处理得颇合情理;那些作品的系年,本来就是曹植研究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即使有专家给它们系过年,也只是推测,并非定论,那么在传记里根据情理暂拟些写作背景,应当也是文学传记许可的。如果是写小说,即使帮曹植新写一点作者认为有必要的诗篇,我以为也未尝不可——既然小丑蒋幹可以无中生有,然则来一点无中生有的曹植诗,也只是小菜一碟。
这就是虚构的尺度不同。这两种尺寸,掌握起来各有各的难处,也各有巧妙不同;如果处理得好,并无高下之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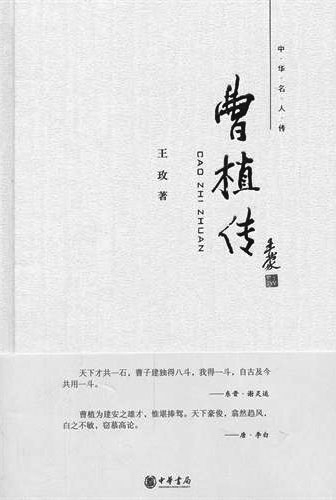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