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霍布斯鲍姆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头衔享有盛名。他终其一生未改政治信仰,是始终不渝的共产党员。这是他个人的选择,并最终成为他的宿命,影响他的学术及个人生涯。他在临死前说,希望死后人们会这样记住他这个人:“这是一个始终高举红旗并不断挥舞的人。尽管他只不过写了几本读起来趣味盎然的好书,他还是有所建树的。”
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于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在伦敦去世,享年95岁。霍布斯鲍姆生于俄国十月革命的1917年。他一生信仰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头衔享有盛名。作为共产党人,霍布斯鲍姆可谓生逢其时,一生目睹共产主义的兴衰,目睹苏联成为超级大国,然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迅速崛起。在漫长的一生中,他也看到自己一生致力批判的资本主义世界在20世纪末及21世纪初似乎走上没落的不归路。但同时他也目睹了苏联的解体——冷战以西方的胜利而结束。作为一个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的历史学人,其人生和学术经历可谓相得益彰,珠联璧合。作为历史学者,他以“时代四部曲”闻名一时,即《革命的时代》、《资本的时代》、《帝国的时代》及《极端的时代》。学术著作与其精彩人生互相印证,也因此成就了可以称之为霍布斯鲍姆的时代。但令人可惜的是,如同跌宕起伏的20世纪一样,霍布斯鲍姆的个人时代也充满着“宿命”。他的人生轨迹固然充满传奇,但同时亦受到“宿命”的巨大制约。
一
要明了霍布斯鲍姆的个人时代及宿命,我们必须要回顾他奇特的人生经历。霍布斯鲍姆出生于一个犹太人家庭。其父为英国人,母为奥地利人。由于出生时父母在埃及谋生,霍布斯鲍姆实际上出生在埃及。他的父母在其年少时即相继离世,从而使他在很长一段时间过着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生活。除埃及外,他先后在维也纳、柏林的亲戚家度过了童年及少年时代。1933年希特勒上台,施行排斥犹太人的政策,迫使当时生活在柏林的16岁的霍布斯鲍姆再次迁离,来到伦敦,寄住在伯父家。少年的经历,特别是在德国的经历,彻底奠定了他一生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在青年时即成为共产党员的漫长人生的基础。这种年轻时即成为共产党员并始终没有脱离党、没有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的经历,成就了霍布斯鲍姆,也成为其终生的宿命。1933年回到伦敦后,霍布斯鲍姆由于聪明好学,自称参加考试如同吃冰淇淋一样令其享受,结果获得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并先后在此完成学士及博士学位。由于他对社会、政治的浓厚兴趣,历史研究当然成为他终生的职业。
在英国20世纪杰出学者中,有不少人是共产党员,信仰共产主义。如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E. P. Thompson、Christopher Hill,著名学者John Saville、Raymond Williams都曾经是英国共产党员,并在自己的领域作出重大贡献。就个人来讲,Raymond Williams的《关键词》(Keywords)一书虽出版多年,迄今仍是我的案头常读之书。但是这些人与霍布斯鲍姆不同的是,他们大多在1956年后脱党,摆脱政治包袱,潜心学术。而霍布斯鲍姆终其一生未改政治信仰,是始终不渝坚信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英共实际上在上世纪90年代解散)。这是他个人的选择,并最终成为他的宿命,影响他的学术及个人生涯。
由于政治原因,霍布斯鲍姆一直未能成为他心向往之的剑桥大学教授并跻身英国最高学术殿堂。从1947年初出茅庐到1982年退休,他一生都在英国伦敦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Birkbeck学院任教。当时的Birkbeck学院类似于中国的夜校或职工培训学院,学生大都来自工薪阶层,白天上班,夜晚上学深造。就是在这样一个三流学校,霍布斯鲍姆还熬了23年才晋升教授(1970年)。如果说是政治原因作梗导致其晋升不顺并为其学术发展拖后腿的话,应该是不错的。不过,霍布斯鲍姆本人至死都不承认这点,反而声称他的学术声誉受惠于他的政治信仰及其共产党员身份。他若不是那种“鸭子死了还嘴硬”的性格,就是有他人所不知的背景。遗憾的是他现在已“见马克思”了,已无法与之进行进一步的对证。
霍布斯鲍姆在写于2002年的自传里承认,因为他的政治背景,他在学术研究上一直回避20世纪。由于他对俄国十月革命的终生崇拜以及强烈的共产主义观点,他害怕他的有关20世纪的学术研究会被人打上“政治说教”的烙印及标签。可能由于此种原因,霍布斯鲍姆花了差不多一辈子的心血研究“漫长的19世纪”。他的“时代四部曲”中有三部是关于19世纪的。《革命的时代》集中研究由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848年欧洲革命的历史,出版于1962年。《资本的时代》则着眼于1848年到1875年西方资本主义大规模上升及扩张的历史。《帝国的时代》是研究1875到1914年间的历史,于1987年出版时霍布斯鲍姆已正式退休好几年了。该书主要解释西方是如何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时代四部曲”的第四部,即《极端的时代》,到1994年才出版。这本书终于回到霍布斯鲍姆自己生活的时代,一个他在学术研究上不敢深入的时代。《极端的时代》描述1914到1991年的历史,同他用鸿篇巨制写就三部曲来研究“漫长的19世纪”相比,这第四部可谓其“极短的20世纪”的不对称的成果了。这难道不是宿命吗?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霍布斯鲍姆在2002年出版的自传Interesting Times当作他有关20世纪的另一部著作。在这本精彩纷呈的回忆录里,霍布斯鲍姆从个人角度描述20世纪如何成为人类历史中最特殊也最令人恐怖的时代。这部自传堪作他“时代”系列的第五部。自传的全名是Interesting Times: A Twentieth-Century Life。霍布斯鲍姆在解释为什么要用此一书名时写道,他的灵感来源于中国的一个古老咒语。该咒语认为,有趣的时代总是有悲剧及动乱的成份。因此在他看来,这一书名可以很好地概括20世纪对其个人及其作为职业历史学家的双重魔咒的含义,这也是本文为什么用宿命作为切入点的主要动机。诚然,这里霍布斯鲍姆是诚实的。作为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个人角度他无法对20世纪的历史作一客观解释。但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专业历史学人,他又必然面对及审视伴随这一世纪而来的各种各样的残酷历史及现实,并加以学术判断。霍布斯鲍姆的纠结及矛盾心理甚至宿命由此而生。在撰写自传时,尽管他已八十多岁,他仍无法完全超越自我,超越自己的政治,公正全面地解释这一既属于他本人又属于人类的时代,以及两者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这难道不是宿命吗?
二
纠结也好,宿命也好,不幸也罢,霍布斯鲍姆并未因此出世或怨天尤人。他是一个善于积极入世并生活得多姿多彩的人。他一生寄情山水田园风光,喜欢电影,喜欢飞鸟,大有“天高任鸟飞”之概。他一生写了四十多本书,其中不少属于有关当代政治、文化的分析及社论。他是著名的Past and Present杂志的长期编辑及撰稿人。他还是文艺社团的发起人,并经常出现在各种媒体的采访中,侃侃而谈,说古论今。他也喜欢同三教九流各种人士交往,如政治上极其保守的历史学人Niall Ferguson就是他的朋友之一。他也喜欢喝酒,英式果酒(sherry)、 威士忌等都是他喜欢的杯中物。
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对各地革命情有独钟,关注有加。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即2011年,中东发生了“阿拉伯之春”,不少国家爆发革命。霍布斯鲍姆当然为之激动,为之欢呼,认为这些革命让他想到1848年的欧洲政治巨变,且有不少相似之处。他认为“阿拉伯之春” 如19世纪中期的欧洲革命一样,也是中产阶级成为革命的主要推动力。作为共产党人,霍布斯鲍姆在年轻时就对革命运动非常积极,把参加群众集会同性爱相提并论。他曾公开声称,除性爱之外,只有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才能让他达到身心俱悦的极度兴奋的地步。霍翁终其一生孜孜于改变世界,并非满足于躲在书斋撰写历史,而对自己创造历史心向往之。他在去世前一年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就叫《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故事》(How to Change the World: Tales of Marx and Marxism)。如果2011年他再年轻一点,他也许会立即背起行囊奔向中东,加入群众抗议示威之列!他甚至在临死前告诉同样也是历史学家的英国人Simon Schama 说,希望死后人们会这样记住他这个人:“这是一个始终高举红旗并不断挥舞的人。尽管他只不过写了几本读起来趣味盎然的好书,他还是有所建树的。”
霍布斯鲍姆多姿多彩的人生经历及心路历程,还体现在他一生十分钟爱爵士乐以至于达到痴迷的地步。大概孔子所谓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的感觉也不过如此,但此君可以达到一辈子“不知肉味”的境界!他爱听爵士乐,还化名长期在杂志上撰写爵士乐评论,并出版爵士乐评论专著。其见解独到,甚至使作为行家里手的专业乐评人都对之赞赏有加。有趣的是,此老对爵士乐感兴趣之初还有一番悲催过程。他年轻时自认长相奇丑,无法吸引异性。他曾在日记中这样描述19岁时的自己:个高,奇丑,无道德心,极其自私,虚荣且办事猥琐,不光明磊落,生性胆小怕死。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样的人走上江苏电视台的“非诚勿扰”节目征婚的话,24位佳丽恐怕会马上全部灭灯的。为了弥补自己貌丑及减轻对异性无魅力的痛苦,霍布斯鲍姆发现了爵士乐,感到爵士乐能帮助他缓解因性冲动而带来的身心煎熬,从而可以寄情于音乐而忘却自己是可怜的无异性问津的“丑小鸭”。等到他后来超越了自己因长相丑陋及缺乏对异性吸引力而自怨自怜的境界后,他发现爵士乐仍然与他的政治理念相吻合——因为爵士乐是大众文化的音乐体现,从而一生乐此不疲。读者诸君如对霍布斯鲍姆的爵士乐观点感兴趣,可以阅读他的《爵士乐境界》(The Jazz Scene)以及1998年出版的《不平凡的人,抵抗运动及爵士乐》(Uncommon People,Resistance,Rebellion and Jazz)这两本书,感受他的独到意境及音乐领悟力。
尽管幼年及青年时期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成为学者之后学术升迁又受到其政治信仰拖累,但霍布斯鲍姆无论在学术成就还是盖棺定论的世人评论及承认诸方面来说,都还是幸运的人。中国古人早就说过,一代良史要“才、学、识、德”四者兼备。霍布斯鲍姆的才、学、识是世人公认的。就是“德”方面,他实际上也是无可挑剔的。因为在西方封杀、批判共产主义时,霍布斯鲍姆从不人云亦云,对自己的政治信仰绝无动摇,至死不渝。这是何等的气魄和气概!尽管受到政治问题带来的消极影响,他还是取得了傲人的学术成就。这又是何等的了不起!霍布斯鲍姆的经历及成就告诉我们,可见意识形态的禁锢并非注定使一个人不能成为一流历史学家甚至一代宗师。
三
在西方学术界,一个历史学家要成为一代宗师一般要具备下述条件:第一是自立门派,成为某一学科或某一重要观点的创始人。如所谓法国年鉴学派的布劳代尔,美国建立近代中国研究的费正清等人。在这一点上霍布斯鲍姆没有做到。他不但不是某一学派的创始人,甚至他的基本观点都是属于别人,即马克思的。对霍布斯鲍姆更不利的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被认为过时,甚至连霍布斯鲍姆本人在自传中都承认“共产主义死了”。十月革命的梦想充其量只是梦想而已,而十月革命所催生的苏联甚至都烟消云散,成为失败的代名词。正因为如此,许多人为霍布斯鲍姆惋惜。如不久前作古的美国纽约大学著名欧洲史教授Tony Judt就指出,霍布斯鲍姆永远背负的“十字架”就是他死不改悔的政治信仰,影响他成为真正杰出的历史学家。
成为一代宗师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要有自己的学术梯队,特别是博士生,通过自己的学生甚至学生的学生为导师摇旗呐喊,从而扩大其影响。这一条件霍布斯鲍姆也不具备。如前指出,霍布斯鲍姆正式退休前一直在一个类似夜校的地方教书育人,该校当时没有所谓博士点,套一个中国目前流行的头衔就是,他不是“博导”。所以他没有通过培养下一代学者来扩大自己学术影响的条件。古今中外,一个人的学术影响大概有三大范畴,一是名牌学校与真正大师相得益彰。如哈佛的费正清及亨廷顿。他们因为哈佛而伟大,哈佛因为他们而更加著名。二是二流学者因为身处一流学校导致自身身价提高,人以校贵。三是一流学者却身处三流学校,学校通过学者而扬名。能达到第一类固然极好,名校名师交相辉映。但如不能做到这一点,窃以为霍布斯鲍姆这样的第三类情况更名正言顺甚至更伟大,因为他的成就货真价实,未掺任何水分,且是辛苦挣来的。当然能够做到这一点,个人需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
在如此诸多的不利条件下,霍布斯鲍姆最终还是成功了。他成功的要诀可能有三:一是多出书。他一生出版了近四十本书。但多出书并不意味着成功。美国老左派史学家Philip Foner(为目前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美国史学家Eric Foner的伯伯),一生出书近百本,却生前名不彰,死后也名不显。国内不少学者全集选集卷帙浩繁,除灾梨枣外,究竟又有多大学术价值及影响?所以霍布斯鲍姆的第二个要诀就很重要了,即要出好书。霍布斯鲍姆的“时代四部曲”,加上他的自传则为“时代五部曲”,部部皆精品,产生了巨大影响,属于“藏之名山”之作。连在政治上与其有水火之分的保守历史学家Niall Ferguson(现为哈佛历史教授)也在霍布斯鲍姆去世后撰文写道,其“时代”系列是任何有兴趣研究近代史的人的“入门必读书”,并称霍布斯鲍姆为“一代真正伟大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第三个成功要诀是长寿。如果前两个要诀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实现的话,这第三个要诀则要看上帝的旨意了。看来上帝对这位共产主义者不薄。他活了95岁。更重要的是,他直到去世,除行动不便外,思路仍十分明晰,仍极富创造力。他在临终前三个月,还亲手编订了自己的另一本书,书名叫Fractured Spring(大意为破碎的春天),是他关于20世纪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论文集,其中涉及宗教、科技、大众消费文化、高雅艺术的没落、美国牛仔文化等多种题材。该书将于2013年3月由美国著名出版社Little, Brown and Company出版。由于长寿,霍布斯鲍姆在英国工作35年,于65岁规定年龄正式退休后(1982年),实际上开始了其人生的第二春。他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纽约大学、康奈尔大学等诸多学校做客座教授,同时开始进入学术研究的黄金期。他的“时代五部曲”中的三部曲——《帝国的时代》、《极端的时代》及其自传《有趣的时代》,都是在退休之后撰写和出版的。他关于20世纪的《极端的时代》于1994年出版时,他已经77岁了。这本书的出版将霍布斯鲍姆的声誉及影响由欧洲扩及全球。从影响上来说,这本书是他最成功的一本书,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中国大陆及台湾均有翻译出版。在全世界该书都叫好叫座,佳评如潮,使霍翁名利双收。
霍布斯鲍姆的巨大学术影响及成功秘诀还在于他的写作方法和技巧。西方史学家撰写史学著作大致可分为三类:叙事体史学家(Narrative Historian),分析体史学家(Analytical Historian),和夹叙夹议类史学家。在中国很有名的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史景迁就是非常成功的叙事体学者。分析类史学著作以论证见长,侧重观点分析。三种方法各有长短,但以对普通作者的影响而言,叙事体著作显然占有优势,因为其以描述为主,用精彩文笔对某段历史娓娓道来,在叙述中不经意地带出自己的观点,雅俗共赏。霍布斯鲍姆的五部曲都明显带有叙事体的风格。这些书思路明晰,文笔生动,用细节说话。对一个成功的历史学者来说,能提出“振聋发聩”或“新奇脱俗”的观点固然伟大也令人敬佩,但能用生花妙笔把一段历史故事生动准确再现,让读者读起来手不释卷如坐春风,实际上更难做到。而霍布斯鲍姆的伟大成功即在于此。他是叙事体大家。他的著作,专业历史学者喜欢,一般读者也能享受。当代中国的学者应该好好读一读他的五部曲。即使不是为了提高历史修养,而单为了学习他如何写作,也是开卷有益的。老实说,许多中国的学者不懂文字,不仅食古不化,食洋不化,甚至无法用中文清楚表达自己的意思。当代中国的最大悲剧是缺乏真正的人文大师,缺乏真正能做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人文学者。
霍布斯鲍姆尽管没有自己的学派,没有惊人的高论,但他的著述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自下而上”叙述历史。他是“自下而上”写历史的先驱者之一。他写劳动人民,写小人物,很少涉及王侯将相。同时他也强调大历史,注意强大的社会及经济力量,甚至跨国公司的作用。可能是因为霍布斯鲍姆的国际化出身和经历,以及他的共产主义信仰(须知共产主义正是以国际主义为出发点的),他因而阴错阳差地成为意识到国际史重要性的最早历史学者之一。尽管他的《极端的时代》一书只写到1991年,但就是在那时候,他已提醒读者跨国公司的重要作用了,可谓先知先觉。
我们当然也不能为贤者讳,从非西方读者的角度看,霍布斯鲍姆的所有著作都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西方中心论。例如他的《极端的时代》把20世纪又细分为“灾难时代”(1914—1949),因为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及经济大萧条的时代,名“灾难”倒也说得过去。但他把1950年—1970年称为“黄金时代”,把1970年—1991年归为“危机时代”,从非西方历史的角度出发则实在有点不着边际。对中国人来说,我们是无论如何不能把1950年到1970年之间称为“黄金时代”的。而霍布斯鲍姆所说的“危机时代”,对中国、印度、巴西及东亚四小龙等不少国家和地区来说,实际上其相当一部分应称为充满希望和成功的时代可能更为准确。当然“术业有专攻”,虽然霍布斯鲍姆的“极端时代”写的是世界史,实际上他还是以研究欧洲史见长的。我们不能要求他对非西方历史同样熟悉。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或限制,这些都丝毫不影响霍布斯鲍姆的巨大学术成就。就影响而言,在当代历史学者中,鲜有人能同他比肩。他的著作不仅在西方,甚至在拉美、亚洲及世界许多地区都有忠实读者。巴西前总统劳拉在其总统就职演说中就援引过他的观点,使他的著作一时在巴西洛阳纸贵。霍布斯鲍姆本人也成为巴西政府及大学的座上宾。在2012年6月霍翁95大寿的祝寿宴上,除学者外,巴西前总统劳拉及意大利现任总统均为他献上生日祝福。他的学术与社会影响由此可见一斑。霍布斯鲍姆的巨大学术成就甚至让英国保守的Spectator杂志在他活着的时候就称他为“健在的最伟大的历史学家”。1998年,英国的布莱尔首相为霍布斯鲍姆颁发了国家级杰出成就奖(Order of the Companions of Honour)。2003年,他获得杰出欧洲史研究奖,并且在2002年被任命为他一生任教的Birkbeck学院校长。由于他的辞职信一直未获批准,他实际上至死都是该校校长。凡此种种,可谓实至名归了。
霍布斯鲍姆去世后,其逝世的消息受到全球关注,并成为英国一些媒体的头版新闻。对他的悼念文字很多。英国的Guardian报纸甚至专门发表社论,称他为当代公认的英国最受尊敬的历史学家,甚至封霍布斯鲍姆为“圣人”(Sage)。更有人称他为“历史学家的历史学家”(a historian’s historian)。美国历史学家Eric Foner撰文称霍布斯鲍姆为“一生追求社会主义的杰出的历史学家”。甚至英国的政客也纷纷参加悼念活动,并对霍布斯鲍姆给予很高评价。如英国工党领袖Ed Miliband在霍布斯鲍姆去世后这样评价道:“他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并对政治充满激情”,“是一位把历史研究带出象牙之塔,带给普罗大众的学者”。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称霍布斯鲍姆一辈子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不仅为“进步政治史的巨人”,也是“影响一代政治家及学术领袖的学者”。
看来霍布斯鲍姆在去世时最终打破了其宿命,并赢得英国朝野及世人的一致尊敬。霍布斯鲍姆的个人时代可能因为其辞世而结束,但他的著作、他的多彩人生和他对建立更好的人类社会的追求会继续激励后人,惠泽世界。
2012年底写于都柏林及伦敦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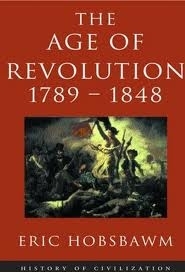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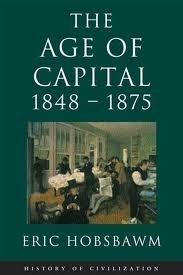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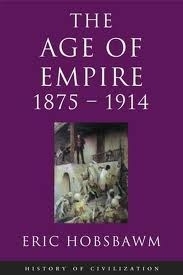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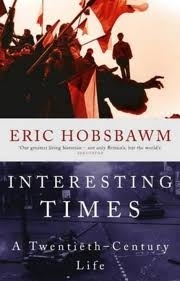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