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写作是在时间与空间的交融中进行的,时空必须互相转换形态,才能进入小说家的创作领域。即是说过往所经历的空间故事不断地建构时间的想象力,而反过来,时间的想象力又在建构着空间的故事。作家王安忆在《空间在时间里流淌》一书中论述文学写作里的生活细节时曾言:“在我的小说的眼睛里,建筑不再是立体的、坚硬的、刻有着各种时代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铭文、体现出科学进步和审美时尚的纪念碑,它变成另一种物质——柔软的、具有弹性、记忆着个别的具体的经验、壅塞着人和事的细节,这些细节相当缠绵和琐碎,早已和建筑的本义无关,而是关系着生活。”这种“关系着生活”的“另一种物质”,则正需要一种特别的叙述艺术来完成,诺贝尔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在这方面显然做到了。他将自己几十年来的个人经历置于许多小说的背景框架中,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虚实相融,以此种方式一次次带读者深入到小说写作之隐秘处,引导读者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的复杂一生。今夏出版的《盒式相机》,则又一次带读者进行了一次生命探微。
《盒式相机》的内容并不如他其他作品一样厚重深沉,读起来好似一段一段的碎片自天空飘洒而下,情感内敛,只有“奇”没有“惊”,只有“感”没有“叹”。若是没有耐心的读者,容易读了一两章便因平淡不了了之。《剥洋葱》将格拉斯隐藏心中已久的一段青年时代的污点轨迹暴露于世人眼前,是直面,也是忏悔;《格林的词语》主要讲述他所参与的重大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以及表明自己的政治思想主张,是表白,也是反思;而在这本《盒式相机》中,“曾经有一位父亲,因为上了年纪,他把几个儿女叫到一起,四个,五个,六个,总共有八个,在较长时间的犹豫之后,他们总算满足了父亲的愿望”,则是使用一种较为松散的拼凑方式来完成这种人生梳理。围绕着友人玛利亚·拉马手中一台无所不见、无所不能的的阿克发盒式相机,借来自不同婚姻的八个孩子之口,以九个章节来回顾他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的生活轨迹,是“乱七八糟”的“东拉西扯”,也是更了解作者人生的“咔嚓一下”。
另外,全书段落行间皆没有唯一固定的叙述主体,叙述者身份未清楚注明,是本书的独特之处,是为一“奇”。读者只能靠爱好、经历、职业、性格等特征暗示来辨别各人色彩,一会儿是帕特,一会儿是拉拉,一会儿是蕾娜,转眼间却是小保尔,这种不依正常对话形式的语言修辞表达是奇妙的。逻辑感强,不是随便穿插,而是依照时间场合有意安排。换言之,书中的“我”的叙事主体地位,主要是由其在小说中承担的功能所决定的。比起只有一个“我”来讲述“我”的语言叙述,这种众多“我”来讲述“我”的方式,看起来更适宜于作者的自我表述,或者说对自我内心多角度的深度反思。不同的回忆、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展示,缺席的父亲形象渐渐被发现、挖掘出来,而经年模糊的“我”更因借助不同时期相关的孩子们换一个名字、换一副形貌被唤醒。同时,这种使用他人的话语而不是个人的直接表述,相反地,又无意间达到另一种保持距离的效果,这种方式使谈及“我”时愈加自然,海阔天空,获得“众我”表述之间那种微妙复杂的张力关系。
“照相的人,更了解生活。”书中所描述的“照相的人”——小玛丽或者老玛丽,如插图所绘般的鲜活,擅于摆出各种姿态,用一台老式阿克发盒式相机为“这个拼凑起来的家庭”摄留人生场景中各种各样的瞬间影像。“她绝对是把什么东西都咔嚓了下来”,有再普通不过的生活碎片,如混合在烟火缸里弯曲的烟蒂和烧短了的火柴;有难以理解的无用之照,如橡皮擦过的碎屑;也有意义闪现的“历史的快照”,如柏林战后被炸飞一半的房子等。令人着实惊奇的是,这台在战争年代经历过炸弹、水灾、火灾的盒式相机犹如童话里的“魔盒”,以奇迹的方式拍出的照片“无所不见”,既能看到过去,又能够预知未来,等到在暗房里面显影出来后,更是已变得与实际情况完全不同,难怪孩子惊呼其为“希望相机!魔幻相机!奇迹相机!”这些皆为本书添上了些许魔幻色彩。
“盒式相机”应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角色。这相机拍出来的照片就像一个素材仓库,有和作者本人的生活历程和情感心路息息相关的一切,为他的一些作品提供了索引和背景依托,就像小玛丽所说的,“在每一片碎屑里面都隐藏着一个秘密”。于是,读者可以知道,小玛丽拍的黑白照房子的照片里,有锁在鸟笼里的两只金丝雀、苍蝇拍上粘着的几只半死不活的红头丽蝇、时而躺在花坛之间晒太阳时而又在地毯上打滚的花猫,原来对格拉斯写《猫与鼠》影响很重要。小玛丽拍的照片正是如此不可思议地开启了《比目鱼》、《狗年月》这些小说的创作密码……“她只听他一个人的话,他肯定也完全依赖于他的小玛丽和她的盒式相机,她只为他拍摄独家照片,据说是他写书所需要的。”是的,格拉斯需要这些照片,为了在能够准确地想象过去情形的同时,也能够找到虚构的秩序、虚构的逻辑,从而去虚构想象的故事。他“完全是以追忆过去的方式活着”,在相片里——在许多记忆空缺之间东翻西寻,然后凭感觉让它们变成图像,此时混为一起的真实或虚构细节,亦随之合理并置且想象性地组合起一个完整的故事。
小说结尾,“是他,只能是他,继承了小玛丽的遗产……为了以后……不得不通过工作来偿还这些,只要他还活着……”掩卷沉思,让读者不得不佩服格拉斯在文学里找到了回应人生无常的方法。这种“自传体小说或小说式的自传”,又何尝不是对人生境况的喻示!乃至于“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无论对享誉世界文坛的格拉斯,抑或对普通人而言,皆是如此。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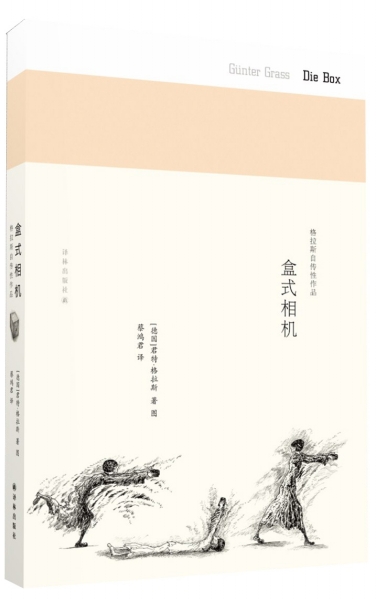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