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竹,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居所的喜物,又是一种深具精神性的物种。
“倚倚修竹,不卉不蔓,非草非木”(元·赵孟頫《修竹谱》),却“其干亭亭然,其叶青青然,其色莹莹然”(明·方孝孺《竹深轩记》),这竹常绿常新,不染于物,濯之愈新,耀之愈明。如此是竹的第一境:纯洁之境。竹由笋苞潜地而行,逢春雨破土而生,拔节而长,本体渐露,端得千竿万竿一例而看,却又各枝各竿各有不同。那竹中空而虚怀,谦谦若君子,含而不露,发而中节。“犹之惠风,荏苒在衣。”如此的“虚中”让中国人品出一种深蓄,一份神喻,正是虚怀象道,无欲则刚。此是竹的第:虚怀之境。“虚其心,实其节”(《修竹谱》),竹直节而向上,挺立而不屈,自古以来劲竹是对竹的礼赞。竹的质,犹在节处坚硬;竹的劲节正在于一节一节相托,劲梢挺立云天。竹节中含着坚韧的托付,默然的操守。此是竹的第三境:守节之境。那竹“凌惊风,茂寒乡,藉坚冰,负雪霜”(东晋·江逌《竹赋》),“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修竹谱》),不因繁茂而浮躁,不因凛寒而燠变,“春木有荣歇,此节无凋零”(陈子昂),坚守贞常不变。此又是竹的第四境:持贞之境。
如此四境:纯洁、虚怀、守节、持贞,一纯一虚,一守一持,本身就含了变化之道,蕴藏着无数天机。四境又可让人返观自照,窥视人本身的内在品质。所以竹在中国,于日常中使用最广,不可或缺;在精神上又最具人格化的意味,广被用来比德人的品格和胸怀,人的操守与气节。直至今日,面向竹林,我们依然感受到古往今来爱竹者们的伟大心灵。
中国古代大师们争相与竹为邻,以竹为友,日日细察竹之生机生态,俯仰林中浮云寒烟,一方面他们将竹的风雅化作自己的风雅,将竹的风节比德自己的风节,将竹的气象潜化而成文人自己的心灵气象;另一方面又以精微的感受将那种风雅流淌在笔端,将那种气节注入笔下的山水风物,用那心灵气象催生艺术形式的品格气象。他们一代代地传递,一代代地叠加,将对竹的品评,跃升入一种精神人格的境界,并将这种境界拓辟在诗与画的田园中,成为中国艺术独特而深邃的内涵。
北宋大家文与可截取悬崖垂竹,以浓淡温润的墨色,撇写竹叶,揭开中国墨竹的优雅篇章。一代文豪苏东坡拈来萧萧修竹,磊磊湖石,挥笔成画,无论疏影横斜,抑或烟雨迷濛,都漾出一段文人独具的意趣,让人们于墨迹中揣见其心头的盘郁。多少诗人站在竹边水际,静心赏会,抒写月下竹上的联句,把那明月的清辉洒向竹林,继而抖擞着洒落白壁花径之上。又有多少画者从那飘飘洒洒、烟水波花的壁影上,兴会竹的天姿,倾听静夜竹石间的清音逸响,捕捉自然歌唱的天籁。郑板桥与金冬心是清末的两管写竹的圣手。“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郑板桥从萧萧的竹声中听出劳苦者的疾怨,赋予竹声以一种同情、关怀的庄严主题,让他自己的墨笔在跳匿奇绝的生动中,兼有了疏野苦涩的神情。金冬心年逾六十学画竹,每画毕,必有题。“秋声中,唯竹声为妙……非苦愁寒喧之声,而若空山绝粒人幽吟不辍也。”金冬心那直劈而下、郁郁累累的竹,倾出庄重不坠的心血,正若山中如禅的沉吟。
墨竹令写竹如若写字,写字如若写心。墨竹成了一份纤远的缠绵,将人心与烟雨修竹维系在一起,通过一管软笔的意写,把可见者与不可见者幽秘相联。中国的墨竹就这样被送上了以绘画识人心、以墨迹见境界的特殊的文化位置。那寥寥数笔守着单纯自发的天性流露,测试内心专注的含蓄与凝聚,却在百代千秋的浩瀚云烟中,挥写无数放拓逍遥的胸廓,瞥见代代传承的民族心灵的漂泊与安顿。在所有墨竹的挥写后面,在那翻飞无定的直写中,都似有累累竹影,隐隐幽意,让人想见那屈而不挠的风节。这种中华文化的独特景观,迥然相异于世界,一方面简约而自然,另一方面却又博大而精深;一方面见证人格的气象品质,另一方面又标示着艺术形式那幽微玄秘的层次与法度;一方面以寒林冷叶凝聚凛凛的生命力,塑造生死怆然的荒寒幽寂之境,另一方面又舞动如风雨江山外万不得已的飞矢,书写胸怀的宏阔与精神的气节。那人与竹相望、相守、相生的境域,凝在腕指之间竹管软笔那随心所欲的运行之中,凝在墨竹意写挥洒的超然之中,凝成某种民族心智的隽远模式和民族气节的庄重界域,等待着一代代的人们重新回到生命体验的本身,去揭示只有中国人方才具有的秘而不发、天人相合的创生机契。
二
一管竖笔就这样悬在中国人的心性之上。这笔就如这竹管一般,常常虚去自己,舒解在腕指的运行之中,成为人心与墨迹的通道。另一管竹枝也同样横在中国人情感的唇边,发出悠远凄美的笙笛之音。晋代戴凯之所撰人类最早的《竹谱》中说:“箫笙之选,有声四方。质清气亮,众管莫伉。”取竹做乐器早在轩辕黄帝之时,相传黄帝使伶伦,伐之于昆仑之墟,吹以应律声。东汉蔡邕曾盛赞今绍兴西南柯亭的良竹:“此地之竹制笛,奇声响绝。”这长箫短笛发出的却是家园的声韵,如龙吟凤鸣,又总带高山流水的自然清音,仿佛从心中抽出的绵长的怀念与愁绪。于是,就有了那众多的有关吹笙与思念的诗篇:“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唐·李益);“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唐·杜牧)。竖笔横笛中传扬的文采音韵,尽得历史的风流,那不可见的、却又手握指按而入于心的“竹感”,那贴在唇边、握在指间、却与心相亲的“竹感”,总让人与自然、与山水、与洒洒落落的竹山竹海相望相居,紧紧相连,爽爽地生出一份民族的悠远风气。
诗画相合,尤其重要者,诗情画意的融合。诗有诗之情长,画有画之意笃,将此诗与画、情与意交织融摄在一起的是人心。但人心是要有所依傍,才能有着落。竹即是人心千古的依傍。在竹里可以洞见世事的沧桑,人生的幽微,道说的妙理,天然的枢机。东坡先生曾提出著名的“胸有成竹”之说:他先写竹之生,续写写竹者的生姿,再写心手合一者的生态。东坡先生谦虚地将之归于文与可名下,却信手拈出,处触天机,其影响又岂在画竹之事。此后历代画竹大师都用自己的语言续写这份历史的长卷。郑板桥就写下这段飘逸神奇的文字:
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雾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
这样的题跋与其说是一段文字小品,不若说是短语式的中国艺术哲学。明代初年的李思问,以“听竹轩”命名简陋的书房。客问:你这里根本无竹,怎么能叫“听竹轩”?他从容回答:正因为无竹,所以用听竹命名……我的住处未尝有竹也未尝无竹,我未尝侧耳一听也未尝不听,因为:
悟而思竹,则竹环乎床帷之外;寐而思竹,则竹见吾梦;行而思竹,则竹盈于目。愁而解者,竹也;语而答者,竹也。吾琴,竹在琴;吾酒,竹在酒;吾箫磬,竹在箫磬。吾书而思竹,书有清幽闲雅之趣;吾诗而思竹,诗有琮琤飘洒之韵。吾方与子言,而吾之神游乎潇湘之北、洞庭之南。此皆竹之助也。
进而,他把自己的听竹与世人的听竹相比:“吾闻之,待外物而乐者,其乐有时而既,乐既,则悲戚继之矣,众人听竹也。吾不以有竹而乐,必不以无竹而悲,是故有待于物外,而乐自至,岂待于竹然哉!吾之心有,在矣。”如此境转心不移的境界,如此横阔而庄严的气象,正是中国人相忘于竹、心与竹化的心灵写照。
竹,千秋百代,飘飘洒洒,已成穿越诗与画、穿透自然与人心的飞矢,完全打通了现实与心灵、天与人的相对相隔的境况,成为众人之心的归依,成为中国人共同体认、带着精神特质的心物。于是,竹成了一种文化的眼光,墨竹、画竹,已不仅仅是“嘉竹如画”,不仅仅是寒林烟雨或风日流丽,更重要的是里边有性情的自由涌动,气节的凛然直现,灵魂的陶然止泊,人格的纯然映现。竹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意涵深长的气韵,让中国人陶然相忘在其中,竹格即人格,竹韵写心韵,竹与人通,人与竹化。在竹的面前,所有的中国人都成了哲人,成了诗人。竹,即成为中国人独特的、生生而不息的精神境界。
从中国人与竹相伴相居的现象,到中国竹的人格化倾向,再到中国墨竹成为人格化的可感可见的载体,进而成为中国人相忘其中的眼光和心境,竹包涵了中国人独特的现实与心灵的周遭,孕蓄了一个民族历史的疏影清魂、持贞守节的文化品质,并形成了一个天人相合的隐秘的文化通道。站在这样的道口,回望悠蔓浑远的竹文化的历史,我们心怀感恩,并滋生着一种责任。那家园与亲人的嘱托,已然化作我们牵挂于心、又心心相印的文化长游,化作只如坚竹的贞常不变的恒永使命,化作我们陶然相忘、心身相安的一份神韵与境界。
(本文乃作者为《中华竹韵》一书所撰序言,本报有编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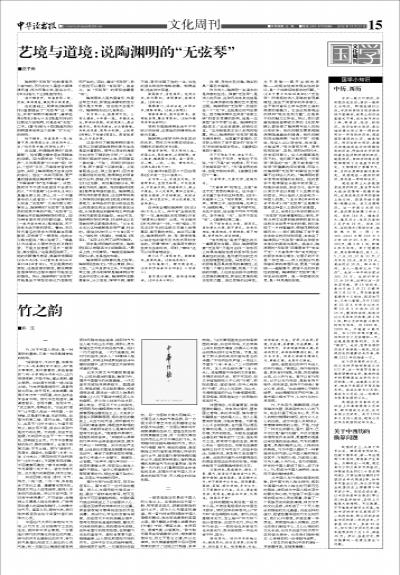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