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的戏剧有文本和演出,莎士比亚的诗歌有文本和朗诵。台词从演员口中发出,诗句从朗诵者口中发出,这就是声音中的莎士比亚。
在20世纪30年代,我看过根据莎翁剧本改编的美国影片原版《铸情》(即《罗密欧与朱丽叶》,1936年出品)。饰朱丽叶的演员瑙玛·希拉在月光下花园里阳台上说的那段独白:“O Romeo, Romeo! Wherefore art thou Romeo? ...”(“啊,罗密欧,罗密欧!为什么你是罗密欧?……”)表现出少女对爱情的纯洁执着和心理矛盾,嗓音如清溪流水,波澜萦回,至今还印在我的脑子里。20世纪40年代,我看过根据莎翁剧本改编的英国电影原版《王子复仇记》(即《哈姆雷特》,1948年出品),饰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演员劳伦斯·奥立维说的那段独白:“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表现出主人公对生死问题的哲学思考,深邃,沉凝,嗓音如大提琴琴弦的颤动,或疾或徐,叩击听者的耳鼓,它至今还在我的耳边萦绕。
数年前老友方平赠我一盒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部154首诵读的录音磁带,诵读者是罗纳尔德·考尔曼(Ronald Colman)。我非常喜爱,一再聆听。莎翁十四行诗有严格的格律规范,但下笔又如行云流水,起承转合,一气呵成。考尔曼的诵读有特殊风味,我称之为“诵读”(reading),略有别于“朗诵”(recitation),诵读更自然,不刻板,甚至使人感到带有随意性。我很喜爱这种质朴的风格。
考尔曼的发音是英国语音,没有丝毫美国腔调。有些字英国音与美国音不同,如clerk(神职人员)一字,英国人读[kla:k],美国人读[klə:k]。莎翁十四行诗第85首中有此字,考尔曼即读英国音。英文字中的r,美国人都发卷舌音,英国人不发卷舌音,考尔曼也如此。他的英国音标准而纯正,典雅而动听。
考尔曼对格律的处理是认真的,莎翁十四行诗每行为10个音节、5个轻重格音步(每步包括前轻后重两个音节)。莎翁在节奏安排上常常把动词过去式的后缀ed作为一个轻音节使用。这个ed中的元音字母e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发音的,但考尔曼诵读时一概把它作为一个音节处理。如第25首中莎翁让spread(张开)和buried(bu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埋葬)押韵。后一字本读['berid],但考尔曼读成['beri,ed],加重了字母e的发音,使之与spread[spred]押韵。听来悦耳。凡莎翁把动词过去式后缀ed当作一个音节使用时,考尔曼便作这样的处理,几乎没有例外。
但考尔曼对格律不是死守的。他做的是reading,而不完全是scanning(严格按韵节诵读)。在节奏方面,他并不拘泥于固定的格式。如第105首有这样的诗行:
Fair, kind, and true is all my argument,
(真,善,美,就是我全部的主题,)
Fair, kind, and true, varying to other words;
(真,善,美,变化成不同的辞章;)
按轻重格(即抑扬格)的要求,每步第一音节为轻读,如此处Fair(美)一字均应轻读。但从内容看,真、善、美三字同样重要,所以考尔曼诵读时把Fair也作重读,与kind、true(善、真)的分量相等。他这样从内容出发的诵读处理,随时可听见。
莎翁十四行诗的韵式为“abab cdcd efef gg”。在用韵时,莎翁常用“视韵”(sight-rhyme),即从字面上看去像押韵而读起来不押韵。如第117首中有love(爱)和prove(证明)二字作为押韵字,除开头的辅音字母不同外,后面都是ove,看上去像是押韵的,但读起来,前者是[lʌv],后者是[pru:v],并不押韵。这一类例子很多。考尔曼读时都按字的本音读,并不迁就莎翁而改变字的读音。也有个别例外,如第51首中莎翁把wind(风)和find(求得)相押,这也是“视韵”:因前者应读[wind],后者则应读[faind]。考尔曼把wind读成[waind]以与find在听觉上也押韵。这种处理出现两次,是绝无仅有的。
考尔曼诵读的一个特点是流畅。想来他对莎翁十四行诗极为熟悉,烂熟于心,所以读来举重若轻,仿佛轻车熟路,毫不费力,但觉抑扬顿挫,急缓疾徐,得心应口,潇洒自如。每一首十四行诗诵读的时间在40秒至50秒之间,从不超过1分钟。这种速度可谓快慢适度,恰到好处。他诵读时注重“文气贯通”,如并不一定在每行末有韵脚处停顿或小停顿,而是顺着语气,或顺流而下,或跳跃前进。他对rhyme(韵)的表达并不作“人为”的强调,这样,韵脚在诵读中便成为一种自然的蕴藏。另外,凡诗行中出现caesura(根据意思而作的主要停顿)时,考尔曼都作停顿处理。由于诵读流畅,所以字与字之间时时有liaison(连读)出现。若字末是辅音而下一字首是元音,“连读”就明显地出现。如第119首的mine[main](我的)eyes[aiz](眼睛)就连读成['mai'naiz];第126首的Her[hə:](她的)audit['ɔ:dit](账目)就连读成[hə:'rɔ:dit]。这样的例子甚多。这种处理使听者感到如江水流泻,舒畅自如。
考尔曼诵读的另一重要特点是适度的感情色彩。莎翁十四行诗歌颂真善美,抨击假恶丑,以友谊和爱情为主题,交织着爱和恨,欢乐与忧愁,和谐与冲突,焦虑与安宁……包含着深邃的哲学意蕴。考尔曼的诵读摒弃了他自己的“个人表现”,完全沉入诗的文本中。他注意掌握“古典的抑制”(classical restraint),不放纵自己的感情。但又根据内容的需要而流露诗本身所蕴蓄的感情波澜。如第66首,莎翁抨击社会的不公正,用11行揭露人世的丑恶与黑暗,连用10个连接词and以加强抨击的力度。考尔曼读这些诗行时语气愤慨,感情强烈,层浪迭起,势如破竹。读到最后两行(译文:“对这些都倦了,我要离开这人间,只是,我死了,要使我爱人孤单。”)时,节奏变慢,情绪忧郁、沮丧,把听者带入无限怅惘的意境。而这一切又都是有节制地进行的,形成一种高雅典丽、完整的诵读艺术。
这种诵读,是一种再创造。诗歌,例如莎翁十四行诗,应该说是由作者、诵读者(朗诵者)、阅读者、聆听者共同完成的艺术创造。
罗纳尔德·考尔曼(1891—1958)是著名的英国演员。他主演的电影,根据狄更斯小说改编的《双城记》(1935年出品)给我深刻的印象。他在影片中饰演为朋友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锡德尼·卡登,他最后赴断头台刑场时安慰一个一同赴难的缝工少女,那说话的声音至今还响在我耳边。他主演的另一部影片,根据希尔顿小说改编的《桃源艳迹》(即《消失的地平线》,1937年出品),也使我至今不忘。他在影片中饰演一位英国外交官,由于偶然的机会来到中国西南边境一处名叫“香格里拉”的世外圣地。他与在这里遇到的一位女友对话,那嗓音也至今仍印在我的耳膜上。但,考尔曼给我印象最深的,而且只要我需要便可随时欣赏的,则是他的莎翁十四行诗的诵读。这是一种能使人心灵颤动、精神升华的诵读艺术。他使我参与了这些诗的创造,我由衷地感谢他。自然,我更要感谢老友方平的珍贵馈赠。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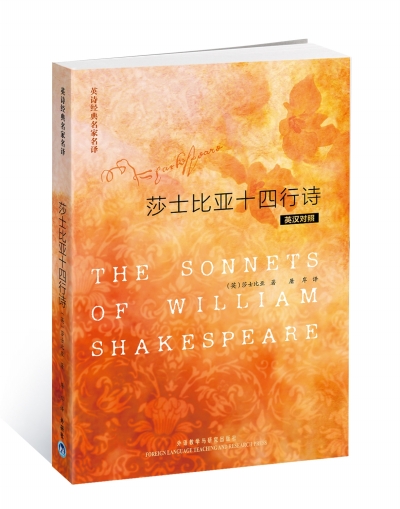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