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青年学者周保松《走进生命的学问》近日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在之前的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版《相遇》基础上,增加了周保松的近作《走进生命的学问》、《真正的教者——侧记高锟校长》、《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重建中国大学的价值教育》、《行于所当行——我的哲学之路》等篇目,以及其挚友陈日东所写的光彩照人的评论《可有可无的灰尘》,从这些引述的篇名都可以感知,周保松在这本随笔集里试图研讨的核心主题是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的重构,围绕中国大学的价值资源、传统、与主流价值观的关系、与政治、社会的关系等核心命题,保松以温和的说理和切身的体验,与其最初的读者中大学生塑造了一个阅读乃至心灵的共同体。
在这个共同体中间,没有压制性的权威,也没有流俗的偏见,更没有浅薄的愤激,无论是保松与对他影响至深至远的陈特教授的多次深谈,主题涉及“死亡”、“幸福”、“意义”、“情爱”等最基本的生命体验(这种师生关系和经验的描述,很容易让读者联想起《燃灯者》赵越胜与周辅成的忘年之交乃至生死之交),还是他在犁典读书会与其他公共空间中,与同学的深度交流,都展现出一种罕见的平等感与真诚性,这确实是保松将他“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在学术生活中做了一个彻底的贯彻。一群苏格拉底式的爱智者,在一个青年教师的引领和启蒙之下,从香港中环价值的黑洞和华尔街价值的宰制中出走,挣脱主流价值观的捆缚与消费主义的引诱,将自身陶冶成“知道如何在古往今来的人、事和思想中,选择他的友伴的有教养的人”(阿伦特语)。这在当今纷扰不已的香港无疑是一道人文的风景,虽然暂时只能发出微弱的光线,可是却未必不能星火燎原,开启更多的人的心灵生活与反思意识。
如今已经成为诸多青年人的人生和思想伙伴的保松,也是一个因生命偶然的机缘与心灵的自然习性,而在其人生历程中邂逅了诸多“伙伴”的人。保松虽然研习的是罗尔斯的政治哲学,而且曾经远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数年,但是他精神的底色却是中大本科生活所塑造的。钱穆的新亚书院发射出来的中国文化之光,尤其是借此投射出来的儒家传统的“士志于道,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人文精神与公共意识,让儒家念兹在兹的重践履在他心灵世界中镌刻不可掩蔽的痕迹。保松的形象呈现出一种意味深长的张力,一方面他从事的是最精深的分析哲学研究,终日与西哲中最深邃的知识人神交切磋,另一方面,他又直接面对年青一代学生的困境与挣扎,试图用他自身的经历与体验(这种经历在脍炙人口的名作《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中有着深刻的论述)“现身说法”,当然这不是一个真理性的独白,而是商榷性的对话,更是将自己的困惑与创痛直接呈现出来,与年轻人一同讨论精神的出路与价值的抉择,这种方式的教学自然不是今天中国大学触目皆是的满堂灌或者一言堂,教学是与同学一道去寻求人生与政治的可能性,也是在一同滋养心智生命的深度与厚度。
不仅如此,保松在香港乃至两岸三地的公共文化中也在扮演越来越积极的角色,他在香港参与直接的公民行动,将中文大学的民主精神通过政治实践的方式,移植到香港的市民社会。作为一个大陆移民者的后代,他在身份认同、社会公平的制度性安排、精神自由的可能性等方面的思索,自然是在深化香港社会对这些议题的探索(这在《行于所当行——我的哲学之路》一文中有深入的讨论),而与此同时,他又是台北《思想》、香港《二十一世纪》、大陆《南风窗》、《南方周末》等期刊和报纸的重要撰稿人和专栏作家,将他的思想探寻与学术成果,毫无保留地贡献于公民社会的成长。保松的文章与如今活跃在公共传媒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文字很不一样,他的文字干净、温润,他的心态平和、敦厚,他不以偏激和极端来耸人听闻,他在慢条斯理地讲道理,而在这种讲述的过程中,他似乎又在与自身对话,并且渗透了扑面而来的个人化的气息,生命与学问真正实现了某种融合,而不是像很多知识分子那样是割裂的、甚至相反的。我想,这是保松的文章之所以独具一格而深受大学生群体欢迎的原因之一吧。
在今天的中国,批评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比比皆是,而真正践行自由、博雅、民主的人文教育的个人却是凤毛麟角,所谓“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人格分裂早已被诸多的大学人内在化,习焉不察地成为集体无意识,而在这种过程中,体制化其实愈演愈烈。保松的可贵就在于,他也有批评和反思,但更多的心思和精力却放置在培育与滋养年轻人的精神生命之上,他像一个盗火者,将古往今来的优异思想和高雅心灵,通过日常的方式引入课堂内外,引入中大草坪上的那些“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比如他在《真正的教者——侧记高锟校长》里就写道:“高锟校长不喜欢别人崇拜他,更不喜欢别人盲从他。他要学生有自己的见解。真正的大学教育,应该鼓励学生自由探索,成为有个性有创造力同时懂得对生命负责的人,而不是用形形色色的戒条将学生变得唯唯诺诺服服帖帖。高校长明白,要培养这种人,就要给予学生最多的自由和最大的信任,容许学生尝试和犯错,并在众声喧哗和不和谐中看到大学之大。这不仅是个人胸襟的问题,更是理念和制度的问题。一所大学的师生,如果看不到这种理念的价值,并将其体现在制度,实践于生活,沉淀成文化,这所大学就很难有自己的格调。”保松对获得2009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高锟的理解,其实何尝不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的夫子之道?!正是通过知、言、行、意的努力合一,并挖掘中文大学的人文传统与民主精神,保松将曾经滋养他的中大传统以“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方式重新呈现出来,这样的大学精神才不是空疏而干瘪的,才是饱满、多元而结实的。
自然,正如书中收录的梁文道与周保松对话中指出的那样,在香港高校如此投注心力在学生群体和教学之上,其实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这种教学上的投入在同样只注重科研业绩(尤其是英文期刊的学术成果)的中大,无疑是与大多数教授选择的职业规划南辕北辙的。但是保松并不因此踟蹰,他行于所当行,遵循着灵魂深处的呼唤与自由的意志,既在大学里传递并演绎人文精神与批判意识的传统,又基于学理和政治实践发表公共言论,不讳言自身的公共知识人的角色定位。所谓学术生活与政治实践的对立,在保松这里无疑是一个“伪命题”。即此而言,他的生命走进了学问,而他的学问也深化了生命,而生命与学问的对接之中,层累而成的磊落而有责任感的人格力量,才是与其有密切接触的师友最深的印象。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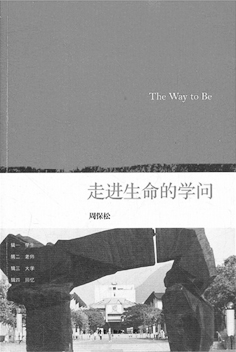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