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重返我们的视野最多不过20年,成为热门话题还是2005年以后的事。台湾也一样,若非鹿桥的《未央歌》,很多人对这所学校还闻所未闻。这并不奇怪,西南联大只存在了八年半,却已离开我们60多年了。然而,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可是响当当的,且不说它云集了北大、清华、南开的多少学术大师,也不说它培养出多少精英,只说这它掀起的一二·一反内战运动,与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并称为中国青年运动史的三大高潮,就足以让人肃然起敬了。
时间是不断流逝的,只有凝结成文字的历史,才能得以保留并进入记忆。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丰碑的西南联大一度被人遗忘,无疑是种悲哀。值得庆幸的是,西南联大罕见地又从历史走回到现实,就连“西南联大”四字也成了启迪人们追求理想、追求进步、追求人生价值的一个标识。其中原因很多,史学家的努力无疑起着推动作用。在这些史学家中,有一位早在我们之前就发现了它的魅力,并投入三倍于这所学校历史的时间,去接近它、触摸它、研究和撰写它。他,就是《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以下简称《西南联大》)的作者、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约翰·伊斯雷尔(John?Israel),中文名易社强。
(一)
我与易社强相识已25个年头了,联结我们的纽带正是西南联大。上个世纪80年代中叶,我为编纂《闻一多年谱长编》收集资料时,易社强来北京,联大校友会介绍他访问父亲,于是开启了我们间的多年友谊。当时,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问他为什么选择西南联大,他说是偶然看到《联大八年》小册子,读后受到很大震动,没想到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竟还有这样一所精英辈出的大学。在好奇心驱使下,他下定决心弄清个中原因,以至把最旺盛的精力和最成熟的年华献给西南联大也在所不辞。
易社强选定研究西南联大是1973年冬天,他后来发现其实早在1958年就与这所学校发生了间接关系。“易社强”这个中文姓名,即是台湾大学教授李定一访问哈佛时给他取的。易社强对这个名字很满意,只是几年后方知李定一原是联大历史系学生,冥冥之间,他已与西南联大结下了缘分。
易社强的最初工作是在台湾和美国进行的,中美邦交恢复后,中国向他敞开了大门。当时,西南联大研究还是一片无人开垦的处女地,所有工作都需从头做起,仅仅为了收集资料,他就至少投入了10年功夫。
易社强为西南联大耗费的时间太久了,其中伴随着许多故事。一次,他又来北京,我带着出版不久的《闻一多传》和《闻一多年谱长编》去探望他。他笑着说:你的两本书都出来了,我的一本书还没出来呢。其实,那时哈佛大学的东亚出版理事会已接受了这部书,只是编辑要删去一些照片,固执的他不肯让步,认为它们是全书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出版的事拖了很久,直到1998年方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付梓。
英文版面世后,我以为很快能见到中文版,没想到,它也延续了英文版的故事(其间还穿插了一些其他故事),结果又延续了12年,比西南联大的时间还长。易社强终于等到了收获,其实他的收获不止于此,他还赢得了云南大家闺秀李晓亮的芳心,成了名符其实的云南女婿。晓亮的父亲李希侃是我的祖父闻一多在中法大学兼课时的学生,他送给女婿的礼物,是祖父1945年8月29日给他题写的录屈原诗句字幅:“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借着这个机会,不妨说一下与易社强做出同样努力的日本学者。尚在《西南联大》难产的1997年,同志社大学教授楠原俊代女士便出版了《日中战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又一次长征·西南联合大学之路》。它是国外出版的第一部研究西南联大的专著,起步比易社强晚,却出版在先。与此同时,日本著名学者、中日学院院长、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安藤彦太郞先生撰写的西南联大史部分章节,也相继在《中日学院院刊》上连载。不幸的是,安藤先生的书还未写完,就于2009年10月与世长辞。否则,我们在看到美国学者笔下的西南联大时,也能看到日本学术大师眼中的西南联大。
说到本书中文版,不能不说到它的译者饶佳荣。饶佳荣是位富有思想、充满活力的青年学者,我和他相识于2007年岁末在云南师大召开“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上。他听说有这么一个会时想参加,然后就自己跑了去。当时,我只知道他的兴趣也在西南联大,何曾想他竟单枪匹马翻译了这部书,还闹出这么大动静。最近受到好评的《联大八年》、《联大教授》、《西南联大》等,也是他策划的。易社强曾说,他把自己嫁给西南联大了,饶佳荣紧随其后,也嫁给了西南联大。有这样一批人追踪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研究肯定会日加繁荣。
(二)
《西南联大》扉页上写着“献给西南联大全体师生”,在我看来,它既献给了西南联大全体师生,也献给了所有为延续中华文化顽强不息的奋斗者。与眼下或以西南联大为参照物进行反省,或拿联大说事,甚或剪刀加浆糊利用二手材料把冷饭炒热的出版物相比,这部书才称得上是实实在在的、沉甸甸的史学著作。
易社强是哈佛大学培养的中国通。1955年,始入哈佛的易社强便在费正清主持的东亚研究计划下接受教育,此后到1963年获得博士学位,一直没有离开费正清的门下。与费正清主要集中于晚清史的研究不同,1958年他将方向锁定在现代中国,考察对象先是学生民族主义,继是一二·九运动。主张学术自由的费正清没有给他太多压力,但严格的史学训练和治学方法,仍然潜移默化传给了他。《西南联大》有许多方面都有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的影子,尤其是两者都站在旁观者立场,用冷静的观察家眼光来审视问题。
用“西南联大万花筒”来形容《西南联大》,也许比其他比喻更形象。这部书,任凭从哪个角度看,都能显示出它的价值。
一,资料占有。相信凡是读过这部书的人,都会为书中材料之丰富而惊讶。我敢说,在材料占有上,目前很难有人能与之比肩。就说书后附录的130多位采访名单,既有大陆的冯友兰、黄钰生、金岳霖、陈岱孙、施嘉炀、钱端升、吴泽霖、杨石先、袁复礼、郑天挺、费孝通、王赣愚等,也有在美国和台湾的伍启元、任之恭、刘崇鋐、吴大猷、陈雪屏、钱思亮等,看到这些学术大师,就能感觉出该书的容量。任何采访都是需要付出的。一次闲聊,易社强说要买辆山地自行车,因为要采访,可云南多坡,爬上爬下有些费劲。不久,他果然从美国空运了两辆,当我们在昆明纪念联大校庆活动中见面时,他和当时的妻子余翠屏,胯下就是当时中国还没生产的这种代步工具。
易社强是西南联大校友接触的第一个为他们写史的人,况且还是一个美国人,这就使他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情相迎,不仅有问必答,有人还拿出从不示人的私人日记。曾经与西南联大发生过关系的西方人,也伸出了援助之手。直到逝世之时还关心这部书的费正清,向易社强引荐了清华和联大的朋友,还提供了包括手稿在内的个人文件,以及在联大外文系任教三年的英国学者白英的档案、报告。曾经居住在昆明或访问过联大的美国外交官、军事人员,也同样如此,当年美国驻昆明领事馆领事菲利普·斯普劳斯,即是其中之一。
口述记录和档案只是材料的一部分,更多的还需去书海打捞。这一点无须多说,翻翻书后长达44页参考目录就知道了。参考目录中,包括了大陆、台湾、美国各个图书馆、档案馆的名字。
为了获得感性认识,易社强多次到昆明,还探访了联大的长沙、蒙自、叙永校区。前些年,我到昆明时,想再看看祖父住过的陈家营和司家营,易社强正好在那儿,便陪我转了一天。那次他兴致极佳,如数家珍讲了许多联大往事,他对司家营的熟悉程度,也证明他来过不止一次。
二,宏观意识。由于《西南联大》的书名,不少人把它当成校史。的确,它是一部校史,可又不仅仅是校史,因为书中回答的问题并不限于西南联大,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导言》中,作者说他之所以研究西南联大,是由于“它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知识史、文化史和政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联大的传统模式和自由理念超越了中国疆域,提出了若干普世性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孕育并坚持通才教育?”、“促使一所大学完成使命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处境艰危之际,如何界定并阐明使命?”,更包括在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环境中,“批判性思维、多元主义、宽容和思想自由的原则到底有多重要?”这种大问题。这本书表面上似讲述西南联大,可作者面对的问题,已超出了校园围墙。如若体会不到这一点,就感悟不出作者的宏观意识,说不定还会陷入故事堆里。
三,特殊体例。大概很少有人注意到本书的体例,其实这也是一种尝试。依学院派标准,这部书还难算是严格的史学研究。四章结构明显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全书主体,包括离开故都、两次搬迁、扎根昆明、融入社会,还包括艰苦岁月、守望理想等。可是这种安排只能照顾到典型人物和活动,难以容纳更多的不为人知的普通事情。作者亦清醒地意识到这部著作不同于一般的大学史,认为任何一所杰出的大学,整体必须是各部之总和。于是,书中单列了一章,按照校史体裁,对各个学院、学系、师资做了分门别类的叙述,目的不仅在于尽量照顾到方方面面,同时有些颇有价值的问题,也可以放在这一部分。这种结构,初看时觉得与我想像的专题研究尚有距离。但认真读毕,方体会到这种框架实出无奈,因为西南联大可写的太多了,无论落掉哪个都不应该。
四,跨越时空。若说体例还有探讨余地的话,那么它的另一个尝试则是成功的,这就是用讲故事的文笔,娓娓勾画出组成西南联大演进的各个环节。书中有些地方类似纪实文学,个别处还加入了遐想,蒙自分校一节的“想象一下这道风景吧”那段,就很是生动。这种文笔,不仅用于弥漫着浪漫情趣的南湖,同样也用于一些严肃的问题上。联大与云南的融合、国共两种势力的暗中较量、与派系矛盾交织在一起的戏剧演出等,就也是这种写法,它缩短了时空距离,跨越了史学文学界线,读后如临其境,拍案叫绝。
五,主题把握。作为一所高校,它的使命究竟是什么,这是作者关心的核心。《西南联大》没有把这个问题装进一只箩筐,而把它分散到各个角落,无论是数次搬迁、学术研究、课程调整,还是学生生活、生存抗争,无一不与这一中心密切相联。为了突出这个主题,作者专列了若干小节,对坚持通才教育、抵制教育部统一课程标准、对旨在控制学生思想的导师制度的质疑等问题,做了深入探究,从中得出西南联大肩载的根本使命是维系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的结论。用书中的话说,就是:“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在这所大学竭力维护中华文化的生机”,“即使是战争岁月,也要保护并促进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西南联大之所以具有独立研究的价值,其意义正在于此。
六,同情理解。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西南联大享有“民主堡垒”的光荣称号。书中以大量篇幅记述了联大赢得这个称号的过程,其中国共博弈、反对专制、一二·一运动等部分,表现出对争取民主斗争的理解和同情,几乎令人看不出意识形态上的差别。
西南联大的“民主堡垒”称号主要靠学生获得,不过,教授政治倾向的转变,也起到了后盾作用。教授的群体性转变,不是特殊现象,经受了1944年日本一号作战打击后,各个阶层对政府的不满普遍滋长,在一系列的反省中,纷纷认为军事失利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制政治。《西南联大》在刻划联大教授在这种形势下的思想转变,没有超出我们的了解范围,但它用史料支撑了这一认知。书中写到张奚若,说战前张申府因在课堂上鼓吹共产主义被赶出清华,他负有很大责任。皖南事变时期,还说蒋介石对付新四军是医生在“化脓溃疡”处动手术。然而,1944年,他开始怒斥国民党的腐败,说重庆当局“独裁专断、腐败无能”,国民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书中还写到,张奚若的这种转变也发生在王赣愚身上,他也是“从完全支持执政党合法行为的客观的学者,转变为政府批评者和改革支持者”。造成这一转变的原因,一是国民党未能遏制日本的进攻势头,二是拒绝实施民主改革,结果导致蒋介石“失去了大多数留美知识分子的尊重和信任”,“使得温和派向左派靠拢”。
在西南联大史上,闻一多是个不可不提的人,他的名字屡屡出现在作者笔下,虽然专写闻一多之死那节文字很少,但正如台湾学者吕芳上教授说,作者把闻一多作为贯穿各章的灵魂人物之一。这,既是情感使然,也是对人生价值观的一种理解。
七,求真态度。站在观察家的立场上,作者根据史实,在一些问题上提出了与我们不完全相同的判断,这也是本书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历史和历史学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领域,前者是“述而不作”,只记录场景,后者则需要思考、分析,提出个人见解。西南联大的湘黔滇三千五百里小长征,是可歌可泣的抗日战争史的一幅壮丽画卷,当时的驻美大使胡适,曾自豪地向异国友人展示了途中的照片。今天,许多著作对这次小长征也给予了极高评价。易社强承认这次长途跋涉是艰苦卓绝的,而且是“中国学术共同体群策群力的缩影”,是“中国高等教育和文化赓续不辍的象征”。同时,他又以占有的材料为依据,认为这次小长征的实际作用,主要表现在“这群青年再也不会觉得祖国和人民是遥不可及的抽象概念”。影视作家陆天明创作闻一多电视剧本时,也说过意思同样的话,但并没有体现在剧本中。易社强则不然,他敢于做出个人判断。
类似之处还有龙云起初对联大迁滇的态度、三校个别学生曾经紧张过的关系、社会学系某些教授反对聘请费孝通等。就连给作者取中文名,又邀请他到台湾大学访问的李定一,也不加隐瞒说他曾休学一年去缅甸,靠倒买倒卖发了一笔财。至于引起联大学生“倒孔”游行的飞机运洋狗事件,近几年才由杨天石考证后提出疑问的,而此事真相,早在书中就做了纠正。还原历史原本面貌,既是史学家的责任,也是学术研究的科学态度,作者的求真不仅于西南联大无损,反而使我们与真实的西南联大更接近了。
八,贯通中西。《西南联大》在弥补我们知识空缺的同时,还给了我们一个警示,即我们在与西方学者面对同样问题时,暴露出的知识结构方面的差距。易社强受的是西方教育,数度到台湾学习,其中一次长达近四年,这种文化背景,使他能够发现一些我们难以觉察的问题。以哲学系为例,陈康教授的名字可能我们还很生疏,但易社强则对他翻译注释《巴曼尼得斯篇》评价甚高,说这并不在于注释是原作的10倍,而在于20世纪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时只想着赶上近代西方,却严重忽略了西方18世纪以前的思想。哲学系德国哲学的力量很强,但最重要的思想家马克思没有出现在课表里。一般人认为这与意识形态有关,易社强却把它与20世纪初英美自由主义者退回到学术界、马克思主义者转向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这一学术气候联系起来,指出这正是大多数联大教授的学术训练背景。类似看似平常的学术研究,经作者这么点拨,其背景和意义就更加显豁。
继承了学者论政传统的联大教授,创办过几种影响很大的刊物。书中重点介绍了钱端升主编的《今日评论》,同时也提到《当代评论》、《自由论坛》、《战国策》、《民主周刊》等。青年学者谢慧已注意到这个现象,2010年出版的《知识分子的救亡努力:〈今日评论〉与抗战时期中国政策的抉择》,便是第一部研究《今日评论》杂志的专著。易社强发现这个问题早于谢慧,但他把这一现象称之为“区域性的文艺复兴”。对于向达的敦煌石窟研究和印度史、西域史教学,以及王信忠的近代中日关系研究,作者也视之为“区域研究”。一个新概念,就这样在西方思维方式中诞生了。相比而言,我们不是不懂得史学研究中需要运用中西文化结合,但缺少自觉意识毕竟不容讳言。
(三)
任何成果都难免存在欠缺,《西南联大》也未能避免。
一,内容还应补充。西南联大是因抗战爆发才合组的一所战时高校,《西南联大》有相当篇幅与这场战争衔接,在介绍外文系师资时,也提到有一位日语教授。这位教授,应是全校唯一的日语教授傅恩龄。但是,再想了解情况,就让你失望了,书中根本就没有他的名字。这部书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事,其中之一是罗隆基与西南联大的关系。看到罗隆基出现在联大,我眼睛一亮,可我继续读下去时,却戛然而止了。在目前出版的西南联大著述中,该书信息量无疑处于领先位置,不少言简之处都可以作为专题展开,可惜大多只是素描,让人读后觉得不够过瘾。
西南联大与云南地方的关系,在书中屡次强调,但多数停留于现有成说,进一步的细节明显不足。1946年6月,费孝通的弟子王康与龙云时期曾任警备、宪兵、防空司令的禄国藩女儿结婚,国民党借此散布说民盟与龙云集团如何如何,此事闹得很大,我送给作者的《闻一多年谱长编》中已有记录,本可作为这一部分的支撑,但作者没有留意。
二,史实还需斟酌。书中说贺麟是国民参政会的党员代表,实际上联大先后遴选的11位参政员是张伯苓、胡适、张忠绂、罗文幹、周炳琳、钱端升、张奚若、罗隆基、傅斯年、杨振声、燕树棠、田培林,并无贺麟。再如说张奚若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坚定分子,这许是印象和推测,张奚若虽然赞成民盟主张,可从未加入民盟。比较重要的是另一件事。1946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西南联大,是这所学校与美国领导人唯一的一次直接交流,其中为欢迎他而办的英文壁报经美国记者报道,成为媒体的一个亮点。书中把这幅壁报说成是何达受吴晗暗示制作的,这与事实不完全相符。这幅壁报的制作者是王康、王子光兄弟,还有万禄等人,作者征引了王康的著作,却没就这件事向其求实。
三,资料亦存疏漏。书中多处引用了北京和台湾两地的《清华校友通讯》,说它们是“容量巨大的聚宝盆”。然而,西南联大在清华历史上只是短短的八年,作为全球联大校友交流的专门刊物《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史料价值在其之上。作者得到过联大校友会的通力协助,书中却未见《简讯》身影,这是一个本可避免的疏忽。
四,注释还可完善。书后的附录,为了简练起见,征引书目特创造了用汉语拼音简注书名之法,如“YNWS”表示《云南文史资料选辑》。但注释这本书时,只见名称未见期号,而这一刊物至上个世纪末就已出版了55期,如不注明期号,从何按图索骥。更有甚者,与繁体版相比,简体版竟然把作者专为中文读者设计的“注释简称表”删除了。幸亏我有两种版本,不然真不知道那些简称指的是哪本书。
诚然,与全书特色相比,上述瑕疵算不得什么。列举出来,只是期望该书异日修订再版时,能够更加完美,成为真正精品。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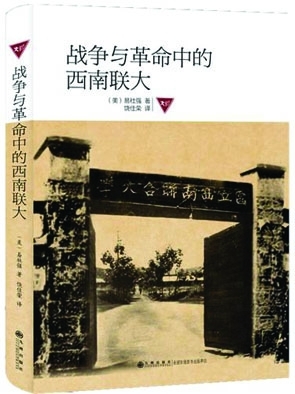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