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比较,是所有涉猎俄罗斯文学并思考哲学问题的人有意无意间都在进行的智性活动。有诸多因素促使这种思考不断进行并持续深入。首先,这是两座巨峰横于眼前的客观事实。二者都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和思想巨匠,生活于同一个时代,同样有着高超的文学技巧和对人类精神问题的深刻思考;只要对这一现象稍加注意,就会燃起对他们进行深入探究的激情:他们之间有怎样的精神应和,又有怎样难以跨越的鸿沟。诸多文学评论家和宗教哲学家都对此话题做出精辟的表述。再者,对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比较和选择意味着对终极思考做出判断和选择。很多人都是这样,以“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以“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结束;或者相反。
美国学者乔治·斯坦纳的专著《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种探究的典范之作。阅读本书是一次欲罢不能的精神旅行,也是对读者人文知识的极大挑战。本书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旁征博引,材料丰富,视野开阔。作者对世界文学和俄罗斯文学都有深入细致的分析。本书以翔实可信的文学分析和犀利透彻的思想阐释,解答了人们阅读两位大师巨著时产生的困惑;以比较文学、宗教哲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并极大地深化了人们的思考。这本书不仅让我们领略了两位大师的精神风采,纠正了因一知半解而造成的偏见;相比于前一段问世的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著作《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书的比较视野更开阔,更富说服力,也更富深度。
全书由四章组成,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分别就二者的生活个性、精神品格以及二者的小说艺术和宗教哲学思考进行了深度阐述。
就两位大师的个性特点和精神品质,本书做了诸多精辟的论述,如“托尔斯泰具有非常巨大的生命活力,拥有动人心魄的力量和令人经久不忘的本领,每一种力量在他身上都显得异常旺盛”;相比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天生具有超人的力量和耐受性,具有很大弹性和动物般的韧性。这些特征帮助他穿过个人生活的炼狱,穿过创作过程中想象出来的地狱”。
作者不断将两位作家带入到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中,与同时代及跨越历史的文学家、哲学家做纵横交错的对比,对各种相关文学现象做纵横开阖的深度阐释,在俯拾皆是的精彩表述中,让读者完成愉快的阅读旅行。在谈到托尔斯泰时,引入当时著名文学家的表述,突出了他巨大的生命能量,“他是无法对付的。这个人就像昨日刮过的东风,在你面对他的时候,它催人泪下,同时又让你全身麻木。”与此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所受到的疾病折磨方面,与尼采、普鲁斯特以及乔伊斯接近,“他们用身体的痛苦把自己包围起来,仿佛让自己置身于‘一座多彩玻璃构成的穹窿之下。透过这层玻璃,他们看到经过强化处理的现实’”;由此显示了作者睿智的观察和概括:“托尔斯泰的健康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疾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带有类似的创造力量的标记。”
在谈及小说艺术时,作者写出了自己的信念:“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小说界的领军人物,在视野的全面性和表现力度两个方面,两位大师都有出类拔萃的建树。”在将托尔斯泰小说与欧洲福楼拜等人的小说进行比较时,认为托尔斯泰的小说高于欧洲小说,不仅是表达了深刻的道德哲学思想(这是很多欧洲小说所欠缺的),而且有很高的叙事技巧:叙述以不动声色的方式展开,充满张力和真实感;主题富有多重性,并以极高的艺术手法带动诸多叙事;在情节构筑方面,作者以《安娜·卡列尼娜》为例进行文本细读,认为其开篇布局超过了同时期的欧洲小说;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通常有双重或三重情节,有助于强化场景的氛围和再现现实的复杂性;最后,作者指出托尔斯泰的技巧策略是他传达哲学理念的手段。作者还告诉人们阅读俄国小说的有效方式,即从总体上领悟,这样才能进入托尔斯泰宏大的核心世界,领略到“伟大艺术在哲学和宗教两个层面上触及人的经历”。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艺术,作者首先从其核心特质“戏剧性”说起,重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的莎士比亚”的说法。接着,考察了戏剧性在欧洲文学的发展,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戏剧的钟爱,分析了戏剧对他在感性、想象方式和语言策略方面的影响。通过对《白痴》、《群魔》等细读,作者触及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戏剧的精神契合点:戏剧方式最适合表现人类状况,实现他的悲剧观。本书以磅礴气势,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上考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技巧,同时指出人们容易陷入的误区,即夸大小说中的自传性成分。弗洛伊德由于对作家身体疾病和心理特质的强调,无法看出作家对精神世界的深邃挖掘。“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残忍的性行为来具体表达自己的哲学观和道德观”,“他的做法符合当时的文学主流”,而不是如弗洛伊德做出的心理分析。作者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极端的形而上学家”,他的“个人经历证实并且强化了他对离奇事物的认识”,作家藉此展开对人性问题的深度思考。就作家创作中反复出现的离奇事物、情节叠加,以及犯罪、惊恐等描写,本书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天才的方式,利用了哥特传统和情节剧”,达到了勾勒心灵现实全景图的目的,进而展开比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悲剧式幻想”现实主义以及哥特式手法将他的小说艺术观与托尔斯泰的区分开来,认为托尔斯泰回避哥特传统特有的邪恶与变态母题,其代价是放弃了作品的丰富性。这样的比较把握了二者创作手法的核心区别。
接下来,斯坦纳从文学史的角度考察二者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对现代文学的启示:在欧洲文学的大背景下,托尔斯泰是荷马史诗的传人,其小说《战争与和平》体现了“史诗的复活”;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则稳固地植根于《李尔王》建构的世界之中,他的小说使生命的悲剧感以传统的方式在整体上得到更新”。作者敏锐地看到了两者小说艺术的内在对抗性。这是以托尔斯泰的文章《莎士比亚与戏剧》中的偏见展示出来的,托尔斯泰认为荷马写作的是真正的诗歌,而莎士比亚的仅是模仿;而他将自己的作品与荷马史诗相提并论,凭他的智慧不会察觉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莎士比亚的接近;这就显示了托尔斯泰的高傲,以及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世界的隔阂。也难怪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后,托尔斯泰说最让他感动的作品是《死屋手记》,这与屠格涅夫的说法相近,完全忽视《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核心小说。
本书让人耳目一新的地方还在于以文本分析的方式披露了二者的难以融合、甚至对立的事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中梅什金的致命问题是“对爱抱有太多激情”,过度相信人的无罪和善良,这导致他学说的无力,而梅什金的名字和父称又不无巧合地选择了托尔斯泰的名字“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这也是作家隐蔽地对抗和嘲讽托尔斯泰及其道德说教的方式。
最能突显二者对立的是他们对宗教信仰理解上的分歧。本书将这个话题推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这首先在于作者触及了核心,即不管是使用“神话”还是“形而上学”来表述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是完全对立的。本书考察了托尔斯泰的作品和日记后,发现他最深的痛苦来自他极高的精神追求与叛逆不羁的身体之间的冲突。托尔斯泰之所以对荷马史诗倍加钟爱,还在于他在这个多神教的世界中感到轻松。这点上,作者与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观点一致。作者进而揭示了托尔斯泰信仰的扭曲之处:托尔斯泰将自己毕生言行的思想阐述为创立适合当时人类状况的新宗教,即没有基督的基督教。最切中要害的表达莫过于对托尔斯泰两难困境的描述:“上帝是创造者,是形成主要神话的诗人;艺术家也是创作者。在这种情况下,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呢?”这揭示了托尔斯泰身体力行的谦卑生活背后深藏于心的桀骜不驯。沐浴在理性阳光下的托尔斯泰不能理解,宗教可以是超理性的。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将一切拉到理性的层面。而对威胁生命的死亡,托尔斯泰不断借作品中主人公的口发出愤怒的质疑:为什么一个人如此渴望生命,却偏偏要死去?在对死亡进行思考后,托尔斯泰得出了让自己感到安慰的结论:“上帝就是生命”,“理解上帝和生活下去是相同的东西”。他以理性和经验的方式完成了终极探索,更确切地说,是遏制了对此问题的深入探究,因为宗教展示的是一种超越理性的精神现实。难怪热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称托尔斯泰进行的精神探索是浅薄的,超不过中学生的水平。
与之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荒诞的事物表示敬意,攻击日常生活中的重复方式”。而“重复”和“正常”则是理性和经验的重要特征。作者引证别尔嘉耶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表述:“没有谁像他这样,对经验世界不甚关注……他的一生完全沉浸在精神世界的深邃现实之中。”这也是不肯跳出“正常”局限的人攻击作家笔下是病态世界的缘由。
在剖析二者的精神世界时,作者以跨学科的视域表达了洞见,引入宗教改革家路德的表述:“在世间建立耶稣的精神天国”,并恰如其分地将之用于托尔斯泰的学说。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认为这样的尝试最终将导致野蛮的政治统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学思考中,托尔斯泰构筑的不是神学体系,而是人学体系,他建立地上天国的努力实际上是“极权主义乌托邦的神学”,而这预言不幸被20世纪苏联的现实所证实。相比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是将人引向上帝的世界,他的世界充满富有宗教色彩的象征、隐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场景中,到处都受到狭窄边缘的束缚,‘边缘的两侧站着上帝。’”这就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隐含于文本中的重要观点:人的出路在于选择上帝,而“迷恋自由、但是无法接受上帝存在的人肯定会走向自毁之路”。这也解释了作家笔下诸多自杀之谜。从二者的神学观看,他们不是仅仅构成对比,而是完全对立,对他们的选择也是非此即彼的。
这就带出了一个别尔嘉耶夫提出、被无数人呼应的观点: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了 “一个难以解决的争议——两套假设,两种基本的存在观在此相互对抗”;这也是本书的落脚点:以对两位大师的平行比较开始,以二者择一作为结论。如果人面对终极思考,就会得出“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结论。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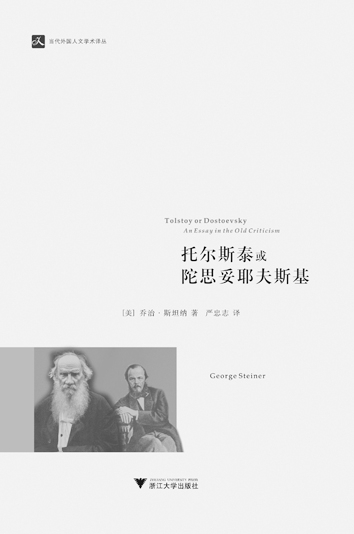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