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生活与创作》([俄]安娜·萨基扬茨著,谷羽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第一版)
我曾写过两篇关于茨维塔耶娃的文章,好像该说的都已说了,但是读了这部内容翔实、见解透彻的传记,仍然很受触动。举个例子,茨维塔耶娃最后致信文学基金会委员会,“请安排我在基金会开设的食堂里当个洗碗工”,当这一请求也遭到拒绝,她遂自缢而死。所留遗书的最后一句是:“不要活埋我!检查仔细点儿。”凄楚哀绝,却又雄浑有力,就像她一生的诗作那样。
《Goodbye》([日]太宰治著,张苓译,收《大方No.2》,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8月第一版)
《大方No.2》上译文篇末所注“未完”乃小说原有,太宰治一共就写了这些。他太想死了,甚至连“再见”都来不及说完。小说中有个人物说:“被女人迷恋,一起寻死,这不是悲剧,而是喜剧。不,应该算是出闹剧。滑稽到极致啊。没有人会同情的。你最好打消求死的念头。”很像作者特意讲给自己听的,但他到底还是与情人山崎富荣一起自杀了。我慨叹于人世间之于太宰治真是一点可留恋的东西都没有了,包括他正在写的这部堪称毕生杰作的《Goodbye》在内。但是正如梁遇春所说:“生不是由我们自己发动的,死却常常是我们自己去找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许太宰治面对生死问题比我们更从容。我对于自杀者一向有种特别的敬意,尤其是太宰治这般坚决得“一死方休”者,虽然我并不想自杀。
《死海搏击:母亲桑塔格的最后岁月》([美]戴维·里夫著,姚君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
我读此书,联想到周作人《先母行述》篇末所云:“作人不能为文,猝遭大故,心绪纷乱,但就记忆所及,略记数行。凡为人子者,皆欲不死其亲。作人之力何能及此,但得当世仁人,读其文而哀其心,则作人之愿不虚矣。”其意甚切,其情至深,对我们来说,大概话也就讲到这儿为止。里夫则是继续讲下去,穷极究竟。由此或许可以看出东西方人在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上的一点差别。里夫说:“回想起我母亲的死,我现在想法极少,遗憾颇多。主要是我感到内疚——生者的逃避立场。我多么希望在她活着的时候,或多或少在所有方面更多地顺她的心意。我多么希望能够压制住我自己的兴趣以促进她的兴趣。这就等于说我多么希望在她健健康康活着的时候,本该在我的生活中将她死亡的事置放在我意识的第一位。当然,我很清楚,这些都是无谓的意愿——是只有真正没有自我的人才可能想象他们能够实现的意愿。其孩子气、假装的圣洁、受虐狂色彩让我心惊胆战,但是,我无法(抑或是不愿意?)完全不理会它们。不管你多么关心一个人,你都无法总好像是他们已经处于弥留之际那样去照顾他们。这又回到杰尔姆·格罗普曼酷爱引用的克尔凯郭尔的话上:理解生活得回顾,过生活要前瞻。问题在于,到那时,通常都为时晚矣。”这段话道尽了“人子死其亲”时的悲哀。里夫在书中一次次把自己推到“不可能”的地步,从而设想种种“可能”,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在母亲永远的死和自己余剩的生之间找到一点平衡。这里有一个认识上的前提,即生命只有一次,故者如此,生者也如此,失之交臂,就再无相逢之时。我想起“生离死别”这句成语。“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乃是以“死别”形容“生离”,然而这也只是形容而已,真正的死别才最让人绝望。
附带说一句,此书原名Swimming in a Sea of Death:A Son’s Memoir,译后记说:“戴维·里夫的《死海搏击:母亲桑塔格的最后岁月》是一本痛苦的书。书中记录了他母亲第三次罹患癌症后接受治疗的痛苦经历,她拒不接受死亡的心态,以及她意识到自己在死亡这个问题上并非她一厢情愿所认为的与众不同时的无奈、不甘与恐惧。”中译本书名里“搏击”一词,稍嫌过于强调大限将至时她主动性的一面了。
《捍卫记忆:利季亚作品选》([俄]利季亚·丘可夫斯卡娅著,蓝英年、徐振亚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和《焚书之书》([德]福尔克尔·魏德曼著,陈钰鹏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
这两本书我同时买到,也是前后脚儿读的,不免有种奇异的感觉——后者讲有94位德语作家,“他们在75年写过被德国纳粹统治者及其走狗们认为是很危险的书,所以这些书都被当众焚烧了。”他们中的大部分已为世人所遗忘。前者则如该书“代译序”所言:“为了不忘却悲惨的过去,索尔仁尼琴写了《古拉格群岛》,为无辜牺牲者树立起一座纪念碑。利季娅写了《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但当局并不希望人民记住过去。”好似其间有着一番较量,而且不限于一时一地。我当然希望世事不像孟德斯鸠临终时说的“帝力之大,正如吾力之为微”,但是《焚书之书》译者的话显然过于乐观:“如果说焚书行动在当时并没有让戈培尔等人达到预期目的,那么到了今天,可以肯定地说,焚书的阴谋已经被彻底粉碎。”真要是这样,也就不劳该书作者这般苦心孤诣了:“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把被遗忘的人从被遗忘的角落拯救出来,使今天的读者重新了解他们和他们的作品,把焚书者的胜利变成失败,让当年的书以新的光芒重新辉煌。”在这里,记忆就是公正——无论这些作家及其作品价值如何,绝不应该因焚书而被从历史上抹掉。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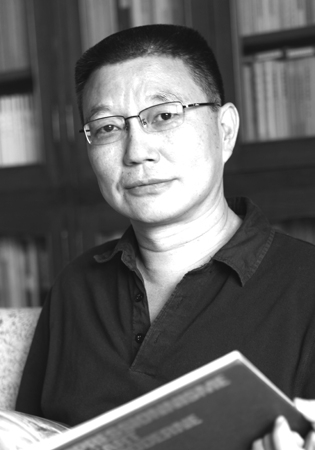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