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英国文学批评家、英语教育家和诗人瑞恰慈,被誉为新批评之父,基本英语(即Basic English,是C. K. 奥格顿在20世纪20年代发明的一种简化的英语体系,他希望其成为新的世界共同语)的主要传播者,在20世纪的欧美学界影响深远。在中国老一辈的人文学者眼中,他是西方现代学术观念在中国最重要的传播者之一,与现代中国人文学界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经六次来到中国,20世纪30年代初在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教过书,与吴宓等学者共事,钱锺书等曾为其学生。二战前,瑞恰慈在赵元任、叶公超等的襄助之下,曾在全中国推广基本英语。细数起来,他的学术生涯是跟20世纪中国许多著名学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之间的交往,历经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他的人生最后也几乎是在中国传播英语的旅程中结束的。但瑞恰慈本人具体为何方人士?他的成长历程如何?他的学术生涯如何?
负笈求学
瑞恰慈,英文全名是Ivor Armstrong Richards,因为常以I. A. Richards署名,所以这个名字更常见于他的著作和学术界。他于1893年2月26日出生于英国英格兰西北部叫三碚(Sandbach) 的小镇。
瑞恰慈于1905年1月作为走读生进入克利弗顿学院(Clifton College)的初中部学习。克利弗顿学院当时附属于罗克比公立中学(Rugby School,英国历史最悠久、最有名望的学府之一),创办于1862年,是一所维多利亚时代新型的寄宿学校。此类学校主要是仿照英国几所传统的重点公立学校来建的,与这些传统的学校有一定联系,但是在课程设置上又引进了新的理念,一方面保留了16世纪以来公立学校的传统课程,即包括古希腊语、拉丁语、古代历史和地理的古典课程,另一方面还开发了现代课程、军事课程和工程课程三大块,重视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科学教育,重视培养学生的个人兴趣。
瑞恰慈的传记作者拉索(John Paul Russo)对他的这段生活比较重视,认为他后来的兴趣和成就很多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源头。比如他在克利弗顿上学的第二年因为肺病而休学一年。在治病的一年期间,因为当时主要是靠野外锻炼来达到治愈的目的,所以他喜欢上了登山,登山培养了他的乐观精神、勇气和忍耐力,而且登山也成为他终身爱好的运动。在养病期间,他也读了大量在学校的一般学生不可能读到的书籍,其中最喜欢吉普林的丛林故事和斯温贝恩的作品。伟大的思想,超越小我的高尚情操,这种为朗吉鲁斯盛赞的源自古典文明的崇高精神以及对整体的追求,成为引导瑞恰慈完成一生大业的神圣之光。
这种在少年时代因病退养自修终而成就伟大性格的故事,在英国文学史中并不鲜见。但是对瑞恰慈而言,学校教育似乎也有同等的意义,塑造了他性格的另一面。
在克利弗顿,古典语言是必修课程,但是,瑞恰慈质疑古典语言对思维训练有决定作用,反而比较重视军事和工程课程,后来在老师查尔斯·斯本思(Charles Hickson Spence)影响下,转向现代课程,喜欢文学,尤其是诗歌等。诗歌成为他后来研究和写作的中心领域之一。
1911年,瑞恰慈完成在克利弗顿的学业,通过考试进入剑桥大学的麦格德伦学院(Magdalene)。1911年的麦格德伦学院是剑桥最小的学院之一,每年仅招收25名学生,图书馆的门楣上写着该校最杰出的毕业生撒弥尔·佩匹斯(Samuel Pepys)摘自西塞罗的名言:心灵即人。1975年,瑞恰慈曾把这句话翻译为“心灵是我们真实的自我”。这句格言为瑞恰慈终生遵守奉行,心灵,人的大脑和意识过程,是他一生学术关注研究的一个中心。
在麦格德伦学院,瑞恰慈的导师是著名学者阿瑟·本森(Arthur C. Benson)。一方面瑞恰慈认同本森对阿诺德的批评,接受本森的多元美学观,反对把艺术与人生分成两个对立面,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连续统一性。另一方面,瑞恰慈对维多利亚后期矫揉造作和自以为是的理性主义、社会进步观念、伦理观念以及以趣味为核心的散漫的文学艺术批评风气表示反感。瑞恰慈比较关注语言学、神经生理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这些新兴学科,希望借用科学理念和方法,来修正和提高思维水平,建立比较科学和实用的文学批评方法和原则。
瑞恰慈决定学习哲学,他的这一决定跟当时也是学生的奥格顿(C. K. Ogden)有关。瑞恰慈在后来的回忆中多次提到奥格顿,他们二人在剑桥的合作,对20世纪前半叶的语言学、哲学、文学研究和英语教学等众多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瑞恰慈初进剑桥,对眼下所学的课程以及将来学什么十分茫然,他与四年级的才子奥格顿一次偶遇对谈,使他决定学习哲学。这时剑桥大学的哲学系,云集了一批大师级人物,据说是剑桥自17世纪以来没有过的盛况。比如任教的有著名哲学家摩尔(G. E. Moore)、罗素等,维特根斯坦也于1911年来到剑桥,师从罗素。此时剑桥的学术圈内也正在发生一场革命,出现一些秘密和半公开的社团,如倡导者、异教会等,从形而上学到伦理学,从古典研究到经济学,从社会政治批评到文学创作,都有新进杰出的学者呼唤新的理性尺度和人性标准,用科学、理性和接近古典的现世的人生理想对抗弥漫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宗教信仰危机,这一思潮史称剑桥人文主义。
瑞恰慈在晚年回忆剑桥的学生生活时曾说,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迪肯森(G. L. Dickinson)的思想对他影响最大,迪肯森的一些作品他能倒背如流。迪肯森把古希腊和中国文化看作是两大理想的文化世界,他喜欢古希腊人神共处的世界,人活得自由自在,不像基督教世界的人活得那么累,每个人都因为原罪而有沉重的负罪感,终生都为自己与上帝相分离的处境深怀愧疚。中国的儒家文化以人为本,宣传礼让,尊重秩序,崇尚仁爱和中庸精神,对人有能力在现世达到至善之地坚信不移。从这个时候起瑞恰慈就把中国的圣人孔子作为自己的思想典范,儒家思想影响了他对哲学、美学和文学的思考和写作,这也可以说激发了他后来多次到中国旅行以及研究中国儒家文化的热情。
1912年,瑞恰慈在剑桥的学习因为肺病的复发又被打断了。1913年回来后,1915年肺病又第三次复发,他参加完毕业考试后,就回到了克利弗顿学院,在那里一边养病,一边听课,继续学习,但这时主要选修一些医学和生理课程。也因为肺病,瑞恰慈就没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闻名剑桥
1918年,瑞恰慈回到剑桥寻找教书的机会。次年,瑞恰慈有幸得到已在剑桥教书的朋友福布斯(Mansfield Forbes)的帮助,找到一份教授英国文学的临时工作,瑞恰慈讲授批评和英国当代小说两门课,很受学生欢迎。这一年剑桥的英语学院也正式成立,瑞恰慈与福布斯、提雅德(E. M. W. Tillyard)三人从此在剑桥开辟了现代英语语言文学研究这个新领域。
瑞恰慈在剑桥把英国文学课教得远近闻名,其得意弟子燕卜逊在晚年回忆说,“我在剑桥当学生时(1925年入校),他的课堂经常是挤满了听众,许多人进不去,他就在教室外面的街上讲课,有人说这种盛况只有中世纪才出现过。” 1926年,瑞恰慈被聘为剑桥麦格德伦学院的教师,一年学校付给350到400英镑的工资,还提供食宿,从此他的生活才稳定下来。
从1919年到1929年在剑桥的十年,是瑞恰慈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十年。他一方面为新设立的英语学院辛勤工作,参与制定教学原则和课程规划,设计考试方式和人才培养模式,对剑桥现代英语专业建设贡献很大。另一方面,他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出版五本专著,写了许多文章,奠定了他在英语研究上的地位。这五本书是《美学基础》、《意义学》、 《文学批评原理》、《科学与诗》、《实用批评》。它们基本代表了瑞恰慈一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
这十年,瑞恰慈在个人情感生活中也取得了进展,他于1926年12月与跟他相识近十年的伦敦姑娘多萝西·碧丽(Dorothy Eleanor Pilley)在夏威夷结婚,他们随后去中国和印度蜜月旅行。这是他们第一次到中国,但只是在北京、上海和香港作了短暂停留,就乘船去了印度。当时的中国内外交困,战乱不止,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可以说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美好的印象。然而他两年之后竟然决定到中国来教书,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作出这一决定,至今似乎还是个谜。研究者认为,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从在剑桥读书起,他就对中国文化有浓厚的兴趣,他与人合著的《美学基础》一书就公开地把儒家的中庸思想作为美的最高原则来阐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英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的广泛兴趣。此外还有个人原因。从瑞恰慈的学术性格上说,他喜欢开创性工作,对开创后的发展期一般没有多大耐心,剑桥的英语学院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在20世纪20年代末已经完成了开创工作,瑞恰慈那颗不安静的心就又开始寻找新的发展机会了。另外,多萝西是个记者和登山高手,喜欢旅行和户外运动,对剑桥枯燥乏味平淡的学院生活很不适应。除此之外,瑞恰慈可能发现他的文学课程并不是如以前那么广受欢迎,20年代的学生对教育的期望变得更加实际,多萝西在瑞恰慈的课堂上亲眼见到了这种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可能正是这些因素让瑞恰慈觉得有必要换一个环境,去进一步验证和宣传他的文学批评理念和教育思想。
游历东方
据国立清华大学聘任委员会会议记录,1929年8月7日在科学馆会议室召开当年第二次会议,第二条决议为新聘任的教授名单,其中第一条就是聘任瑞恰慈为外国语文系教授。当时在清华外文系任教的英籍教师吴可读(A. L. Pollard-Urquhart)是他在北京的联系人,他此前给瑞恰慈写了信,建议他选教员薪水相对比较稳定的清华大学来工作。
瑞恰慈夫妇于1929年9月14日才辗转到达北京,旋即开始在清华和燕京大学授课。他讲授一年级的英文课以及文学批评和小说等课程。当时清华外文系由戏剧专家王文显教授主持系务,他在国内外语界口碑盛佳。瑞恰慈的到来也增加了外文系的知名度,授课也比较受学生欢迎。但从瑞恰慈的日记来看,他对学生的了解似乎不多,除了认为中国学生勤奋好学记忆力超强之外,对学生的总体印象不佳,多次提到学生不主动提问,缺乏探索精神等。他对中国人的很多看法跟19世纪后期以来流行欧洲的对中国文化的偏见一致,但是作为学者,瑞恰慈一方面意识到中西文化的巨大差距,另一方面,虽然因语言的隔阂无法深入了解中国教育的现实需求,但他仍然比较尊重中国文化,积极探索帮助中国实现社会转型的途径。
在清华期间,除了教书之外,瑞恰慈积极参与校务活动,利用各种机会广泛接触中国学者,学习研究中国语言文化。据吴宓日记记载,瑞恰慈就多次向他请教中国语言文化方面的问题。
到清华的第一周,瑞恰慈就请了一位中文教师在家教多萝西中文,瑞恰慈似乎也在利用一切机会接触中国学者,开始实质性地学习中国文化。他原本是哲学专业出身,对中国传统哲学抱有极大兴趣,根据他留下的笔记,至迟于1929年底,他已经开始与主要来自燕京大学哲学系的几个中国学者进行定期的学术讨论,大约在1930年5月中旬,他在燕京大学哲学系的李安宅、黄子通和Lucius Porter帮助下,开始研读《孟子》。他们定期举行座谈,他在后来回忆说,“在北京我尽可能地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但是这些活动的特点是互不理解,你经常遭遇的是不明不白从头到尾的理解的失败。我觉得我必须做点事,因此我组织了一个四人小组,每个人都非常能干,我主要当秘书,在中国人面前,我没有什么好掩饰的,我只能把一个个汉字分开,除此之外,一无所知。”《孟子》的研读似乎进展十分顺利,瑞恰慈获益匪浅,于是他开始萌发了把读书讨论笔记整理成书的念头。1930年7月,他写信给剑桥同事提亚德,说决定写一本研究中国思想的书,已经有了雏形,同年10月给艾略特的信中,提到已经动笔写研究《孟子》的书。1931年,瑞恰慈离开北京,赴哈佛任教,据研究者推断,他此时才真正开始写研究《孟子》的书,虽然教学工作繁忙,但书写得很顺利,1932年1月,奥格顿主编的杂志Psyche首先刊登了《孟子论心》的部分内容,全书终于在1932年7月出版。
《孟子论心》的出版,对瑞恰慈来说意义十分重大。他开始认真研究中国文化,把他在前十年发展的意义理论和阅读方法用到跨文化阅读之中,寻找东西方意义之间的联系。他这次在北京有了重要的斩获,在北京的英语教学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对思维和语言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开始对语言的功用和文学阐释作了新的思考,影响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向英语教育的转向。
转型长路
瑞恰慈结束了在哈佛的课程后,1931年秋天回到剑桥,开始教学工作。但是剑桥的生活让他们夫妻二人都觉得不习惯了。他们给北京的朋友吴可读写信表达了对北京的怀念。在这个时候起,瑞恰慈重新开始与奥格顿合作,把主要精力放在奥格顿的基本英语计划上。他参加了一系列会议,如1933年去美国和加拿大参加基本英语大会,在报告中大力宣传基本英语,称之为教育工具和国际第二语言。1934年1月,他写信给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部主任大卫·斯蒂文思(David H. Stevens)提出自己有到中国去推广基本英语教育的愿望。此时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基本英语的前景比较看好,已经分别在1931年和1933年为奥格顿的正语学院(即The Orthological Institute,是奥格顿为传播基本英语成立的教学出版机构)发展基本英语计划提供了资助;1936年1至2月,又给翟孟生主持的北京正语学院提供了资金。1936年2月,瑞恰慈写信给麦格德伦学院院长,告诉他自己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一年的资助,将去北京主持正语学院的基本英语发展计划。1936年4月,瑞恰慈夫妇从日本转道北京,他的目的十分明确,要在中国推行奥格顿和他一同开发的基本英语教学计划,实现通过语言改变思想的理想。
基本英语是他的朋友奥格顿在1918年发明的,那时他们二人在剑桥正在一起写作《意义学》,根据瑞恰慈自述,他是参与了最初的发明的,但是他的主要贡献还是在组织传播基本英语上。从1919年到1929年,瑞恰慈在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剑桥大学也奠定了稳固的学术地位。但是这次远赴中国,投身英语教学,可以说他已经决定逐渐放弃文学研究,转向英语教学,并使之成为他后半生至死不渝的事业。
20世纪30年代是瑞恰慈在事业到达巅峰后决定重新开始的十年。许多人对这次转型颇为不解,因为瑞恰慈只需沿着他开辟的文学研究路子走下去,他的成就将不可估量。瑞恰慈自己后来回忆说,“其实,写完那两本书后(指他的《实用批评》和《教学中的解释》——本文作者注),我对后半生要花在如何公正地批改试卷上,感到不是滋味。太难判别一篇评论真正有多差,太多了,愚蠢的评论占了大多数。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决定退出文学,退出文学学科,完全退出,进入基础教育的?我学到点东西,知道了学术铁轨的位置,我以最坏的方式跨越这个铁轨。人家一遍一遍地告诫过我,罗素曾这样做过,他办了所学校,写了一本谈教育的书,可是人家说,‘难怪,因为他没有新的东西可说了。’”当时,英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放弃学术去从事教育是智力退化的表现。在朋友中似乎也只有艾略特支持他。研究者认为他离开剑桥有正反两方面的原因,负面的原因是他厌倦剑桥枯燥乏味的学院生活,这种态度似乎早在1923年他给多萝西的信中已现出端倪,在那封信中他写道:“我在这儿干什么?我问自己……我对剑桥没有感觉,剑桥也没有感动我。可能呆在这儿也值得,但是那就意味着一场艰苦奋斗。”可能对文学研究本身的怀疑也是他离开剑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他在文学研究上并没有像他预测的那样可以写出一套近似科学的抽象原则,与罗素等其他剑桥的学者媲美,但实际上他越想接近科学,却发现离科学越远。从正面而言,他性格中那种渴望挑战、永不满足的探索精神,也是重要的原因,这种欲望尤其是在他的东方游历之后变得越来越强烈。
瑞恰慈夫妇于1936年5月初达到北京,与他们在北京清华大学的老朋友翟孟生、温德和吴可读见面,还受到外文系教授王文显和校长梅贻琦的欢迎。正语学院在翟孟生的领导下,做了不少工作。6月,瑞恰慈接到学校通知,同意秋季离校的申请。于是他积极在北京活动,从大学到中学,推广他的基本英语计划,培训教师等。基本英语项目得到中国政府和学校的全力支持,到1936年底,瑞恰慈甚至产生了离开剑桥的想法。1936年12月底,他离开中国,1937年1月回到剑桥,但这次回剑桥主要目的是向学校交涉下一年的离职申请。
瑞恰慈再次获得学校的同意,于1937年3月返回北京。他完成“中学英语目标和方法的初步报告”后,于6月向南京政府汇报,南京政府成立了改进中国英语教学委员会,专门负责配合他的基本英语教学计划在中国的实施。这种顺利的形势让他十分高兴,觉得基本英语即将在中国各地开花结果。
但是1937年7月7日,日本开始全面侵占中国的现实很快打乱了他的计划。他们不得不搬进英国使馆躲避战火,并且最后决定离开北京南下。9月中旬,瑞恰慈先到香港,下旬飞到长沙,继续与叶公超、赵元任等人就基本英语的具体细节进行协商,办教师培训;9月底到广西,沿途得到当地教育机构的协助,宣传基本英语。因为日军的轰炸,他10月到达越南的河内,10月中旬又返回中国,去了昆明,到大理、洱海、丽江、玉龙雪山一带游览。从他们夫妇的信和日记来看,他们充分意识到一场势力悬殊的战争已经来临,基本英语似乎已经成了他们继续得到经济资助的借口。在昆明当地教育机构的帮助下,瑞恰慈为当地的中小学教师作了培训。1938年初,他回到北京和天津,继续编基本英语课本和教师手册,5月离开中国去了日本,从日本乘船去温哥华。
1938年9月,瑞恰慈回到剑桥,开了两门课,现代诗歌和英国伦理学,但兴趣仍在基本英语上,他写信给斯蒂文思表达了希望去美国开拓基本英语教育的想法。1939年1月,他最终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5万美元的资助,在斯蒂文思安排下挂靠在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由哈佛大学聘为大学讲师和交际委员会主席。但是这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去美国的计划受阻。在短短的两年中,他的基本英语梦想两次被战争打破。
通过与政府部门的交涉,瑞恰慈获得同意赴美接受哈佛的聘任。9月下旬,瑞恰慈乘船驶向美国,到达哈佛后开始办公。他的小组在美国的活动受到广泛的关注,《时代周刊》在1940年15日发表专题文章,称之为“瑞恰慈公司”。
从1939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瑞恰慈和他的团队主要把基本英语用在移民归化教育和扫除文盲的教育中,为美国的平民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拉索列举了他们的几项成绩,其中有瑞恰慈和吉布森主持的扫盲项目,教贫穷又不识字的老人说英语和阅读英语,还有编写基本英语教学图画,编写《基本英语口袋书:英语自学方法》等。虽然瑞恰慈为基本英语付出很多,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世界对基本英语的成败评价不一,普遍认为它跟帝国主义的文化政治关系密切,这使得他们失去了政府的支持,民间对此也不无怀疑,所以可以说此时基本英语已经基本失败。瑞恰慈也在考虑回到英国从事以前的哲学研究,正当瑞恰慈徘徊于去留之时,他获得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库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的认可,被提升为仅有的五位全校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之一,于是他决定留在美国。
二战以后,瑞恰慈在哈佛的正语学院改为英语研究所,1950年以后又改为语言研究公司,从事语言教学的收入逐渐成为公司的主要来源。1947年,瑞恰慈与艾略特等人一起获得哈佛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他继续从事英语语言教学研究,对现代技术保持了一贯的兴趣,编写看图说英语和组织摄制英语教学电影是他的主要贡献。同时他还参与了哈佛大学人文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设计,在通识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教学大纲中,贯穿了他一贯强调的人文主义教育理想,教育的目的不只是发展学生的智力,而是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学校的目的是培养理性,而理性的目的则是帮助学生更好地生活。
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多年之后,瑞恰慈夫妇于1974年返回到剑桥,1977年,瑞恰慈获得剑桥荣誉博士学位。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让他看到推广他四十多年来一直坚持的英语教学理念的机会。1979年4月,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携夫人启程飞往中国,在桂林、杭州、上海、山东等地演讲,与中国学者交流英语教学方法,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以致最后病倒,从此以后没有苏醒,于1979年9月在剑桥一家医院辞世。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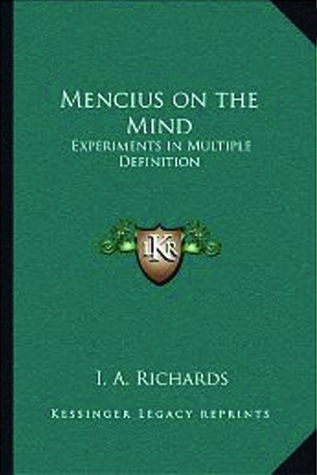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