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力量是通过思想家的言说和著作得到传递的,而思想家的言说和著作也使得思想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得到保存。2003年由涂纪亮先生主编的12卷本《维特根斯坦全集》出版,在当时成为(而且目前为止仍然是)世界上收入维特根斯坦已发表的著作最为完整的全集,在国内外哲学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数年之后,涂纪亮先生将他翻译的其中几本著作另外结集出版,再次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2009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建议修订该全集中的第5卷和第12卷,重新结集出版。经过两年的努力,三卷本的《维特根斯坦作品集》日前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全部出版了。在出版之际,我作为主要译者,感触良多。
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的是,翻译是一门永无止境的学问。虽然我曾翻译出版了一些著作,但每次阅读自己的译文,总是感觉如坐针毡,为那些蹩脚的错误汗颜。虽然我自己也反复教导学生要阅读原著而不是译著,但“让哲学说汉语”却总是我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情愫。我们知道,把西方哲学原著翻译成准确的汉语,这要比对这些原著的研究本身更为困难。研究工作是以对原著的理解为基础的,但要把这种理解转化为正确的汉语表达,则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在这种意义上,翻译工作应当比研究工作有更高的要求,真正的译著应当是对原著的再度创作。正是本着这样一种原则,我努力追踪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脉络,发现自己在原译著的翻译中存在的问题。也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追踪和发现中,我感受到了翻译作为一门学问的永无止境。当我面对周晓亮为我的译著留下的密密麻麻的校对批注时,当我看到张敦敏毫不客气地修订我的错误译文时,我心中充满的更多地是感激,心中想到的更多地是反省。
当然,在重新阅读维特根斯坦著作的过程中,我还感受到了思想的文本对我的更大冲击。文本传递的思想总是伴随着阅读者的理解而变化,但思想的文本则会在不断的阅读和反复的理解中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哲学家们的著作总是给人留下一些解释的空间,使得后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填补那些文本上的“空场”或“飞地”。或许,这正是阅读哲学著作的魅力所在。同时,这似乎也在告诉我们,哲学家的著作必须经过反复阅读,才能从中发现思想的秘密。我正是在反复阅读维特根斯坦的过程中,逐渐体会到维特根斯坦思想的独特魅力,特别是感受到维特根斯坦以一种非凡的表达方式向我们显示的思想内容。思想的文本在这里似乎更像是跳跃的音符,他的所有讲演笔记似乎都在向我们倾诉着他当下所思的一切,他为讲演所留下的文字似乎都在告诉我们他思想的秘密所在。阅读着这些文字,我仿佛可以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哲学家就站在面前,他用那略带日耳曼语调的英语向我讲述着他心里的故事,告诉我他心中的忧虑和问题。尤其是,他关于感觉材料和私人语言的讲演笔记,更让我触摸到了维特根斯坦内心深处的思考以及由此引发的提出问题的方式。哲学家的思想是通过文本向我们传递的,这些文本正是以独特的方式向我们呈现出了哲学家的真实思想。我把这种方式理解为文本对阅读者形成的“思想撞击”。
不过,给我带来更大震撼的却是哲学文本的“复制作用”。如果说思想的复制仅仅是思想者对已有思想的简单重复,那么,文本的复制则绝不是如此简单的重复。哲学文本的复制带来的是对思想的不同理解,是对文本的不同解释。因为正是这些不同理解和解释,才使得文本的复制变得必要;也正是文本的复制,才使得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得以可能。从此次重新校译维特根斯坦著作的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文本复制对思想理解的重要意义。当然,这里的文本复制就是指对原有出版译著或著作的再版过程,或者是对已有译著的修订过程。正是在这种再版和修订的过程中,文本中的思想才得以重新释放,阅读者才能通过阅读不同版本的译著中得到对文本的比较分析和对思想的深入理解。此次对维特根斯坦著作的再版修订,也给了我一次重新认识和理解维特根斯坦中晚期思想的很好机会。特别是他对哲学性质的评论,也让我重新体会到了思想者的独特力量。“哲学的困难不是科学的思想困难,而是态度变化的困难。意志的抵触必须克服。”“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遭遇哲学问题(如果有的话,也属于诸如自然科学问题)。我们只是在构造句子时没有按照实际的目的,而是根据我们语言中的某些相似的东西才会遭遇到它们。”“一个哲学问题只有在正确的背景中才能得到解决。我们必须给这个问题一个新的背景,我们必须把它比作我们通常不做比较的情况。”……所有这些话语,再次听上去依然如此震耳欲聋,发人深省。维特根斯坦在这里向我们反复表明的思想,正是以这样的文本方式表达出来的,而对这些文本的复制给我们带来的也正是对这些思想的不断反思。
必须指出的是,文本的复制作用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对思想的重新理解,更重要的是对哲学文本所显示的思想的传承和推进。显然,没有文本就没有思想,而我们对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正是通过不断地复制保留了思想信息的哲学文本。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对文本的复制就是让思想成为永恒的主要方式。我希望,对维特根斯坦著作的不断修订和再版,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而且可以使得他的思想在中国的哲学土壤中得到保留和发展,让他的哲学思想成为永恒。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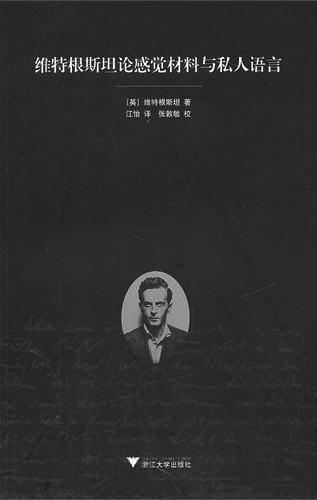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