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罗斯的三部作品《美国牧歌》(1997)、《我嫁给了共产党人》(1998)和《人性的污秽》(2000),与其说是“美国三部曲”,倒不如说是“背叛三部曲”。这三部作品分别对应了美国的不同时期:激情洋溢的六十年代、充满恐怖疑云的五十年代以及政治丑闻娱乐化的九十年代。这不是罗斯第一次书写政治意味浓厚的作品,但是他以如此密集的方式连续关注不同时代的精神面貌,在其中倾注如此多的精力和思考,还是有些令人意外。当然,美国的时代精神,只是这三部曲表面的共性,我从中所得到的印象却是在时代精神的观照下,那些被卷入时代风暴中的普通小人物一次次陷入背叛漩涡的时代悲剧。
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很多悲剧都具有史诗性,但是偏偏在罗斯的作品中,读者都很难读到一种史诗性的描述,就连那些描述大时代的作品也仍然采用了普通个体的视角。三部曲中,有个共同的人物,就是隐藏在故事背后的作家内森·祖克曼。他是这三部小说的叙述者,时而是个儿童,时而是个作家,时而是个身患前列腺炎的普通老人。他串起了这三个故事,也串起了美国的历史。我们不知道内森有多大程度上是作家罗斯的身影,但是从他断断续续的回忆中,我们才能察觉到他是有意造成这种时代的断裂感。这是一种高明的叙述策略,换句话说,罗斯从不“讲述”,他只是“叙述”——两者的根本不同在于,前者是被整合规整过的故事,后者是镶嵌在历史中的回忆断片。这种小说策略在《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中采用最为明显,故事的主人公艾拉是一名信仰共产主义的战士,二战结束后他因为成功扮演林肯成为明星,并因此结识了演员伊夫。他们的婚姻因为双方在信仰与价值观上的不同愈加难以维系。婚姻破裂后,伊夫出版了《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一书,让艾拉遭到了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作品中,内森不但是故事的叙述者,他还是艾拉最为喜欢的年轻人,他把他的思想灌输给内森,希望后者能继承他的信仰。而且,这个故事的叙述者并不是唯一的,除了内森,还有他艾拉的哥哥默里。罗斯在他的作品中不止一次采用了这种双重的、叠加的叙述方式。库切注意到这种罗斯式的小说策略时说:“我们所读到的叙述并非假装成天真的叙述。向我们讲话的那个声音,是一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的声音,但这个成年人服从于他本人年幼的自我视域,反过来把一种任何孩子都不具备的强烈自我意识借给了这个年幼的自我”。我们在阅读作品时要服从一个孩子的世界观,一个孩子的青春视角,但是这个孩子的青春,却深陷在一个老人的回忆里,这种双重的交织,是这部作品的最大的特色。
读罗斯的作品,你很难抽离出一个清晰的主题,所有的片段都深陷在回忆里,断断续续,似真似幻,虚构的笔法与真实的历史交融。他从来没有兴趣描述一段历史,他所感兴趣的只是那个时代中不同的人物因为不同的道德困境和政治困境造成的悲剧。《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中艾拉的悲剧是,他为了他的信仰丧失了一切,他被他的妻子和精神导师所背叛。《美国牧歌》中,那个犹太企业家利沃夫,被他的女儿梅丽所背叛。在反越战的年代里,年轻的梅丽成了炸弹客、恐怖分子,她同样被她激进的理想所迷惑。《人性的污秽》中,古典学教授科尔曼因为在课堂上说两个未来上课的学生是“幽灵”,被污蔑为种族主义者,开除雅典娜学院——因为那两个学生恰好是有色人种。科尔曼同样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背叛,被他担任院长期间治理得井井有条的雅典娜学院,被他得罪和未得罪的同事,其中还有当初他力排众议聘请的第一位有色人种教授所背叛。如果追究更为深层的原因,科尔曼的一生也建立在一个谎言之上,他原本也是有色人种,但他的幸运在于在种族歧视的年代里,他选择背叛了他的肤色,背叛了他的家庭和亲人,才有了今天的地位和荣耀。但现在,早年的背叛追上了现在的他,给了他狠狠一击。电影版的《人性的污秽》中有句台词说的好:“我为了自由,最终却变成了自由的囚徒。”这种背叛自我的背叛,让所有的人性丧失了光辉。
在《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中,罗斯借默里之口说出了背叛的意蕴:“每个灵魂都是制造背叛的工厂。无论何种缘由:为了生存,激动,高升,理想主义。为了可以带给人的损伤,可以施加于人的苦痛。为了其中残酷,为了其中的乐趣,显露潜能的乐趣,统治别人的乐趣。你让他们吃惊了。那不就是背叛的乐趣吗?……不但背叛的快乐取代了禁律,而且你不需放弃道德地位就可以违犯……暗中损害你心爱的人,暗中破坏你的对手,暗中破坏朋友。背叛正属于这同一类的荒谬,不正当,零碎无条理的乐趣。这类乐趣有趣味,可操纵他人,是秘密的,其中大有引人之处。”我说罗斯的这三部作品的主题是背叛,因为时代的诱因,一个个普通人都深陷各种背叛的漩涡,但是仔细分辨,却有不同的背叛形式。冷战时期,艾拉因为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而背叛;六十年代,梅丽为了自己的理想主义情怀,为了反战而背叛;到了1990年代,夹杂着克林顿的性丑闻,背叛仿佛成了一种娱乐形式,大众口中津津乐道的娱乐话题。几种不同的背叛,掺杂着几代人的伤痕。
背叛,最有名的说法来自于昆德拉笔下的萨宾娜,背叛就是脱离自己的位置,背叛就是摆脱原位,投向未知。“萨宾娜觉得再也没有比投身位置更美妙的了。”昆德拉笔下的萨宾娜同样背叛了家庭、祖国、爱人,把自己投向了未知的国家。这种背叛具有了一种更加叛逆的流亡浪漫主义的色彩。但是这种背叛与罗斯笔下的背叛最大的区别是主动与被动的区别。你会发现萨宾娜没有任何根基,她的背叛是主动的,而且绝不与人有任何关系。而罗斯笔下的背叛有主动者和被动者,而那些看似主动者也往往纠缠在另外一层的被动关系之中。这些被动者的背叛是一种“被背叛”,而且往往用一个高尚的理由和理想包裹起来。萨宾娜的主动背叛起始于逃离一个专制的国度,后来却被这种背叛的魅力所吸引,在背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罗斯笔下的人物生活在一个貌似民主的国度,但最终却被这种民主所背叛,被一种美国精神所背叛,被一种乌托邦的梦想所背叛。这些人物的悲剧就在于此,“小心这将自己孤绝起来的乌托邦的梦想。”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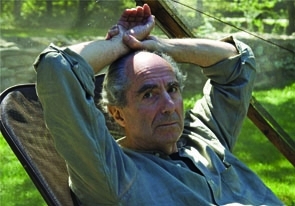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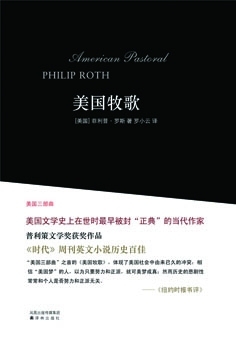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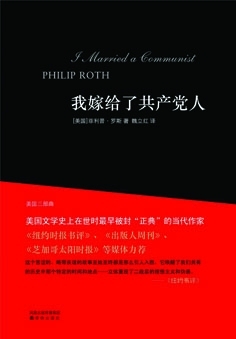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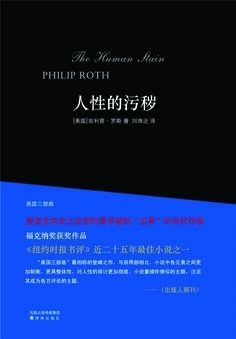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