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沈教授初识于五年前,他刚从海外归来时。说是初识,却全无陌生感,就像是认识了一辈子。尤其让我这个全无师承、一向自行其是的江湖大姐心头一喜的是,这位学院派藏学家对于草根派拙著的肯定。
作为学者的沈卫荣,不仅是人大一位知名教授,即使在国内和国际藏学界也卓有影响。他的学问或许可用藏传佛教文献中常用的两个词汇——甚深和广大——来形容,其中最精彩最有价值的部分反映在他数量不少,且用中、英、德、日等多种文字发表的藏学专业论著之中。据我所知,他用德文发表的博士论文《一世达赖喇嘛根顿珠巴之生平及其历史意义:对达赖喇嘛政体及其格鲁派历史研究的一项贡献》,被认为是国际藏学界研究格鲁派早期政治、宗教历史和达赖喇嘛活佛转世系列之形成的经典之作;另一专著《〈圣入无分别总持经〉对勘及研究》,则于汉藏佛教研究之间的重新沟通具有里程碑意义。在我读过的学术论文中,有两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篇是2005年发表在台湾《新史学》杂志上的《西藏文文献中的和尚摩诃衍及其教法——一个创造出来的传统》,另一篇是2009年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汉藏佛学比较研究刍议》,前者正本清源,拨开藏文古文献中的重重迷雾,重新诠释汉藏佛教历史上的“吐蕃僧诤”事件;后者高屋建瓴,以国际学术前沿的视野,为建立汉藏佛学比较研究这门新学科勾画了蓝图。这样的评判并非过誉,传统的藏学研究因之注入新元素。若用“学贯中西”来褒奖,沈教授必定不自在。这位谦谨的学人保持着永远的学生姿态,因为学海无涯。正如他自己在文中所说,“少小失学,至今对中学一知半解;游学西方虽十又六年,可对西学的认知尚不及对中学之一知半解”;他所做的不过是“有心步前贤后尘, 勉强作些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之学”罢了。学然后知不足,书到用时方恨少,相信这番夫子自况不仅仅是自谦。
在从事教学、科研之余,近年来沈教授陆续发表了一些学术随笔类的作品。从看似非主流的领域入门,从少有同行者的偏僻之路出发,跨越古今中西的门槛,在学术建树的同时,偶尔小试笔锋,发表一些非专业人士也能读懂、并从中受益的随笔,由此得到读者的认同和赞扬,值得称道。相比较而言,我并不认为这本随笔集足够代表作者的最好水平,可以与他的论文集并驾齐驱。进一步说来,即使达到了目前的最好水平也不希望就此结“茧”,我们有理由心存高级期待。为此建议有意对西藏的历史、宗教和文化作深度了解的读者,不妨将这本随笔集与沈教授的学术论文集《西藏历史和宗教的语文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出)结合起来一并参看,那里有多篇涉及西藏历史和藏传佛教研究的文章很有意思,对于一般受众而言也具适读性。由于学术和大众的分野,更为避免重复编选,而未能收入本集中。
从其人到其文,通篇看来,我以为收编于本书的文章大致可分为三类:一为认知的纠偏,二为学识的传播,三为心迹的表明。这三者常常互为表里,既专题亦综合,略作区分只为在此表述方便。尤其对于“纠偏”,纯系本人从阅读感受中归纳而来,作者并非刻意为之,不过是说事明理,把我们不以为问题的问题作为问题提出,从而引起注意和反省。例如,元明之际自中原士人开始滥觞的对于藏传佛教,尤其对于密教传统的误读,妖魔化+色情化,以偏见作定见,代相传递,直至当下,集中反映在二十多年前的某组小说中,发表后一度引发风波,并且差一点儿酿成危及民族关系的灾难性事件。沈教授告知我们,那种偏见是错的,问题出在哪里,本来应当是怎么回事。当然,另一方面,例如西藏佛教史上被创造出来的传统中,对于汉传佛教尤其禅宗的认识和态度同样有“偏”可纠,若干篇意在匡正的探讨文章已收纳在他的学术论文集里。
如果说这还是仅就具体事物而言,那么在更大范围、更高层面上,例如重新审视国学概念,是不是具备了相当的发言权。《闲话国学与西域研究》等几篇文章涉及了这一话题,旨在更新国学≈汉学≈儒学≈四书五经的传统认识,这也是从事边疆史地研究者的同声表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经由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缔造,广义国学理应涵括各兄弟民族文化。实际上,沈教授不仅为此鼓与呼,也正好有条件起而行。如前所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名下设立的西域研究和汉藏佛学比较研究两个学术机构,已成实践大国学理念的教学基地。
学识的传播,某些重申的常识不妨当作新知来读,至少对我来讲是这样。面对做学问的学问,即方法论方面的,如语文学,可能会有不少人像我一样,将之视同于训诂学一类,非大学而小术,但当读到这样一段文字,说不定就会改变看法:“译注一世达赖喇嘛的两部传记时,并未奢望要重构15世纪西藏政治和宗教的历史,但当工作完成,却惊喜地发现这样一部历史已跃然纸上了。”这样的例子还可以列举一些,如此日积月累,学问扎实厚重了,豁然别有洞天,应是题中之意。
另有关于“背景书”概念的引进,更是有益的提醒。你可以走遍天涯海角的未知地区,却很难走出你母体文化已然构筑的樊篱;你所见闻的,往往是迎合期待的,或者是,印证了你所预设的真实。即使足不出户,依然面向大千世界,“背景书”何尝不在时时地左右着我们的识见和言行。当然,抛开文化背景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只是当我们试图寻求真相真理,从而达至理解宽容,或者决定是否坚守,每当这时候,警醒到这一点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些盲目乃至谬误。
至于心迹表露,其实充满字里行间,有一篇最为直接:《我的心在哪里》,自问自答,具体定位在语文学,潜心做学问:“一位热爱学问、文献和文献研究的语文学家,平生最大的野心不过是要厘定、读懂和解释传到我手中的文本。” 是夫子自道,也可视为群体宣言,从中显现一个动态的链接和延伸——承接近现代以来自王国维、陈寅恪、季羡林等一代宗师和以韩儒林先生为代表的南京大学历史系所开创的学术传统,并且完成代际传播:今天在沈教授和他的同事乌云毕力格教授指导下的年轻后生们,兼修多民族语文,训练有素,学有专攻,对于非汉文文献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使用了抽丝剥茧式的语文学方法;同属国粹国故的多文种文献资源,或将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被开发,我们中华民族的国学内涵有望就此丰富起来。
一方面是冷学问,一方面是热话题,沈教授参与了讨论,凸显了中国知识分子另一优良传统:书生报国,心在民族大义。从西北舆地之学发蒙到当今边疆史地研究,百余年来所贯穿、所充溢的,正是最为深切、痛切、热切的爱国情怀,这一心迹无须说明,不言而喻。网上热议的、读者欣赏的,正是这类非同一般的功夫文章,诸如《谁是达赖喇嘛》——几百年历史一路看过,是体系和概念,符号和象征,说复杂也简单,他不是哪一个谁,这个复数的他只是被规定、被引申,尤其当下更多地被“政治”了。近年来总称为“西藏问题”的一系列国际化了的争讼居多为伪命题,作为一名受过严格训练的语文学家,他把纯粹的学术看作安身立命之本,志业既不在热闹处,私下里甚至为写这些“小文章”而感羞涩,所以沈教授的热点发言有可能只是偶一为之,惊鸿一瞥。作为读者,遗憾的同时表示理解。
言之有物,言之有理,借用藏式形容词言说,被理性知性光芒照亮的学者散文,那是嘉言宝库、智者喜宴、松石宝串、金色麦穗,是甘露精华、吉祥雨降、霹雳之钥、孟夏雷声……看到这组比喻沈教授定然会心一笑,因为它们正是他所熟知的古今藏文经典的书名或副标题,这类藻词的使用也正好反映出藏文书写者对于世界别样的感知和表达,以及对于知识的格外珍视与热爱。
来自藏汉各民族本土学识的培育,加上欧风美雨的灌溉,成就了沈卫荣其人,由此也惠及了一众学生和读者。在我,虽然虚长多年,但从亦师亦友的沈教授那里获益良多。试举一例:拙著《风化成典·西藏文史故事十五讲》完稿后,特请沈师审看,订正了多处史实,其中最重要的提示,是将唐蕃时期的法成法师单列一节。这位法成法师在敦煌,终其一生致力于佛经翻译:将梵文译成藏文和汉文,或者藏汉文互译,于民族文化交流的发展和贡献厥功至伟。陈寅恪先生曾将法成与玄奘相提并论,称誉为“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而国人对其事迹知之不多,中外藏学界甚至对于这位大师的族属是藏是汉迄无定论。对于其人其事,一经提点,赶紧补写一节,果成点睛之笔,全书亮点。
从千几百年前的法成法师,不期然地联想到我们的沈教授,同样的精通藏汉文,同样的在从事着民族文化间的交流,只是时代有所不同,内容更其丰富。每一代人都有他的文化担当,薪继火传,生生不息;进一步联想到首创了“托命”之说的前辈大师,联想到沈教授同时代的这一群学术精英,看起来冥冥中已被赋予了使命。这样的联想让我感动。
本文为《寻找香格里拉》一书序言,本报有删节。
本文选自《寻找香格里拉》,沈卫荣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32.00元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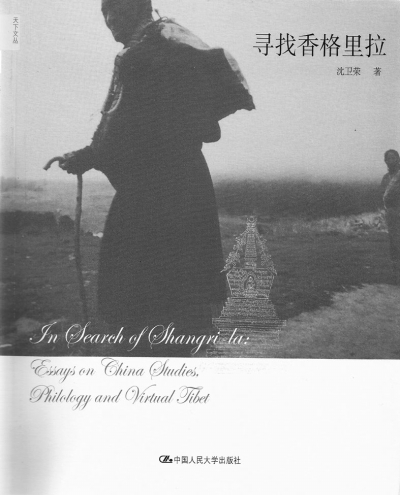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