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唐诺先生《阅读的故事》本有一番欣喜,早前读他《文字的故事》觉得有趣,写过一篇文章谈这本书,说有“情趣焕然”的好话,同时也说它“却失于杂沓”。这之前零散读过一两篇唐诺谈书的文章,感受尚好,因此对他写《阅读的故事》怀有期望,不过书拿到后略翻阅,似乎有点懵然,以为自己读不懂,姑且放置几日,待得秋阳高照,阳光满室再作阅读,岂料结果还是没能读懂那些奇怪的语句,免不了有些失落。
大约作者写作此书原意是想以哲学方式解释深奥的阅读原理,因此书谈论关于阅读及相关的事物,譬如记忆、时间、图书馆、书籍分类、甚至阅读的正确姿势等等,这当然是很有趣味的话题,然而信手翻来读到“从实际历史演化的末端成果来看”这样的话语,略有点诧异,毕竟历史演化一直在不断进行,恐怕宇宙存在这演化当会继续下去,何来“末端成果”。而“实际历史演化”一语同样使人不解,是否历史演化还有“实际”与“虚幻”之分,读来心生可疑,遂留意作者的造句,见“重读的最绵密最精纯最极致形式便是记忆了”一句,雾水满头,抛却花哨的排列修饰辞藻,此语当为“重读的形式是记忆”,实在不明白作者在说些什么。可能作者本来有些很好的思想,经他的文字玩弄,结果面目全非,这些短句且不去管他,毕竟阅读一本书无须注意小瑕疵,但若读到大段文字如:“这就是我个人过往的书籍总体图像,一个人类不无侥幸成分所艰苦创造出的独特基因之海——科学的进展太快了,事隔几年我已经不敢确定这个举细胞生物世界的基因交换取用说法是否还成立,但我仍坚信这个睿智而且璀璨的书籍总图像是禁得住捶打的,就像不信拉马克主义的古生物学者古尔德所指出的,人类的生物性演化系遵循达尔文的天择机制,然而人类文化的演化却是拉马克主义的,而且‘文化演化的速度是达尔文式的演化不能望其项背的,如今达尔文式的演化虽然仍在进行,但是速度却已经慢到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冲击了。’这样的话由忠贞达尔文主义者的古尔德来说,效力尤其宏大。”恐怕还是要问一句:作者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卡尔维诺的阅读姿势》一节开篇曰:“对不起,我把话说得轻佻了些,之所以这样,其实多少是为着对抗某种常见的迷思,希望我们把心思舒展在阅读,而不是尖锐集中在所谓的‘第一次’——有些第一次可能意义深远,有些第一次则就只是第一次罢了。太意识到自己要开启阅读的神圣性,太慎重,太悲愤,太风萧萧易水寒,觉得全世界都该在此历史一刻屏息等待你,这时候有必要浇一盆冷水,我们只是读本书看看,不是要去刺杀秦王赢政。”全然与卡尔维诺阅读姿势不相干又自我矫情的一通废话。接下来再读《一次只做一件事》:“不要用诸如‘专注’、‘专心’这么严重而且往往意有其他所指的词,卡尔维诺要我们让周围的世界渐渐消失,不被打扰,不被看电视不读书的邻居打扰,也不要被自己打扰(包括上厕所、抽烟和失望的风险云云),因为阅读就只是阅读,一次最好只做一件事。”这些扯得不知所云的话,前后意思相反,一次只做一件事就是“专注”、“专心”,与上厕所、抽烟等等无涉。继续接后面的话:“做一件事情,包括阅读,通常我们的动机总是复杂多样的,事后对我们的影响也是复杂多样的,但动机顶好在你阅读开始进行,就跟着周遭世界渐渐消失,并于事后的作用更犯不着记挂着,它自己自动会来,你叫不叫唤它都一样,就跟你舒服享受一顿好晚餐,它必定对你的内脏、骨头、血液、腹肌二头肌、免疫系统,乃至头皮下的脑子连带头皮上的毛发都有影响,但你管它!”如此罗嗦又含糊不清,语言不干净,废话连篇,且喜欢乱扯,致意思表达不明,读者即便有好心情来作阅读,也要被这样的语言败去了兴致。
倘使不大愿意相信这就是唐诺的写作,尚可继续耐心读下去:“日本已故小说家井上靖生平写得最好的一本书《天平之甍》,故事说的就是中国唐代时候日本四名遣唐留学僧为了弘法订律乘船到中土的一趟旅程,最终,清秀但柔弱的玄朝在中国还俗娶了长安街市的女子;粗犷且性格独特的戒融,如柏拉图所担心的,打开始就不打算再回日本”咦,柏拉图居然担心到日本小说家的中国故事里去了,要知道柏拉图生活于公元前约427~347年的古希腊,相当我们的战国时期,根本无法担心到唐朝去。再来看作者笔下所谈论的张爱玲:“另一个实例则是张爱玲小说。这位生长在极古遗老家庭和极现代(当时)租界地交壤之处的天才小说家,从小拿老人家东长西短的真实故事传闻当童话听,因此一直被看成是个精微洞视一切人情世故的无与伦比的小说家。张爱玲小说在这上头的确惊人,就她书写时的轻轻年纪而言,但等你自己年过四十了,被迫知道人心的复杂种种,你再回头读张爱玲,不管是《怨女》、《金锁记》或其他珠玑般的短篇传奇,你很容易发现原来她是如此‘文学’,小说中诸多人的反应、诸多触及人性复杂幽深的地方,张爱玲往往力有未逮,她只能凭借自己惊人的聪明去猜去想去编,并仰靠自己漂亮灵动而且气氛营造能力十足的笔盖过去——真是苦了你了,孩子。”除了堆砌矫饰的语言,就是空洞的絮叨,原本比较简单的意思经他拽来拽去的辞藻,反使阅读吃力起来。知堂致信俞平伯曰:“陶渊明说读书不求甚解,他本来大约是说不求很懂,我想可以改变一点意义来提倡它,盖欲甚解便多故事穿凿,反失却原来浅显之意了。”阅读本无须穿凿,浅显道来便是可读的好故事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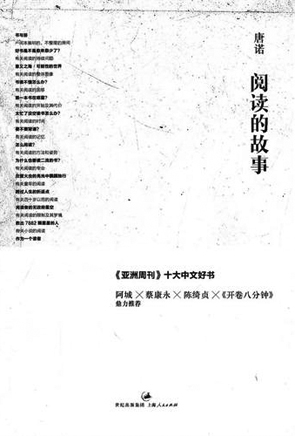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