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目前已经具备了毁灭这个星球上一切生命的能力,而人类的理性、良知与克制将是确保人类安全与秩序的最终依靠。今天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不断重新发现甘地。
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1869—1948)无疑是不同时期作家们非常热衷的一位人物。在20世纪初,即甘地尚未获得世界声誉的南非生活时期,就有作家为其作传,该作者约瑟夫·多克也成为甘地的一位长期朋友。20年代,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发表了《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甘地在1925年开始写作自传,先是连载于《新生活》(Navajivan)杂志,后于1927年和1929年以《我体验真理的故事》(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的书名分上下两册出版。1948年1月甘地遇刺身亡后,几乎每年都有好的甘地传记出版,到甘地诞辰百年时有关甘地的著作数量已经超过4000种。
1969年,正值圣雄甘地诞辰100周年之际,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H·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出版了《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暴力起源》(Gandhi’s Truth: On the Origins of Militant Nonviolence)一书。这本书成为不多见的、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甘地研究和精神史学研究的典范,被誉为对于中年圣雄的“史诗般的研究”。
圣人:独特的人物研究类型
1958年,埃里克森出版了《青年路德》(Young Man Luther)一书,从此确立了有关历史人物的一个新的研究类型——圣人(homo religiosus)。十多年后《甘地的真理》的出版更为作者赢得了令人景仰的学术声望和不容忽视的学术影响力。从宗教改革家路德到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领袖甘地,埃里克森将其心理分析的重点始终聚焦于历史上的大人物。对于埃里克森本人而言,虽然他的青少年时期以及成年早期恰巧与甘地、列宁、穆斯塔法·凯末尔等人同一时期,他目睹了这些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对世界的巨大影响,但他对这些历史上的大人物的理解远远超出了“大人物发挥关键作用”这样庸常的历史认知。埃里克森将大人物的研究路径与心理史学(精神分析)的洞察力结合起来,向读者展现了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英雄主义和领袖类型,并通过对大人物的研究巧妙地回避了民族、阶层(阶级)和代际关系,以寻找避免人类假种(pseudo-species)间毁灭性对抗的途径。在现代历史传记中,大人物研究路径(great-man approach)是最令人不快和不被人尊敬的历史教条,而心理史学家在对历史上的个体进行心理分析时往往会夸大历史上这些大人物的作用。埃里克森对大人物的研究,特别是对路德和甘地的研究,常常使其研究方法面临“是否可以运用于一般个体研究以及稳定社会体系中的个体研究”的质疑。萧延中教授在心理传记学译丛总序中明确回应了这样的疑问:不能激起社会情势之普遍信仰激情的人,无意于谋求改变人类精神构成的人,不适于采用“心理传记学”的分析方式。
于是,分析大人物就成为精神分析和心理传记的自然选择,而甘地被选作埃里克森的精神分析对象则纯属偶然,或者说是由于这位心理分析学家与圣雄甘地心灵相通的缘分。1962年,埃里克森受邀到印度主持一个有关人生周期的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举办地就在阿赫梅达巴,一个素有“印度曼彻斯特”之称的城市(埃里克森在书中将它与美国的匹兹堡类比)。在这个印度最早的工业化城市诞生了这个国家最早的工会组织,长期以来拥有印度最团结、最统一的工会组织和最为完善的现代福利制度。甘地从南非返回印度初期,就在这个城市领导了一场纺织工人罢工,促使印度第一个工会组织诞生,这使他与这个城市发生了重要的历史联系。他赋予这个旅游者较少光顾的城市某种历史的神秘感和持久的精神魅力,而这个城市也使甘地从南非的圣雄开始成为全印度的圣雄。在印度的这一因缘际会使已经完成《青年路德》的研究、着迷于人生周期研究的埃里克森将心理分析的聚光灯投向中年的甘地,就又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自然选择了。
甘地的真理
1918年的甘地年近五十,刚刚结束了21年的南非异国生活返国不久,面临重新认识和适应祖国印度并为印度民众所了解和接受的现实问题,而在其生命早期即已显现出来的被认为是母性特征的照顾他人的特性,又使他思考如何为国家和同胞服务的问题,于是中年人的责任问题成为埃里克森在其甘地研究中所关注的中心问题。甘地服侍年老的父亲,努力改造其作为“反面认同”的朋友,像一位母亲一样照顾南非凤凰村、托尔斯泰农场和印度修道院的追随者,崇尚非暴力行动的萨提亚格拉哈信仰以拯救对手的灵魂,这些都是甘地一生中在不同时期照顾他人的主题再现。“照顾”可以被理解为甘地一生行为的重要动机。
“照顾”的动机主题在甘地的萨提亚格拉哈信仰中臻于成熟。萨提亚格拉哈是理解甘地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个概念是甘地为了表达自己的非暴力理论,对一位亲戚的建议进行修改后自己创造的一个词。1907年,甘地第一次详细阐述了作为理论和斗争手段的萨提亚格拉哈。在甘地看来,萨提亚格拉哈既是对真理的坚持,也指爱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人类没有能力了解绝对的真理,因此没有资格进行惩罚。”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永远都不允许使用暴力来对付自己的敌人,而要用耐心和理解使对手摆脱谬误。在甘地看来,对于真正的非暴力的斗士,他们战斗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敌人。尊重敌人,理解敌人的动机,赋予敌人作出改变的勇气,都是萨提亚格拉哈的重要内容。于是,妥协常常成为萨提亚格拉哈的一部分。甘地在同他的一位传记作者路易斯·费希尔谈话时说自己在本质上是一个倾向于妥协的人,因为他从来不敢肯定自己占有真理。在甘地的自传中,他又说他对真理的激情使他认识到了“妥协的美丽”。当然,甘地一向反对策略性的非暴力,也反对为妥协而践踏原则。
尽管如此,萨提亚格拉哈并不是一种随遇而安的哲学。虽然甘地在其非暴力斗争早期将萨提亚格拉哈解释为“消极抵抗”,但经历了在南非的早期实践之后,萨提亚格拉哈在印度的实践已经日益表现为一种富有战斗性的、激进的斗争策略。甘地就是希望依靠这种斗争策略来改造世界,反抗邪恶和不公正。非暴力是“勇者的武器”,而不是“懦夫的盾牌”。将本书副标题中的“militant nonviolence”理解为“激进的非暴力”或“富有战斗性的非暴力”,似乎更贴近甘地非暴力思想的本意。
无论对于甘地还是甘地希望与其共同创造历史的追随者而言,萨提亚格拉哈并不能解释他们如何实现共同的目标。也就是说,如果萨提亚格拉哈仅仅是甘地一生动机趋势的一种实现,那么它又是怎样发展成为激发印度民众的一种历史运动呢?“真理的工具”又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工具呢?埃里克森再次提出了他颇有研究的“认同”问题。在这里,认同“既是‘定位’在个体核心的一种过程,也是‘定位’在他与别人共有的文化核心的一种过程”。因此,认同的核心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英国的殖民统治给印度造成了深刻的心理和感情伤害——甘地称之为“四重毁灭”,即英国在印度实施的政策对印度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精神都造成了伤害,也损害了印度认同。甘地青年时负笈英伦、其后又在南非生活21年的经历使他不仅经历了个体意义上不同人生阶段的认同危机与认同重建,也与其他印度人一样遭遇了如何定位自己与宗主国英国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些复杂的个人经历使他有资格以个体化的方式领导民众重建印度的民族认同。萨提亚格拉哈就是重建印度民众破碎的认同感的重要途径。于是,一些印度物品如使用本地棉花手工纺织而制成的“卡迪”(khadi)土布和手纺车(charkha),都被看作印度认同最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和标志。手纺车还很快成为国大党的标志之一,后来又作为印度的符号出现在了印度的国旗上。“像一位精通精神分析的专家那样,先是深入了解病人的过去,找出其各种情结的根源,让病人看到这些根源,从而去掉他的负担。”甘地使印度发生了“心理上的变化”,是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理对甘地贡献的一个准确评价。
心理史学的研究路径
如果将心理史学理解为心理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历史学是最容易感受到来自这一新领域的影响的学科,而心理史学受到历史学视角的审视和批评也就再自然不过了。与甘地生活在几乎同一时期的、印度争取独立历史上的其他重要人物,特别是代表印度穆斯林的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以及印度“不可接触者”的代言人阿姆倍伽尔(B.R.Ambedkar)在印度民众中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尽管甘地的非暴力抵抗得到了为数众多的印度民众的支持,但真纳和阿姆倍伽尔也不乏支持者。许多印度人接受了甘地以及他领导的自治运动,但并不是所有印度人都追随、接受甘地的领导。埃里克森从甘地的内心特别是贯穿其一生的“照顾”倾向研究甘地日益增强的使命感,这符合精神分析的逻辑却容易造成错觉,即在争取印度独立的问题上全印度只有一种声音,尽管埃里克森在前言部分就毫不讳言自己“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研究印度的专家”,但这样的研究还是使一些历史研究者感到困惑。当然,即使是从心理史学的视角来看,改变反对一方的态度和立场应该是非暴力抵抗的主要目的,而这一研究对于反对一方受到的心理与政治影响的描述和分析却非常有限。虽然与弗洛伊德在其研究中重视本我(id)的作用相比,埃里克森的研究更加注重从自我(ego)的视角展开分析,但对于诸如1918年阿赫梅达巴纺织工人罢工这样的事件,仅仅从自我以及同盟者的角度进行分析显然不能涵盖事件所有当事人的心理过程。这也是埃里克森的研究有时遭人诟病的地方。这些苛责或许很有道理,但对于埃里克森有关甘地的研究初衷,即探寻甘地“真理”中所蕴含的非暴力勇气的精神起源而言,埃里克森的研究应是无可挑剔的。
作为圣人与政治家之外的甘地
在为人们熟知的历史人物中,甘地是不多见的在年轻时即已声名显赫并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甘地早已被神化和神圣化,“甘地”似乎也已成为圣人的同义语,就连他的童年也被“甘地化”了。事实上,童年时期的甘地只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小男孩:一个淘气的孩子,一个在有点可笑的偷偷摸摸和有负罪感的气氛下和一群同样顽皮的小伙伴学着吸烟、吃肉的孩子……甘地自己也从不认为自己就是人们眼中的圣人。泰戈尔说过,应从一个人“一生中的最佳时刻,用他最高尚的创举,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来判断他”。甘地则认为:“对诗人而言的确如此,因为他让满天的星光降落大地。但对于我这样的凡人来说不该用他们一生中少有的辉煌时刻,而要用生命历程中落在他们脚上的尘埃来评价他们。”甘地总是以低姿态进入大众生活,他“对自身完美所持的质疑态度”使他贴近了普通百姓,大多数印度人感到自己和甘地心心相印,并为甘地的道德观所感动和骄傲。
有人说甘地是迷失于政治的圣人,而甘地则认为自己是努力成为圣人的政治家。实际上,在“圣人”与“政治家”之外,甘地还有更多乏人关注的侧面。
基于母性特征的“照顾”动机是埃里克森精神分析透视镜下甘地一生生活与事业的重要精神支点,而甘地身上比较明显的权威主义特征同样无损他倾心照顾他人的母性情怀。埃里克森注意到了甘地在与妻子嘉斯杜白及四个儿子关系中的权威主义人格特征。在南非生活时期,他就意识到家庭的责任会影响到他服务社会的人生目标,因此选择了一种“瓦纳普罗斯达”(vanaprastha,摆脱家事)的生活。他的妻子虽然总是幻想着过“正常”的家庭生活,但仍然努力过她丈夫选择的艰难的生活——向全世界打开家门,“努力把他的‘家’从照顾家眷转为设点招待同事和追随者,最后变成带有很多宗教秩序特征的农耕定居地”,与甘地一起过毫无隐私的生活。从新婚时企图逼迫小新娘读书识字,到要求妻子清洗住在他家的一位不可接触者的便壶,以及1901年当他下决心回国时要求妻子交出收到的珠宝礼物,“盲目的、迷恋的”丈夫甘地以自己的方式为妻子安排和设计生活,而妻子嘉斯杜白的自我克制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圣雄甘地及其事业。对于自己的儿子,甘地则要求最高又期望最低。他没有送他的几个儿子上学以接受与他一样的教育,但却希望他们能够效法他孜孜以求的生活方式。他设想由自己来亲自教育儿子和真理学院的孩子们,而实际上他在教育方面所能付出的时间又微乎其微。甘地所认定的真理或楷模使他的儿子们常常陷入极端的困境:当他们的真理意味着要反叛甘地的真理时,甘地会以不承认或断绝与他们的关系相威胁。甘地倾向于把最亲的人“当作私有财产和鞭笞柱”,这种“残酷的仁慈”以及甘地极度公开的生活使他的亲人们特别是他的孩子们不得不承受被遗弃、被忽视和缺乏保护的痛苦。
甘地不仅在家庭中是一个十足的权威主义者,在令他着迷的公共生活中,他也常常表现出一个权威主义者的诸多个性特征。在南非的托尔斯泰农场,甘地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让那些以淘气著称的男孩与纯洁的女孩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洗澡,以培养他们自我约束的责任。一天,有一个男孩洗澡时嬉笑两个女孩。甘地得知后训诫了那个男孩,并希望两个女孩身上要有些标记以警告每一个男孩不要再把邪恶的眼光投向她们。甘地彻夜未眠地思考用怎样的标记才能使女孩们有安全感,他想到让女孩们剪掉秀发。虽然女孩们最初难以接受,但最终还是支持了甘地。在凤凰村,他曾通过绝食一周,使三个“罪人”(一个女孩和两个男孩)注意到他受了多少罪。那个女孩和他一起绝食并让人剪短了自己的头发。甘地通过“自我选择”的受罪使孩子们感受到了惩罚。
甘地的这种人格特质也影响了印度的民族主义政治。1920年,国大党的那格浦尔年会标志着甘地的不合作策略在国大党内得到确认,也确立了他“比形式上担任最高职务更为巩固有力”的领导地位。甘地通过他力主成立的国大党中央执行机构——工作委员会强力推行其政治主张,并深入印度各地争取对其计划的支持。他的声望和影响力使他在退出国大党后仍然发挥强有力的幕后作用,对印度现实政治产生了无法忽视的实际影响,成为“国大党的无冕之王”。在争取印度民族独立的政治活动中,甘地表现出的说服、挑战、强制甚至威胁的作风显示了他权威主义的人格侧面,而这种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印度的王公传统。这样的人格特质不仅无损他为人们所熟知的更为“正面”的品质,还使甘地的形象更真实,使这位圣人更像一个亲切的常人、凡人。
重新发现甘地的必要
在《甘地的真理》英文版的扉页上,埃里克森写道:纪念马丁·路德·金。正是对非暴力的共同信仰使马丁·路德·金与甘地联系在一起。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如果他到印度旅行,那只不过是一次常人所做的普通旅行;但假如他有机会前往古吉拉特邦,拜访甘地的出生地,那将是他以圣徒的身份所进行的一次朝圣之旅。1959年,马丁·路德·金参谒了新德里的甘地墓。
一生孜孜于非暴力的甘地在暮年亲眼目睹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暴力冲突以及印度最终分裂的残酷现实,并死于激进的印度教徒之手。20年后,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又重复了他的命运,被暗杀身亡。他们的人生遭际以及甘地在独立后的印度既受到隆重纪念又常常被人遗忘的现实,使人们在受到甘地及其毕生追求的非暴力事业极大鼓舞的同时,也常常产生伤感和无奈的情绪。
人类目前已经具备了毁灭这个星球上一切生命的能力,而人类的理性、良知与克制将是确保人类安全与秩序的最终依靠。今天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不断重新发现甘地。
在精神分析的烛照下,埃里克森引领人们穿越时间隧道,完成了一次历史与心灵的印度之旅。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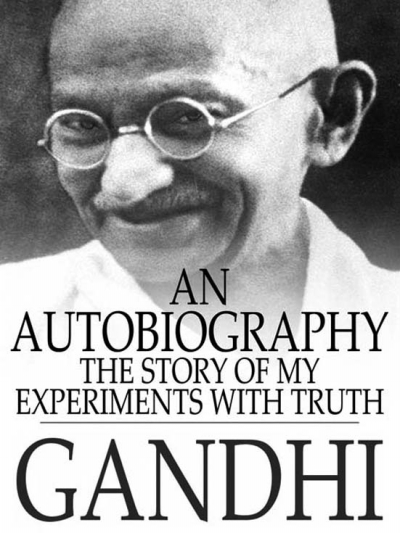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