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文学何为”成为一个屡屡被提及的话题,“世界文学”也越发彰显出它的独特意义。在上海交通大学和哈佛大学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期间,本刊特邀请中方代表团团长、清华大学王宁教授和美方代表团团长、哈佛大学戴维·戴姆拉什教授(David Damrosch)就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中国文学在全球文化和世界文学语境下的地位等问题进行了对话。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
王宁:您的大著《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2003)和《如何阅读世界文学》(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 2009)在中国学术界不断被人引证,而且这两本书的中文译本也将出版,您也成为中国文学界瞩目的人物。首先请您说一说,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有着鲜明的后现代消费文化印记的时代,人们经常说“文学已经死亡”,文学研究也受到严峻的挑战,世界文学对我们有何特殊的意义呢?
戴姆拉什:在我看来,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比以往更加需要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因为如今许多人的视野已变得更具国际性和全球性了,而且人们不断地跨越国界旅行,学术机构也愈加开放,中国学生大规模地到世界各地求学。我认为,在这方面文学提供给他们一个独特的机会来思考全球问题以及文化的内在生命。文学作品虽然从未直接地反映周围的现实,但这些作品却折射了这些生活现实,并在另一个与之密切关联的世界创造了它,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世界的内在张力和各种可能性的真正方式。当然,与世界文学相关的问题确实在三个方向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精英文学作品与有着更为广大的读者大众的通俗文学作品之间的张力。华兹华斯在1800年《抒情歌谣集序》中说:“莎士比亚的作品正在被进口的通俗文学的泛滥所淹没。”当时伟大的英国文学经典作品之所以不被人诵读,其原因恰在于人们均沉溺于阅读那些“病态的缺乏才气的德国悲剧作品,以及泛滥成灾的拙劣小说”。
所以今天的问题就是,大量的通俗文学作品涌现以及阅读标准和阅读兴趣转变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另一个机会就是人们把阅读文学的方式转向了因特网。尽管如此,在我看来,对于作家来说这仍是一个很有希望的时刻,原因之一是,文学正在整个地进入一个多媒体的空间,而这正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一直得以生存的地方。大多数文学在一开始并不是写出来供单个读者阅读的。文学始终是社会的一部分,不管是那些唐朝诗人聚在一起饮酒作诗,还是临别赠诗,诗歌几乎就是一种社会交往的媒介,同时也是私人的审美乐趣。因此我认为,我们也许正在通过社会接触走出那个把高雅艺术当作日常生活的牺牲品来看待的、简单的、人为造成的时期。
任何伟大的变革总是使一些作家受益,使另一些作家受挫,也许一些十分重要的作家会退却,而另一些作家则会通过这些变化而受益。尽管华兹华斯曾担心无人阅读莎士比亚,但莎士比亚并没有因为华兹华斯时代通俗小说的崛起而相形见绌,反倒被更多的人阅读和翻译,因此我认为假如莎士比亚今天还活着的话,他或许也会为电视连续剧撰写脚本,他也会改编自己的剧作,他在今天的观众会比任何时候的都要多。
王宁:我也有类似的看法。在如今的时代,文学似乎不像以往那样受人欢迎,因此很多人便把关注的重点转向通俗文化、互联网或电视等等。尽管如此,在我看来,物质生活越是丰富多彩,人们就越是试图从精神生活中获取营养。文学自然应当向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精神食粮,我们也可以据此培育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准则。另一方面,既然我们阅读世界文学,我们就应当推出一些优秀的作品,不仅仅在某个国家流通发行,而且应该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都流通和发行。因此我认为,我们实际上也在以一种批评的方式挑选并欣赏不同的作品,这样也能从这些作品中得到远比浅薄的通俗文化和消费文化所能给予的更多的东西。我不知道您是否也有同感。
戴姆拉什:我完全同意您的见解。我听说在过去的十年里,不少中国作家受到利益的诱惑去写通俗小说,而且当下大多数中国小说都不是严肃的文学作品,而是通俗文学。您认为这是公正的理解吗?或者说您能告诉我当今一些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作家吗?
王宁:我认为,在当今中国有三类作家。第一类如同您刚才所说的,专门写一些通俗的主题,试图以此来谋取利益。他们大概占全体作家的三分之二。许多作家不努力写出优秀的传世佳作,而是试图通过写作来赚钱,他们总想从日常生活中获取一些耸人听闻的事件来大加渲染,或刻意对经典作品进行戏仿,这样他们一方面解构了既定的文学经典,另一方面则可以吸引大众读者的眼球。第二类作家则是严肃的作家,他们虽然为数不太多,但却仍然潜心写作,诸如韩少功、余华、莫言、王安忆、徐小斌、阎连科、贾平凹、格非、苏童等。他们也许并不像以前那样拥有大量读者,但他们确实在努力写作,试图发表最佳作品。当然,他们也受到大学教师、学生以及批评家的阅读和研究。第三类作家不仅为艺术而创作,同时也为市场而写作。他们一方面写作一些严肃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也撰写影视脚本,这样就能挣些钱来解决日常生活所需,来专心从事严肃文学创作。所有这三类作家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全貌。
戴姆拉什:这种情况和美国也差不多。在美国,许多畅销书都是侦探小说、间谍小说以及历史传奇。我查阅了上世纪50年代美国的畅销书目,竟发现不少有着较高艺术品位的小说居然也在畅销书目中,这些作家包括纳博科夫、菲利浦·罗斯和塞林格,他们的作品已被公认为经典,而且十分受欢迎,它们既是畅销书,同时也被当作重要的虚构作品来接受。但当下的畅销书榜却没有那种高品位的作家。
但在我和一位朋友交谈时,她指出,实际上这一差别是由于现在有更多的普通人在阅读。他们总是喜欢侦探小说,因而有那么多的侦探小说充斥市场。并不一定是高雅文学作品的市场销量变得更少了,因为基本的读者也在扩大,但还是那些畅销书更受欢迎。但我认为,我们将看到在那些具有艺术性的小说中,某些作品确实也起到了真正给人精神价值的作用,同时也促使人们对当前的世界进行心灵和智性的思考与理解。在维多利亚时代,大多数人都阅读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他们也像阅读那些侦探小说那样读他的书,也像观看电视连续剧那样专心致志地阅读,因为他们那时还没有电视剧,他们不得不阅读狄更斯。实际上,如果人们真的想看电视剧的话,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现在有电视剧了,伟大的艺术家可以利用流行的媒体使自己的作品变得更为人所需。
王宁:确实如此,中国当代的情形与此十分相像。有些古典文学作品通过影视的手段变得更为流行,有些被边缘化的现代经典,尤其是那些“红色经典”,通过影视的中介也再度十分流行。但那些翻译过来的文学作者,如塞林格、纳博科夫和菲利普·罗斯等照样在普通大众中深受欢迎,特别是《麦田里的守望者》,它的发行量已经超过20万,而且还有不同的版本。塞林格去年去世时,有更多的媒体炒作这部小说。
戴姆拉什:这倒很有意思。作者的去世倒成了他的作品销售的一个新动力。
何为“世界文学”
王宁:第二个问题是:世界文学的内涵是什么?这个概念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是如何发展演变的?您认为仅仅为世界上不同民族和国家的读者阅读的作品就可以称为世界文学吗?或者说正如您所指出的那样,文学必须是虚构的、有价值的,同时也是优美的?这其中自然隐含某种价值判断的意味。
戴姆拉什:“世界文学”这一术语可以追溯到伟大的德国诗人歌德,他在19世纪20年代发展了“Weltliteratur”这一术语,这多少是一个新颖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指文学流通的国际性,同时也指不同的作家在国外得到的反应。歌德是19世纪第一位在现代世界文学中流通并受益的作家,因为在他年迈时,他已经逐渐在保守的德国失宠了,被认为陈旧了。他去世后作品在国外具有那么大的世界性声誉,随后又在德国倍受欢迎,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作品在国外的流通。世界文学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就在于它必须得到很好的翻译,有些优秀的作品未得到很好的翻译,这就意味着它不可能在国外市场打响。
王宁:我也有类似的看法,世界文学不仅仅需要流通顺畅,而且要有好的翻译并得到好的评价。但另一方面,我也在很大程度上作了些发挥。根据我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判断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必须依循一些客观的标准,即应同时兼顾普世性和相对性。
首先,它必须通过翻译的中介超越自己的民族、国家以及语言的疆界。其次,它必须被收入那些具有权威性的世界文学选集,因为更多的人并没有很多时间去一本一本地阅读小说,他们宁愿花时间去读文学选集。这样,文选就同时含有经典性和可读性两种因素。再者,即使它被收入文学选集,也并不一定在普通读者中深受欢迎或为后代作家所继承。如果它能被用作大学教科书或主要参考文献,将得到大批受过教育的读者的欣赏。第四点就是,这位作者必须得到批评性的反应甚至引发争议,因为有很大争议的作品也意味着它具有一定的批评价值。另一方面,在编选世界文学选时,我们也应该考虑到不同的国家分布,而不能像杜威·佛克马所描绘的那样,在一部由法国学者编写的文学史中,中国文学只占130页,而法国文学所占的篇幅却是其12倍。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由此可见,在编选世界文学选的过程中也隐含着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倾向。我想知道您是否同意我的这一看法。
戴姆拉什:当然同意。我一直在花很多时间从事文选编辑的工作,一开始是庞大的英国文学选,接下来就是那部六卷本《朗文世界文学选》。在这方面我们的见解有所不同,因为您强调的是接受和对话中的某种权威性,而我则在很大程度上旨在描述世界文学的杰作。在我看来,另一些模式也可以被看作是世界文学。在我的《什么是世界文学?》中,我描述了世界文学的三种基本模式,即一部文学作品可以是经典的作品,或杰出的作品,或作为观察世界的窗口。经典文学往往指古代具有权威性的作品,如儒学经典就是如此,维吉尔和荷马也是如此,这些作家的作品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作品;然后就是那些现代的但并未有定论的作品,杰作确实是歌德定义世界文学的基本观点,因为那些作品确实艺术上是优秀的,即使在今天这些作品也在流通并得到读者的认可;但也有一类作品,即使没有伟大的文化传统,也没有一篇书评能够认可它,但它毕竟被译成了多种语言,那也可以被看作是世界文学。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现代文学市场的作用,伏尔泰的《老实人》在出版的第一年就被译成十种语言,甚至在当时并未被收入任何文选,也没有受到任何批评性反应,但竟也成了世界文学,其原因就在于它的流通,在于它的意义和品质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我认为文学作品作为观察世界的窗口的观点在今天十分有意义。世界文学的读者可以得知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另一种文化是何种模样。在我看来,能够产生世界文学作用的作品是基于个体的经验的,因为它在读者面前展现出另一个世界。我作为一位文学编辑者,扮演的作用是双重的,因为在我的文选中占据大部分篇幅的作品几乎完全符合您的标准,即它们是经过时间考验的名著,得到大量的批评性反应,并且得到诸如但丁或《红楼梦》等杰作那样的评论。应该说这些作品占据了绝大多数的篇幅。但是我也收入了一些我十分感兴趣的作品,比如一些从未被收入任何文选的诗歌,我认为这也是世界文学,我希望有人去读它。这最终改变了您的标准,但我希望有人对其作出批评性反应并翻译它们。我认为这就是现在的世界文学。
我认为重要的是扩大学生的视野和疆域,我们需要作些翻译,因此我们同时也把那些没有得到很好翻译的作品重新翻译出版,因为翻译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使读者的阅读更加广泛,因为我们都发现,许多人仅仅满足于阅读有限的几部经典作品,但是他们并没有超越老师教给他们的方法,没有带着好奇心去阅读它们。因此我认为正是这一令人兴奋的“世界文学时代”给了我们新的语境、新的方式去考察这些作品,将其与跨越疆界的别的作品关联会十分有意义。
王宁:我想您的侧重点是作品的可读性,而我则同时注重作品的可读性和经典性。这样,我想我们对于世界文学的看法几乎很接近了。
戴姆拉什:只是在共同的框架中的具体侧重点上的差别而已。
王宁:我们还可以发现,文选编辑者也能够帮助一部文学作品成为经典,就好像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所声称的那样,有时他们将诺奖授予某一位不知名的作家从而使他成名,成为经典作家。尽管他们试图论辩,经典性并非他们的目的,但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某一位作家,这一行为本身至少有助于那位作家更加受读者和批评家的关注。
戴姆拉什:那倒不见得如此。我们作出这一经典意义的判断是因为我们需要写出每门课的教学大纲,因此教师们就选择一组应该去读的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这虽然有争议,但无论如何,我们不会包括那些微观经典(microcanon)、暂时经典(temporary canon)作品,因为这也许会影响我们下一次再上这门课。每一位文选编者都应该意识到我们得为那些值得人们去读的作品争得权利,质量肯定是绝对重要的,但也并非单方面的。要使世界文学值得人们拥有,它们必须是引人注目的作品,而引人注目的品质必定包括不同的方面,也就是说,它们必须向我们提供重要的审美体验。
走向世界文学阶段的比较文学
王宁:我们现在讨论第三个问题。人们现在总是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相关联。实际上在中国,早在1998年,教育部在调整学科目录时就已经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两个二级学科合二为一了,这个学科的名称就叫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开始,国内一些比较文学学者还为此争论过,他们认为,比较文学在西方早已成为单一的学科,为什么要把世界文学合并进来呢?但现在我们发现,比较文学的最早阶段就是世界文学。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比较文学学科也被人认为已经“死亡”,但是新的比较文学却在这时诞生。因此我认为这个所谓的新的比较文学应该被称作“世界文学”。这也是为什么我精心设计了我们这个“走向世界文学阶段的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因为在我看来,比较文学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实际上帮助被认为处于危机阶段的比较文学走出危机的境地。再者,这也是为什么不仅在中国而且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参加比较文学会议。您说是这样的情况吗?
戴姆拉什:是的。在过去的十年里,参加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的人数已多了十倍,而且越来越具有国际性。15年前,提交年会的论文有150篇,其中只有三位学者来自美国以外的地方。而去年在哈佛,我们主办了一届年会,共有2100名学者提交了论文,与会者来自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印度以及中国等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我想强调世界文学的比较文学有这样几个特点:经典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研究应当还在做,例如传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研究依然注重两国之间的文学关系,并对它们的传统进行比较研究,例如考察一国的形象在另一国的再现,这主要是法国和德国的状况。这种研究仍然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进行。但我认为,现在对世界文学的强调则有着不同的计划。大多数民族的传统都来自更加广阔的区域环境,并受到国际交往带来的滋养。鲁迅就是一个杰出的范例。他通过阅读日语和德语学到很多东西,他也做了不少翻译,据说他翻译了上百部作品,他通过日文翻译了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并写出了自己最有名的小说《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最有名的奠基人之一,鲁迅就是一个世界文学人物。还有胡适,他也对比较文学很感兴趣,他曾经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在那里获得了博士学位然后回到中国。他们的著作在不同的学术机构之间流通得很好,使大家共同受益。
王宁:对,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三年一度的年会始终对外国学者开放。在每次的年会上,我们都邀请不少外国学者,尤其是来自西方和日本、印度等周边国家的学者,但我们的国外与会者还未达到五十多个国家,在最多时有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学者与会。我们总是鼓励我们的同事进行超越本国和本语言环境之外的文学研究。实际上,如果说比较文学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危机的话,那么世界文学已经帮助比较文学走出了危机的境地。同时,我在我所参加过的一次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发现,世界文学也是一个讨论得十分热烈的话题,尤其是在苏源熙题为《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的十年报告中,世界文学被不断地提及。您认为是这样吗?
戴姆拉什:对。
王宁:还有一个问题,世界文学选或国别文学选的作用是什么?是否应同时兼顾经典性和可读性? 我想请您说一说您在编选《朗文世界文学选》时所依循的选文标准。您是否认为质量应该始终居首位,还是仅仅考虑到民族—国别文学的分布?
戴姆拉什:在《朗文世界文学选》中,当我们确立选目时我们有一些主要的目的。其中一个便是力图超越以往在美国出版的世界文学选的欧洲中心主义,那些文选一般只收入西欧文学,或加上一些美国文学。因此当世界文学被用作一个术语时,其意义十分狭窄。像《诺顿世界文学选》,最初出版于1956年,仅局限于西欧文学,尽管后来逐步开放,但也范围有限。因为这些文选多是专供欧美大学生用的文选,而老师们通常更喜欢他们已经教得比较熟的作品,而不一定追求新的东西。因此朗文文选以及最新一版的诺顿文选就选了三分之二的西方作品,三分之一的非西方作品,全书共6000页,其中4000页为西方文学,另2000页为非西方文学。我知道这仍然是不平衡的,但是我们得在一系列限制中工作,例如当前教师的训练程度以及他们希望教什么样的作品等等。此外他们还试图提供一些不同地方的文化接触,我们围绕一个问题把不同的文本放在一起以便起到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作用。当然,我们始终重视翻译的质量并力图得到好的译文。
王宁:您的意见很好。最后一个问题:作为在美国大学任教的比较文学学者,同时您也对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十分感兴趣,那么能否请您告诉我们目前中国文学在全球文化和世界文学语境下的地位究竟如何?如果这一现状并不令人满意的话,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呢?您作为《朗文世界文学选》的创始主编,在您主编的文选中收入了多少位中国作家及其作品?
戴姆拉什:我们在朗文文选中收入了大约23位中国作家的作品。入选的古典作品包括孔子、老子、庄子的经典文本,还有唐诗以及《西游记》和《红楼梦》的精彩章节——这两部小说每部都选了大约75页。我们还选了一些晚近一些的作品,我认为我们今后需要做这样的工作,我们要发现哪些是当代最有意义的短篇小说作家。我应该承认,在美国,日本现代小说比中国现代小说更广为人知,为什么市场更早地接受日本,我想这肯定有很重要的原因,也许几十年前就有了很多接触,或者说是由于日本与美国、美国与中国之间文化和政治上的原因吧。现在正是大力加强文化交流以及中国文学在美国流通的大好时机。我想您知道现在的读者有一部分乐趣是发现世界上的不同地方,美国学生对此也颇有兴趣。土耳其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罕·帕穆克的作品居然被译成56种语言,他来自一个小国,其语言也不甚流行,而他却成了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获得了广大的国际读者,远远超过了他在土耳其的影响。
王宁:因此翻译是十分重要的一种媒介。我的一些同事始终认为,中国文学之所以在全球文化和世界文学的语境下被边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翻译的缺失,您认为翻译是唯一的原因吗?
戴姆拉什:当然不是唯一的原因了,还有东方主义也导致人们对中国的忽视。现在人们对当代的事情很有兴趣,作为一位文选编辑者,我主要关注另一个方面。美国人往往只有很短的历史记忆,因此所有的倾向都是试图知道什么是新的东西,我必须让他们去阅读杜甫和老子。
王宁:作为一位文学编辑者,您确实为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普及和推广作了很大的努力。我们衷心地感谢您!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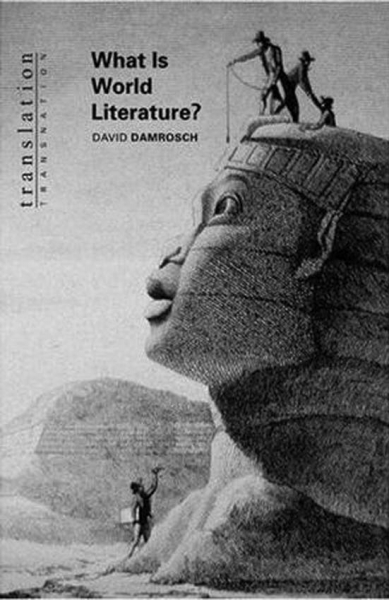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