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东晋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的民族融合时期,正是这一时期,产生了一个浓缩中国文化特质且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词语——“中华”。“中华”一词始见于西晋末,是“胡人”大举进入中原的背景下,中原士人为把中原的政治与文化同“胡人”相区分而产生的自我称谓,故“中华”乃胡汉互动的产物。但入唐以后,“中华”一词被广泛使用,不仅成为唐朝的别称,也成为中国名号。这意味着当初为与“胡人”相区分而产生的“中华”称谓及概念已发生根本变化——成为胡汉融合体的一个统称。“中华”始于胡汉区分,却终于胡汉的融合,胡汉融合正是认识“中华”概念的起点。“中华”是较宽泛的文化概念,“中华”之“华”具有以“衣冠礼乐”喻指文化的象征意义,这使“中华”概念具有极大的包容度和开放性。这是后来“中华”所指称的共同体得以不断扩大的原因。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两个大规模、长时段的民族融合过程。一个是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一个是宋、辽、金至元明。这两个民族融合过程均以分裂与统一交替的模式进行。导致分裂的原因是民族之间的剧烈冲突与对抗,经过长期冲突、对抗,各民族之间逐渐磨合、适应并相互吸纳,联系日趋紧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又为统一奠定了基础。所以,经过长期分裂又逐渐走向统一。在统一时期,各民族及其文化以和平方式进一步交融、整合,并最终在心理和意识上熔铸为一个整体,民族融合的成果通过比较安定的统一时期而日臻成熟、巩固。这大致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主要特点和一般规律。过去,我们多习惯于把历史上的分裂时期看作民族融合阶段,把统一时期看作民族融合的结束,这一认识显然存在偏差。事实上,从分裂到统一才是民族融合的完整历史过程。从此观点看,东晋南北朝至隋唐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一个完整过程。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一个浓缩中国文化特质且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词语——“中华”。
从“中华”一词的使用看其性质与背景
人们之日常话语中的“中华”一词始见于记载两晋南北朝史实的史籍中。这些史籍有《晋书》《十六国春秋》《宋书》《南齐书》《周书》《魏书》《昭明文选》《北史》《南史》等,它们或是两晋南北朝时期成书的史籍,或为记载两晋南北朝史实但却成书于唐初的史籍。而在此之前史籍中,目前尚未发现“中华”一词。据此基本可以断定,“中华”一词是产生在两晋南北朝时期。
那么,在当时的社会领域和人们日常话语中,“中华”一词的最初语义是什么?它是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下被使用?对此,首先需要了解当时人们是怎样使用“中华”一词的。《晋书·桓温传》记有东晋大将桓温的一段话:“自强胡陵暴,中华荡覆,狼狈失据,权幸扬越。”桓温为东晋时率军北伐的著名将领,从“中华荡覆……权幸扬越”的语境看,“扬越”尚不在“中华”范围。故桓温所言“中华”,乃指长江、淮河以北的广大中原地区。桓温在《荐谯元彦表》中亦云:“中华有顾瞻之哀,幽谷无乔迁之望。”亦言胡人占据中原地区。《宋书》记晋室南渡后,史臣言及东汉张衡所造浑天仪时曾慨叹道:“(张)衡所造浑仪,传至魏、晋,中华覆败,沉没戎虏,绩、蕃旧器,亦不复存。”“中华覆败,沉没戎虏”一语,清楚表明“中华”是指时已“沉没戎虏”的中原地区。
以上话语均出自永嘉之乱后南迁的东晋、南朝朝臣及士人之口,可见在当时东晋、南朝朝臣及士人中,“中华湮没”“中华覆败”“中华有顾瞻之哀”“中华荡覆”是一个很普遍的说法。他们所言的“中华”,大致包含两个语义:其一,“中华”指晋室南渡以前的广大中原地域;其二,“中华”是相对于“强胡”“戎虏”而言。其实,当时中原地域仍然存在,只因被胡族占据,故有“中华湮没”“中华覆败”“中华荡覆”之慨叹。从此语境看,“中华”与“强胡”“戎虏”的界线乃泾渭分明。永嘉南渡后,“中华”还出现了另一个语义,这就是将原晋朝统治下中原地域的朝臣、士人统称作“中华人士”“中华之士”“中华朝士”。
综上,从当时对“中华”一词的使用来看,可以发现如下事实:第一,“中华”用以指原晋朝统治下的中原地域;第二,“中华”一词用以称谓原晋朝的朝臣和中原士人。第三,使用“中华”一词的人主要是南迁或未南迁的原晋室的朝臣和中原士人。从上述三点看,当时“中华”一词的含义主要同西晋王朝相关。西晋丢失的中原地域和原西晋朝臣、中原士人均被冠以“中华”称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使用“中华”一词的人也多是南迁或未曾南迁的西晋朝臣及中原士人。如果说,“朝臣”是代表政治,“中原士人”更多代表文化,那么,“中华”的基本含义则是指称原西晋王朝的地域、政治与文化。王树民亦云:“‘中华’名号不仅表示一定的地域,更表示一定的文化和具有这种文化的人。这一点为其他各名号所不及。”从这一基本涵义,可大体明了“中华”一词的性质及产生背景。以此判断,产生“中华”一词的社会背景,应当正是晋室南迁这一政治、文化大变局。换言之,“中华”一词的出现与使用,从根本上说应是“胡人”大规模进入中原地域的一个结果。
在“胡人”大举进入中原地域的背景下,中原方面客观上需要有一个简约、明晰的自我称谓,来把原晋朝统治下的中原地域及以该地域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及社会传统同胡人及其文化相区分。也就是说,“胡人”作为“他者”的大规模进入,进一步激发了“我者”即中原士人的自我意识,这样,中原方面客观上即需要有一个既包含自我意识与文化认同又能高度概括自身特质的名号,来作为与“胡人”相区别的标识。这是“中华”一词应时而生的文化机制。
唐代以“中华”作为唐朝别称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经历东晋南北朝近400年分裂局面,南北重归于统一之后,“中华”涵义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尤其在入唐以后,“中华”一词开始广为流行,不但成为唐朝的别称,很大程度也成为中国的名号。
在记载与周边各政权的交往中,唐人的话语普遍以“中华”来代指唐朝。贞观十五年(641),李道宗送文成公主到吐蕃,吐蕃“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渐慕华风”。可见“华”已作为唐朝的代称。贞观时,给事中杜楚客在谈及北方突厥时云:“今令其部落散处河南,逼近中华,久必为患。”“逼近中华”,意指逼近唐朝直辖的疆域。
在唐朝的法律条文中,同样以“中华”来代指唐朝。例如《唐律疏议》规定:“造畜蛊毒,所在不容,摈之荒服,绝其根本,故虽妇人,亦须投窜,纵令嫁向中华,事发还从配遣。”可见在贞观时期已把“中华”作为对唐朝的称谓写入法律条款,这反映李唐统治集团心目中以唐朝为“中华”的意识在唐初已甚为强烈。把“中华”作为唐朝的称谓正式写入法律条款,一方面表明以“中华”称谓唐朝的说法在唐初已很普遍,同时此举对“中华”一词在唐朝的流行和推广无疑起了重要促进作用。
唐朝以“中华”自诩,还充分体现于唐太宗有关“中华”与“夷狄”的一段论述:“朕践阼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唐太宗这一番话,显然是以“中华皇帝”身份与立场来说的。贞观时唐朝处于向外开拓的全盛期,在周边各邻近诸部中声威显赫,时“西北诸蕃咸请上(唐太宗)尊号为‘天可汗’。”这是唐太宗出此夸矜之言的背景。但另一个更重要的背景是,李唐统治集团承袭“北方胡统”的关陇集团为核心,他们是北魏、北周以来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北方胡族上层集团的代表。入唐以后,以唐朝皇帝为代表的李唐统治集团竭力以“中华”自诩和自居,一方面表明其对“中华”的主动接纳与认可,另一方面也有藉此淡化和模糊李唐统治集团之胡族身份的意图。有唐一代,“中华”一词的普遍流行,特别是被作为唐朝别称的广泛使用,恐与此背景即李唐王室的主动提倡有极大关系。
唐太宗表述的“华夷观”虽不排除存在个人胸襟及思想开明的因素,但这种全新的“华夷观”归根到底却是时代的产物,是两晋南北朝以来胡汉大规模融合的一个结果。可以认为,胡汉融合因唐朝的大一统而日益呈现出一种包容胡、汉和华夷不分的全新时代气象。这种全新时代气象,很大程度正体现于“中华”一词当时作为中国名号与唐朝别称的广泛使用。
“中华”概念的特点与内涵
一般以为,“中华”是由“中”和“华”两个概念组合而成。“中”是“中国”之意,这一点无疑义;但对“中华”之“华”的含义,一些学者将其理解为“华夏”,认为所谓“中华”一词,即“中国华夏”之意。事实上,从当时人们使用“中华”一词的语境看,这种理解不但流于简单、片面,且存在明显的偏差,并不符合当时人们所言“中华”一词的本意。那么,“中华”的“华”究竟是何义涵?
有一现象很值得注意,东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华”“中华朝臣”“中华之士”等称谓出现的同时,还出现一个与之相类的称谓,即“衣冠之士”,指中原士人。“衣冠之士”这一称谓,正是入唐以后唐人将永嘉之乱中原朝臣、士人与世家豪族的南迁称作“衣冠南渡”的缘起。
“华”字最早出现于西周金文,本意是“花”。《诗·小雅》有“常棣之华”“裳裳者华”,故“花”均作“华”。汉代孔安国《尚书·武成》注曰:“冕服采章曰华。”由光华、鲜美之义引申于文化,“华”遂有以服章之美来喻指文化之高的含义。这正是以“衣冠”来称呼“中华士人”之缘由。陈连开已注意到“衣冠”与“中华”一词之间的关联性,指出:“‘中华’用于人事、文化、民族,最初大概因‘衣冠华族’而发生,扩而大之,指‘礼乐冠带’这种中原传统文化和具备传统文化的人。”这是很有见地的判断。倘“中华”一词确因“衣冠华族”而发生,那么,“衣冠”即是对“中华”的一个象征性表述,具有以“衣冠”即“服章之美”来喻指文化的涵义。这同国学大师章太炎将“中华”一词释为“以为华美,以为文明”的含义完全吻合。
这充分显示“衣冠”具有象征中原政治、文化之喻义,而“衣冠之士”正是用“服章之美”来喻指中原地区具有政治身份的朝臣和具有文化身份的士人。所以,在当时的语境中,以“衣冠”即“服章之美”来喻指文化之高,正是“中华”之“华”的真正内涵。
综上所述,“中华”的真正内涵是“衣冠礼乐”,是由“衣冠”所代表和象征的礼义、文化与文明。这一特点和内涵,无疑赋予了“中华”概念极大的包容度和开放性。“中华”不是一个民族或族别称谓,其时与“中华”相并行的尚有“汉人”“汉儿”“胡人”“鲜卑”等族别称谓。因此相对于民族称谓而言,“中华”是一个包含地域、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及具有这些因素的人的广义文化概念,它具有较为宽泛、有包容度、边界开放且模糊等特点。正因为“中华”一词的边界开放且模糊,不对胡族设限,胡族对其亦无明显的抵触与排斥。
文化不是抽象存在的,而是附着于人并通过人的活动来发生作用。这一时期北方胡族逐渐融入“中华”,离不开一个关键的中间媒介——即代表着中华“衣冠礼乐”的“中华士人”“衣冠士人”。胡族统治者对“中华”的认同和不断趋向“中华”,正体现于对“中华士人”“衣冠士人”的倚重并通过他们来得以实现。钱穆先生将胡人接受中原文化总结为两点:“诸胡杂居内地,均受汉族相当之教育,此其一。北方世家大族未获南迁者,率与胡人合作,此其二。”第一点为胡族进入中原之背景,但晋室南迁后,“北方世家大族未获南迁者,率与胡人合作”则是当时极普遍的现象。史籍中胡族统治者不遗余力网络、寻求衣冠士人的记载比比皆是。无论十六国,还是北魏、北齐、北周,均有相当数量中华衣冠士人参与权力中枢,他们为胡族统治者所依重并发挥着关键作用。事实上,中原衣冠士人在北方政权中往往起着决定政权方向的关键作用,他们既是北方政权趋向“中华”的引领者、谋划者,同时也是为胡族塑造“中华”身份并推动其一步步融入“中华”的关键力量。
显然,胡人对衣冠士人的倚重及中原衣冠士人“率与胡人合作”,既体现了胡人对“中华”的积极接纳,也体现了“中华”所喻指的文化之包容度与开放性。这种包容度和开放性正缘自“中华”是一个较宽泛的文化概念。“中华”能在唐代成为新的胡汉融合体的统称,正由此概念的这一特质所决定。
综上所述,“中华”一词始于胡汉的区分,却终于胡汉的融合。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根本原因在于“中华”一词并不是一个狭义的“汉人”概念,而是一个较宽泛的文化概念,它的边界开放而模糊,既不对胡族设限,胡族对其也无明显的抵触与排斥。特别是“中华”之“华”所具有的以“衣冠礼乐”来喻指文化的象征意义,给“中华”这一概念带来了极大的包容度和开放性。入唐以后,“中华”一词作为唐朝别称与中国名号被广泛使用的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华”概念的实质是“华夷融合”。从很大意义上说,这正是后来历史发展中被“中华”所称谓的人们共同体得以不断扩大的原因。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石硕)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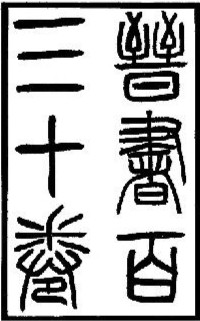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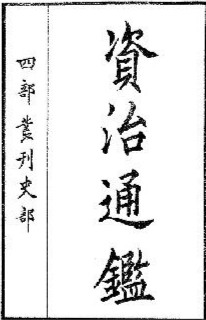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