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出门时突然下起了小雨,淅淅沥沥,甚无止意。昨天与杨苡先生通过电话,她是守时的人,我不能爽约;更何况,这次准备讲述的内容是她数月之前就拟定好了的,那一件件往事、一个个场面,一定在她的脑海里盘旋了许久许久。推开房门,杨先生果然已经穿戴整齐,半靠在床头等候着我了。
剧院的后台,对于每一位观众来说,都是神秘而不可测的:那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那里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杨先生正了正身子,开始了她的讲述:“告诉你吧,什么样的后台,我都看见过!”
从后台的厕所讲起
以前,我也曾多次听杨先生说过,由于家庭的影响,小小年纪的她就跟随着大人们进戏院看戏了。“那是位于天津日租界的新明大戏院,唱的都是京戏。”我笑了,“您能看懂吗?”她也笑了,“四五岁的孩子,一窍不通。”
一天,她实在是坐不住了。台上武生们闹闹哄哄的打斗,她不感兴趣;青衣花旦们咿咿呀呀的唱腔,让她昏昏欲睡。她吵着要解手,女佣只得带着她到处寻找厕所,就这样,两人误打误撞地闯入了后台。
“当年的戏院,并不像今天的剧场,将厕所设在观众厅两侧的安全门后边。它是既无指示牌,也无带路人,害得我们俩转了一大圈才发现,它竟然悄悄地藏在舞台的后边!门口没人看管,什么人都可以使用,除了演员,也包括看戏的观众……我从来没见过如此简陋的卫生间,没有抽水马桶,一律是蹲坑,连个挡板都没有。只见一个个穿着戏服、勾着戏脸的演员们,前前后后地走了进来。刚才在台上还是位婀娜多姿的小姐,或是位羞羞答答的玉女,此时此刻居然裙子一撩,无人般地蹲了下去……”
这就是杨先生今天讲的第一个故事,让我笑得直不起身来。
“这就是我对后台的第一个印象,准确点儿说,应该是认识吧——后台的演员跟前台的观众一样,都要上厕所;后台的厕所也跟普通百姓的公厕一样,都是蹲坑。彼此之间的区别仅仅是:他们在台上演戏,我们在台下看戏。他们认认真真地表演,我们恭恭敬敬地欣赏。戏演完了,观众们起身向他们鼓掌叫好,他们则向全场的观众鞠躬表示谢意。”杨先生所讲的这个故事,应该发生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转瞬间,将近一百年过去了。她已经忘记了演员的名字乃至戏码的内容,但她却清楚地记得:后台并不神秘,演员并非另类,她有点儿喜欢上了他们。
话剧团的后台
如果说,杨先生对于后台的第一印象是通过一个孩童的眼睛获得的话,那么,她第二次进入后台,已经是天津中西女中高一年级的学生了。“那是1935年……”杨先生喝了一口水,开始讲她的第二个故事。地点依旧在天津日租界的一个戏院里,但台上演出的却是她盼望已久的被称之为“舶来品”的话剧。
“那是中国旅行剧团前来天津巡回公演,光是《雷雨》一剧,我就看了三遍。而且还大胆地写了一篇观后感《评中国旅行剧团〈雷雨〉的演出》,在天津的《庸报》上发表了!”
这段故事,杨先生已经讲过许多遍了,这一次的重点一定是在后边。果然,她掏出手帕擦了擦眼角,话题立即转移到了今天的主题:后台。
“我和几位同学从侧幕边悄悄地钻了进去,嘴上说是找厕所,实际上是好奇,就想看看那些深深地打动了我的演员们在后台究竟干些什么。”
于是她们东张张西望望,蹑手蹑脚地在各个角落转了一圈,奇怪的是并没有人注意她们,大家都在静静地等候上场。“后台是那样的安静,一点儿不像我十年前看到的京戏班子。陶金在默默地背诵着他所饰演的周萍的台词,忽而仰头,忽而低首,在狭窄的后台走来走去,仿佛进入无人之地;唐若青坐在镜子前面化妆——她剪下一小块黑纸,贴在了门牙上,刹那间,一个豁着牙齿的老妇人,亦即那个饱经沧桑的鲁妈便活生生地出现了;只有赵慧深——那个既让人可怜又让人可畏的‘繁漪’,从我面前走过时回头看了我一眼,大概她猜出了我就是那个写观后感的小丫头……”
这场“探奇”,最多十分钟的时间,却让杨先生牢牢地记住了一辈子:话剧是一门严肃的艺术,表演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什么是后台?那是演员们备战的场地,那是神圣不可玷污的地方。
应该说,就是从这一刻起,杨先生和演员们交上了朋友。尽管家教严厉的母亲始终反对,但她却从不视他们为“戏子”,而是当作亲密无间的知己。“我尊重他们,因为他们尊重艺术;我热爱他们,因为他们热爱艺术!”
中央电影摄影场的后台
杨先生将头倚靠在了身后的枕头上,她累了,微微地有些喘息。我静静地坐在她的身边,注视着她那祥和的脸庞,回味着她刚刚讲过的话。突然间,她睁大了眼睛,并且一把拽住我的手,“我还没有讲完!你万万想不到,我还看见过这样的一种后台——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后台!”
杨先生的第三个故事又开始了。那是1939年,已经是西南联大外语系二年级学生的杨先生利用暑假的机会,和同学们一起到昆明的滇池去游玩,正巧碰上了中央电影摄影场在那里拍摄故事片《长空万里》。这是一部讲述一群爱国青年逐步走向抗战前线,最终献身于航空战线的片子,导演是孙瑜,演员有金焰、高占非、白杨、魏鹤龄等。“这是我第一次看拍电影,大家远远地围了一个圈子,静悄悄地,屏住了呼吸。”
“我的好奇,并不在白天的露天拍摄,而是在晚上的演出。可能是为了宣传民众吧,天黑以后剧组的全班人马,便借用寺院附近的一个广场,搭起台子演起了话剧。”
我查了一下资料,这批演员当年演出的剧目有《塞上风云》《群魔乱舞》和《故乡》等。但是作为“剧迷”的杨先生,偏偏忘记了台上的演出,她的脑海中深深镌刻着的,是那个让她一辈子都忘不掉的被称做“后台”的后台——“那是一块露天的空地,就在大雄宝殿前边的院子里。没有化妆间,没有休息室,只有几个凳子散放在院中的松树下,树干上挂着几面残缺不全的镜子。演员们就坐在那个摇摇晃晃的凳子上,对着镜子一丝不苟地化着妆,没有一点嘈杂,没有一丝声响。”
“他们可都是大明星啊!谁人不知,谁人不晓?”杨先生激动了起来,“《十字街头》《马路天使》《渔光曲》《大路》……这些片子迷倒了多少观众,震撼了多少国人!他们无一不是当年的影帝与影后,可是为了抗战,为了艺术,他们竟然忍受着这样的艰苦,却怡然自得,坦然相对!”
苍天为顶,大树为墙,月光作灯,星星作伴……这是世界上最为壮观的后台,编剧编不出来,导演导不出来,但它却是真真实实的存在!“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能够这般吃苦?”我的问话刚到嘴边,杨先生的回答已经脱口而出:“因为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当作明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戏剧工作者,一个抗敌战线上的文艺小兵!”
之后的某一天,是个星期日,杨先生没有课,演员们也没有演出和排练。于是白杨找到章曼萍,请心灵手巧的她为自己做个花布手提包;又于是西南联大的女学生杨苡陪着她俩一起去逛商店,挑来挑去,挑中了一块素雅的布料。白杨颇为客气地对着那个店员说了声:“对不起,打扰你了!”又于是三个人就像小学生一般,手牵着手走出了布店,没有人围观,没有人指指点点。
这么小的一件事情,杨先生竟然记忆犹新。这应该是当年那个“后台”的延续,更应该是当年那个“后台”的精髓所在。那天,白杨接过了她的新朋友杨苡的纪念册,亲笔题写了一句话:“打回老家去!”仅仅五个字,足以让20岁的女大学生明白了一切。
越剧名角竺水招的后台
将近一个小时的讲述,杨先生的嗓子有些沙哑了。她指了指门口的一个铁皮盒子,我起身将它拿了过来。打开一看,原来是五颜六色的巧克力——“吃吧,朋友送的!”于是我们二人像孩子般地大嚼了起来。“好吃吗?”“好吃。”“喜欢吗?”“喜欢。”杨先生一直将我当作孩子,我也一直视她为母亲。我知道应该告辞了,于是将笔记本收进了提包里。
“怎么?准备走了?”杨先生惊讶地望着我,“我还没讲完呢!”难道还有后续?还有更加精彩的后台?我急忙坐了下来,等待着又一个新的故事的开始!
杨先生端起茶几上的茶杯,一口一口地慢慢抿着。她在思索,思索着怎样开始这个新的讲述。“……那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故事了,应该是上世纪50年代初。我认识了越剧名角竺水招,作为小生‘竺派’的创始人,她带领着她的剧团来南京演出。”
“我看过她演的《柳毅传书》,还有,还有……”似乎是为了“遮丑”,我这个对于越剧一窍不通的“戏盲”,赶紧冒充起了“内行”。
“后来《柳毅传书》拍成了电影,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为了照顾我的面子,杨先生转移了话题,“可是有谁知道,她还曾大胆地进行过越剧改革,排演过现代戏《家》。”
她和竺水招的相识,竟然一见如故。竺水招要见她,是因为她知道,杨苡先生和作家巴金有着数十年的交往,要想排好与演好这部根据他的名著改编成的新戏,必须得向杨先生请教。于是,后台的故事便这样开始了:谈巴金,谈原著,谈改编,谈人物……杨先生甚至将家中的不少珍贵的资料都借给了她,并且还将这一切原原本本地向巴金先生作了汇报。
“从古装戏到现代戏的改革,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取得了成功,赢得了赞誉。”杨先生至今都记得那个剧场——就在新街口附近,就在胜利电影院的对面,名字叫做南京世界大戏院……“当年的那个轰动,你是无法想象的!”杨先生的兴奋洋溢在脸上。
我明白,我感动,在这个剧场的后台里,她终于不再是看客,不再是观众,她已经成为作者之一!
(《北京青年报》12.3 陈虹)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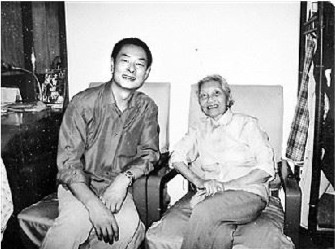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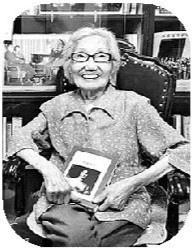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