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田成华从事精神科的治疗已经30年了,以下是他的自述。
一
90年代大家都不愿意做精神科医师,主要是怕受到歧视。别人一听你是精神科医师,很多人会“另眼相看”、敬而远之,甚至会跟我半开玩笑说,“你是同疯子打交道的呀?”
如果说这些年来,精神科门诊有什么变化的话,主要还是疾病谱的变化。30年前,来精神科门诊看病的病人,一大半都是症状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如今,门诊中的抑郁症、焦虑症患者,占了大部分。这反映出大众对精神疾病的认知程度,比以前要明显提升了,大家对普通的、程度没有那么严重的精神科疾病,也越来越重视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的观念转变;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竞争压力加大,患焦虑和抑郁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
但精神科所处的冷门位置,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因此,精神科医师的数量,并没有因为需求量的增大而有大幅增长。我国目前精神科医生仅有3.4万人,相当于每十万个人中只有两位精神科医生,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精神科医师少,主要是因为社会上对精神疾病有一定的歧视和偏见,但也跟待遇有关系。精神科不像外科系统,有各种手术,有器械,也不像内科系统,有复杂的药品、仪器检查,相应也就少了项目提成,因此除了北京、上海这些施行医师服务费的地方,精神科医师的主要收入几乎全靠不高的挂号费支撑。
精神科门诊的特点也有所不同,尤其是初诊,要将一个病人各方面的基本情况问得非常细致,其平均门诊时间是其它科室的几倍,专家号一天看二三十个号就已经是上限了,但所有科室的挂号费又都是差不多的。这样一来,精神科可以说是收入最低的科室之一了。
因此,除非是出于强烈兴趣,很少有毕业的医学生选择作为精神科医师执业。据我所知,北医八年制的医学生毕业班,每一年大概有一二百人,其中一般只有三五个人去选择做精神科医师,比例只有约5%左右。
二
医生少,多数精神障碍患者就得不到充分治疗。在理想的治疗模式中,患者最好跟着一个医生长期复诊。因为同样一种病,不同医生的治疗方案是有细微差别的,比如说同样的合并药,其中每一种药剂量需要多少,之后如何随着起效进行增减,每个医生有自己的风格,如果是总换医生的话,哪种方案都不好执行下去。
当然,很多医院的预约体系也并不利于这种长期复诊模式的实行。就拿北大六院来举例,如今的预约体系很难保证让病人每次都挂到同一个医生。每个医生每天的复诊号有限,其他的患者只好在网上能抢到谁的号算谁,无法保证治疗的连续性。
所以,我最近在个人层面做一个预约制的实验,我特需门诊的病人都由我自己预约,每天上下午各14个号,这样可以保证我的患者之后都固定由我来治疗。
不过,这种模式很难推行到整个医院层面,因为提前把所有号约好,经常会遇到到日子时患者爽约的情况,有时一上午14个号,能爽约三四个,我只能在诊室空等着,这也是对医疗资源的极大浪费。预约制度的困境,究其根本,还是医生资源根本不够用,所以医院只好让患者挂号的时候“撞大运”,这次抢上哪个大夫的,就找哪个大夫。
另外一个问题,是各地精神科的医疗质量做不到同质化。同样是主任医师的头衔,在北京的三甲专科医院和在一个县级市,医生的水平可能相差悬殊。这势必造成全国的病人都往北上广跑的局面。
三
精神科治疗,其实非常需要团队合作。因为有的病人可能有好几种病,会互相干扰,比如外科手术后的病人同时出现意识障碍、幻觉等,或者癌症病人出现抑郁。外科医生对这方面的经验不多,需要精神科医生会诊。
还有种情况,是抑郁症和其它症状的外部表现差不多,比如说甲状腺功能亢进有可能跟躁狂症的症状表现类似,需要医生依据足够的经验进行筛查,分辨出到底是哪种病。
团队合作无法施行的原因之一,是优质的医生资源实在太少了。团队合作对各科大夫水平的要求比较高,因为需要医生对其它一些病有了解,才能去寻求其它科室医生的合作。但从省一级的专科医院往下到地级市,越往下走,医生学历越不高。
在我国,精神科的培训和心理学的培训是两套完全分开、互不交融的系统。一位精神科医师,如果想再深入学习有关心理咨询方面的内容,需要自己额外花许多钱和精力去参加心理咨询的课程,单纯精神科的职业教育里是不包含这方面内容的。而一位临床心理学的学生,也不会在精神病专科医院中参加成体系的培训,至多参加见习,去走走看看。
大体而言,在如今的公立医院中,专门从事心理咨询的工作者被称作“心理治疗师”,而“治疗师”要比医师低一个等级。一般医院系统评医师职称,都有初中高三级,但是心理治疗师目前在公立医院中只有初级和中级,没有高级职称,这就使得水平较高的心理咨询师宁愿自己在外开工作室执业,也不愿意进入医院体系中来。
另外,目前绝大多数公立医院都要求心理治疗师拥有医学背景,纯心理学背景者,想要进入医院体系十分困难。不过好的消息是,有些医院,比如我所知道的武汉中德医院,已经开始有这种医生跟心理咨询师合作的常态化。虽然目前这种模式还不是主流,但是纯心理学背景的人进入到医院,与精神科医生的合作为病人提供服务,这肯定是一个未来发展的方向。
我个人认为,目前如果要解决这种困境,最核心是要提高包括心理科和精神科医生两方面人员的数量和质量,尤其是精神科医生。而提升数量的关键,是要提高专业人员的待遇,吸引更多的医学生来选择精神科。
(《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第34期 路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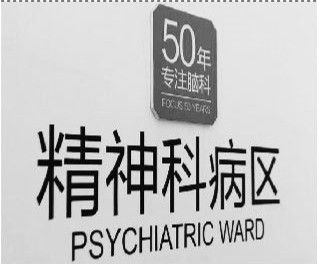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