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小漪
我的朋友,老上海人,他有一天打电话回单位,讲的上海话,对方直接说听不懂,让他不禁慨叹上海话在上海的慢慢式微。虽然说方言的挽救刻不容缓,但这件事倒让我从另外的角度理解到,在一个地方,以前不讲方言是很难融入的,现在看来,不讲方言影响越来越小。
而我的成长经历,始终和方言息息相关。我出生在江苏常熟一个叫梅李的小镇,常熟话是我的母语,父亲却坚持让我学苏州话,于是,我在家里和父亲说苏州话,和母亲说常熟话。
16岁,我第一次跨出梅李,考进了常熟的一所省重点高中。那时候我会故意像城里人一样发音,或者索性含混过去。可是做不到,方言就是烙在你身上的印记。好在时间一长,大家也习惯了。
18岁去了苏州读大学,同学的语言范围又从常熟市扩展到了江苏省。我一直以为我是懂苏州话的,并且自信地和本地的同学交流,然而,给我当头一击的是,我说的并不是时下正流行的苏州话。就好像是伦敦腔碰上了纽约街头俚语,让自己显得滑稽而古板。
方言在大学里既会成为被攻击的软肋,但更多时候是你最坚强的依傍。有一个同学,因为家乡都是北方移民,只说普通话,因此被称为“没有方言的人”。
大学毕业,我在杭州的一家报社工作。这里一半是杭州本地人,一半是外地人,通用的工作语言是普通话。
我喜欢听杭州人讲杭州官话,不难懂,又有点隐隐发噱。报社有个老同事,杭州人,开了个杭州话专栏,用市井俚语解读新闻,那可是18年前的事,读者特别多,成了当时的名牌栏目。虽然听不懂,可是看他的专栏特别来劲。
还有个年轻男同事,专门跑菜场,一本正经用“每日股评”的架势播报菜价,也是浓浓的杭州市井腔,他的专栏也是一炮而红。杭州人幽默又努力,从不害怕创新,到现在我仍然这么认为,杭州人在传承和创新之间是拿捏得最好的。
尽管喜欢杭州和杭州人,我却没有学会杭州话。后来我到了上海,成了上海人的媳妇。先生也不算是地道的上海人,他小学的时候跟着婆婆从常州来上海。上海话是友好的,易懂易说,兼收并蓄,你能轻易从中听出宁波话、盐城话的痕迹。我还惊讶地发现,它和常熟话的距离也很近。比如“哪里”,上海话称“阿里”,和常熟话是一样的,但苏州话不这么说。
我想要和家人没有隔阂地沟通,和他们一起笑,懂他们的梗。这种渴望让我没有障碍地讲起了“洋泾浜”上海话。那时候常常去家附近一家报摊买杂志,买杂志的人太少了,老板是个上海小姑娘,经常连买带送,顺便热心地纠正我的上海话。每次经过她的报摊,都能聊上一阵子。这样只用三个月,我的上海话就已经很地道了,这给我的工作、生活都带来很大便利。
我经常想,像我这样一个生在长三角的孩子,从小镇出发去探索人生秘境,眼前的世界一点点扩大,方言是引领我去触摸一个地方质感的线头。曾经努力想要凭着这根线头“和当地人一样”,也慢慢学会了当一个局外人去欣赏,但最终选择主动拥抱,只是因为太爱这个地方。不会讲一个地方的方言不影响生活、工作,但会讲,真的会更好。
(上观新闻 9.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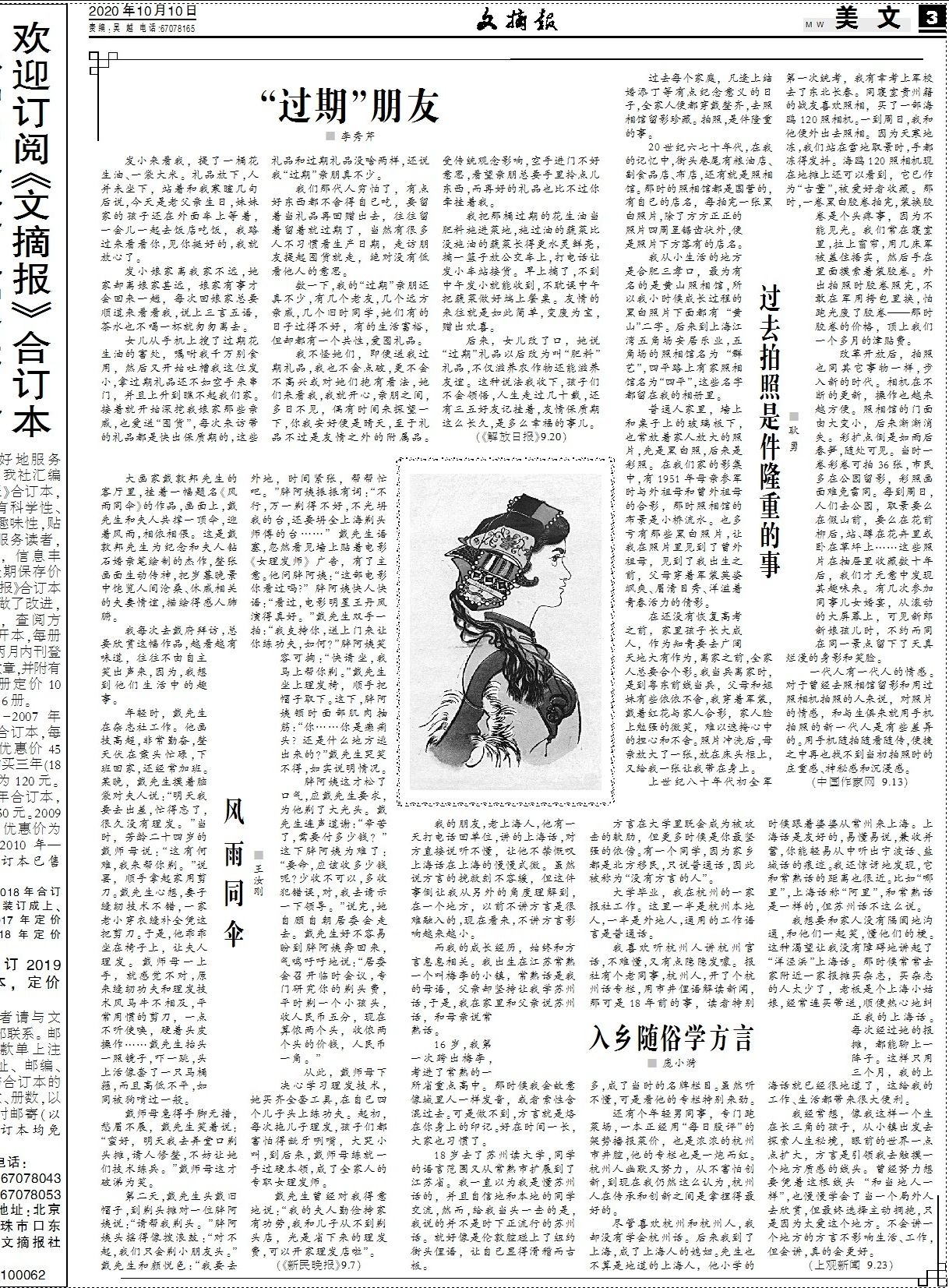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