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
他们来自天南地北,却有着共同的身份——“集报人”
报友间有一种共识,“集报不是为了挣钱。”跟报纸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马振予订过报、编过报、上过报、买过报、找报友换过报,就是从来没有卖过一张藏报。
一辈子结缘报纸
马振予家住在北京站附近的一条胡同里,几间小平房不算宽绰,老马还是挤出了一间专用的藏报室。10平方米的小屋被塞得满满当当:一面墙并排立着齐房顶高的报柜,装报纸的大号文件夹层层叠叠地摆在上面,每一本都被撑得鼓鼓囊囊;还有一些没来得及入册的报纸,对折着码成摞、堆成垛,像潮水一样从柜子里涌到房间各处。
老马上初中时,每个班每天只能拿到一份报纸,由班干部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我那时是学习委员,每天就管这报纸。”回首与报结缘的起点,82岁的老马眼睛亮起来。
“我看报上内容特别丰富,国内外的大事小情、副刊登的诗歌散文都挺好,就舍不得当废纸扔了。”早早懂得敬惜字纸的小马,开始把每期换下的旧报珍藏起来。到今天,这条集报之路已经走了近70年。
马振予觉得自己人生中的每一个转折点都和报纸有关。“文革”中,就因为爱看报,他被打成“三家村的黑走卒”,下放到陕西蔡家坡一家造纸厂接受劳动改造。在造纸厂,他参考之前从报纸上看来的材料搞技术革新,受到表彰。得益于此,1974年,马振予回到北京和妻儿团聚。
1979年,他又调入北京市计算机工业学校做老师,老马觉得这也是报纸的功劳。“我就是一个学化工的中专生,能到中专去教书,主要是因为我平时读书看报,知识积淀比较厚。”
从报纸中尝到了甜头,老马立刻把因读报受的苦都抛诸脑后。改革开放春风吹来,媒体发展掀起高潮,马振予兴致勃勃地把“撂荒”多年的集报事业捡了回来。他订报、买报,也利用业余时间四处搜寻各种珍贵的号外甚至是发行范围很小的行业报,乐在其中。
自行车是他集报路上的汗血宝马。“当老师不用坐班,听说哪家出了好报纸,下了课我就去找。买不着?蹬上车我就奔报社!”
老马的“黄金时代”
马振予把刚退休的那些年,看作是自己集报生涯的“黄金时代”。
“那时候60来岁,腿脚、精力各方面还都很好。”为了跑报社、买报纸,他能从东二环一路蹬自行车到西五环,车子前前后后换过四辆,大小伙子也没他的劲头足。
“黄金时代”开篇,老马的集报事业取得了两大突破:一是不再见什么买什么,而是有了明确的收藏重点——这在报友圈里叫“专题”。老马主攻的是聚焦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号外专题。
2000年以来,中国的喜事多、大事多,各地报刊印发的号外也跟着多了起来。老马像个运筹帷幄的老将,给全家人明确分工,一遇大事发生,就迅速按“作战计划”行动。“一般是俩闺女、女婿去西单、王府井,老伴儿蹲守北京站,我骑车直奔天安门。”可能的分发点一个也不能落下,能拿到的号外一份也不能错过——每次等这一大家子人拿着各自的“战利品”陆续回到大本营,基本上已经入夜了。但老马还会连夜给外地的报友打电话,互通有无,商量交换号外的事。
实在换不到的,就去“磨”报社。最让老马难忘的,是一份得来不易的“国足出线”号外。
2001年10月7日,中国男足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第一次冲进世界杯决赛,举国欢腾。据老马统计,当时全国大约有二十多家报社印发号外。老马很快就把专业媒体、当地媒体和北京媒体的号外攒齐了。
后来,他从报友那儿得知,吉林长春《新文化报》也出了一份“梦圆今夜”号外,版面漂亮,但印数很少,很快就派发完了,几个长春报友都没拿到。
这颗“遗珠”,让老马意难平。那些日子,他得空就给新文化报社打电话,发行部、编辑部、资料室、总编室……一个个部门打过去,得到的回答都是号外已全部发出,没有留存。他的执着感动了报社员工,大家都在帮他回忆号外的去向。
终于,有工作人员想起,曾给当地主管新闻出版的领导送过一份。得到线索,老马来了精神,他几次三番打给报社社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光电话费就“花多了去了”。
最终,老马收到了一封挂号信,信封里不仅装着那张从领导手里要来的号外,还有一份10月8日当天的报纸。老马小心翼翼地把这份号外收进藏报册,即便后来有人出价3000元,他也不肯卖,“我留着以后捐给博物馆呢!”
家里的藏品渐渐成了规模,结识的报友也越来越多,老马忙活起另一件大事来。
“报友们得有个组织啊!”他联系上罗同松和王永山——两位在报社工作的老报友,三个人一起跑前跑后,终于在2003年找到中国报业协会当挂靠单位,成立了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
有了自己的组织,全国报友应者如云。“60后”报友范光永就住在潘家园旧货市场边上,自然而然地爱上了老报纸收藏。他也是集报分会的第一批骨干会员,分会成立之初,老马拉着他义务为报友服务,他负责收取会费,老马负责邮寄会刊。两人一个天天跑传达室取汇款单,一个拉着老伴写了无数信封,两家的街坊看他们这么忙活,见了面就打听,这是做什么买卖呢?
朝着专家的方向“修炼”
除了集报,报友们也“追星”。不少集报爱好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偶像,93岁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方汉奇先生。在学界,方先生被誉为中国新闻史学泰斗;而在报友们眼里,方汉奇先生更是名副其实的“集报泰斗”。
“粉丝”马振予替方先生做过统计,60多年来,他利用集报资料著述教材及专著合计约150万字。层层叠叠的老报纸,搭成了方汉奇一生构筑中国新闻史学大厦的脚手架。
“集报集到一定数量,就应该把重点放在提高集报质量上,收集有价值的历史报、珍稀报,向纵深、专题、历史延伸三个方面发展。”方汉奇先生对集报人有很高的期望。报友们也照先生所说,在各自的收藏专题上朝着专家的方向“修炼”。
如今,按照出版年代的不同,老报纸在收藏市场上的身价在200元到几万元之间浮动。眼见有利可图,市面上出现了不少影印报、复制报甚至工艺更复杂的“假报”。
收藏红色老报刊专题的朱军华和范光永是多年好友,也都是集报分会报纸收藏鉴定委员会的成员。“我们一共有9个人,免费帮报友甄别老报纸的真假,防止报友上当受骗。”朱军华把藏品的真伪看得很重,他觉得每一份老报纸都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市面上“无中生有”的伪报、赝品,表面上就是谋财,往严重里说,更是对历史的扭曲和篡改。
报纸鉴别不像其他的文物鉴别那样普及和专业化,报纸的造假成本又低,伪报甚至会流入一些地方博物馆,或以插图的形式出现在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中,误导观众和读者。“现在国家很重视红色收藏,报纸是重要的藏品,在辨别真伪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集报图什么
“我们这些集报人,在别人看起来,可能挺没出息的。”马振予感慨,“我老伴儿有时候都说我‘等你死了,把你的报纸都卖了废纸’!”相濡以沫这么多年,老马知道老伴儿说的是气话,他也理解妻子的烦恼——集报有两大特点,一是占地儿,二是花钱。
老马藏报室里顶天立地的大书柜,在集报人家里算是标配。“人给报纸腾地方”在报友看来也是见怪不怪的事。
除了北京站旁的平房,老马在朝阳区还有一套两居室,那也是报纸的天下。老两口不去住,只派外孙女每天过去守着,因为“有点人气儿报纸不容易坏”。老马估算这些年花在报纸上的钱,只能给出个大概数——“二三十万元总是有的”。
“80后”集报人惠彬专收小众的北京街道、社区报刊,他觉得那是展示城市历史文化的一扇小窗。惠彬在一家酒店做维修工作,平时不算太忙,有空就一个社区一个社区地打听,问人家有没有出过报纸。“北京的边边角角,我比本地人知道得还清楚。”
藏品多了,他租房住的房子放不下,就成捆成捆地运回河南老家。父母难以理解儿子的痴迷,也跟他撂过狠话,“再拿破报纸回来,都给你烧了!”
集报人范光永、朱军华收藏的都是身价不菲的老报纸,除了高价买报,还要大批量地购买专门的塑料保护膜,花费更多。
报友间有一种共识,“集报不是为了挣钱。”老马说,跟报纸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他订过报、编过报、上过报、买过报、找报友换过报,就是从来没有卖过一张藏报,“咱爱报纸,不是图钱。”
那图什么?面对这个问题,报友们一时也没法给出明确的答案,只好跟记者讲起了“题外话”。朱军华说起了自己创造的一个“第一”——因为抗战最后一役在他的家乡高邮打响,2018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他拿出自己所有的抗战专题报纸,建起了“苏中抗战老报馆”。那是全国第一家抗战报纸博物馆。
范光永提起多年前深埋在脑海中的一个梦想——“等我退休了,把藏报都捐出来,在中国老报纸起源的地方——北京宣南地区,建一个北京宣南老报纸博物馆。”“就是留存一份直观的史料、留下历史的见证吧。”朱军华说,“我们图的不是经济价值,是社会价值”。
(《新华每日电讯》1.10 雷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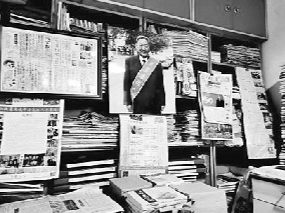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