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一家免费餐厅,能维持多久?起初,梁洪瀚的答案是三个月。而如今,在广州市番禺区西城路,他运营的这家名为“雨花斋”的免费餐厅已超过三年。
过去六年,像这样提供免费素食午餐的“雨花斋”餐厅,全国已开有逾七百家,而每家店之间并没有组织关系,没有经济控制,完全凭着各地爱心人士自发建立、勉力维持。
老城区的免费餐厅
三年前,本职工作为英语培训教师的梁洪瀚在网络上看到雨花斋的消息,为其免费午餐的模式感到惊讶和好奇。梁与五个热心公益的朋友一同驱车至中山市,探访当地的雨花斋餐厅。回来后,他们各自捐出餐具、粮油、桌椅、空调,筹集了一笔资金,共同发起了广州首家雨花斋公益素食餐厅——番禺雨花斋。
2014年11月,番禺雨花斋正式面向大众开放。起初来用餐的多是邻里、周边商铺的人。半年后,人渐渐多起来,如今每天来番禺雨花斋用餐的人数稳定在三百到四百人。
附近小区的保安、环卫工人、流浪汉、残障人士都是这里的常客。更多的则是老人。据梁洪瀚观察,八成以上的食客都是老人。这与当初餐厅选址的考虑相契合,“以老人家为主,靠近老城区,对老人家方便”。番禺雨花斋所处的市桥街道,附近有十多个房龄超过二十年的老社区。
除了住在附近的老人,也有一些老人每天乘公交车过来。番禺雨花斋的义工郑敏曾遇见常来用餐的老人提着菜回家,“我才知道,那些老人那么远来吃一顿午饭”。郑敏发现,真正长期来用餐的大多是独居的老人,“现在的老人家都很孤独,他们来这里可以聚在一起聊一聊”。
和来用餐的人一样,番禺雨花斋的工作人员也是身份各异,有放暑假的大学生、旅游经过的人,也有在附近工作抽中午时间来帮忙的年轻白领,他们全都是义工。大部分义工是老人,他们多是从餐厅的常客转变为餐厅的义工。义工是流动的,每天人数不等,像郑敏这样的长期义工,基本上是已经退休的人。
义工之间也有分工。年纪稍长的几个老人负责择菜,年轻一点的洗菜、炒菜,站在门口迎宾的通常是几个残障人士。
心智残障的小雷(化名),起初是被一名义工带来用餐的。后来开始帮着烧水、拖地、摆凳子,慢慢地也成为雨花斋的一名义工。
郑敏告诉记者,是他们主动去引导这些残障人士做义工的:“这些人在社会上是缺少人关心和认同的,我们希望他们能找到自己被否定掉的价值、被关爱的感受。”
复制雨花斋模式
已逝世的浙江建德广安禅寺前住持文全长老是“雨花斋”的发起人,曾无偿收养许多老人。2011年,文全长老责令弟子殷建办一家面向老人的免费素食餐厅。
文全长老和殷建拿出积蓄,与几位爱心人士共同发起了全国首家雨花斋公益素食餐厅。2011年9月12日,位于建德新安江文化广场的雨花斋正式开业。一些被文全长老收养的老人在其感召下,成为这家店最早的一批义工。
2011年12月,全国第二家雨花斋在浙江省德清市创立。紧接着江苏常州和盐城的公益人士也办起了雨花斋。此后,从浙江周边省份到全国各地,陆续有公益人士创立了当地的雨花斋。全国各地的雨花斋并无组织关系,在资金管理上各店都是独立的。
对于雨花斋的快速发展,有专家认为,其动力源于真实的需求:一方面,老人对餐饭有基本的需要;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走进慈善事业,而雨花斋的模式简约,没有大小、形式等束缚,所以可复制性非常强。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陶传进指出,“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善的成分,遇到合适的条件就会萌发出来。一种模式具有感染力,就可以抓住人心,快速传播。”
“道义之家”的磁场
在雨花斋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雨花斋的规范准则和核心理念也在逐渐成形和深入。早在创办全国首家雨花斋之初,文全长老和殷建便对餐厅的运作流程设定了基本的理念:
一是“惜物”,提倡光盘,以节约粮食和减少洗洁精的使用。雨花斋餐厅内,每张桌子上置有一壶“惜福水”(白开水),提倡用餐后,用开水冲涮碗内残留的汤汁后喝掉。
二是“惜缘”,雨花斋的义工称呼每位来用餐的人为“家人”,并在初见时行深度鞠躬礼。雨花斋的所有义工不分等级,都以“家人”或“学长”相称。
此外,对于义工做事的态度,文全长老和殷建还制定了“五了”规范——“吃了就好、做了就好、够了就好、舍了就好、了了就好”,提倡包容和节俭。
梁洪瀚则认为雨花斋的精神真正将中国传统的“家文化”落地了,“食客、义工构成了一个道义之家”。每个月,番禺雨花斋都会收到一些企业家和慈善组织捐赠的粮食和食用油,为餐厅节省了很大一笔开支;一些来用餐的老人有时会捐一些家里多余的大米。
(《南方周末》11.23 甘甜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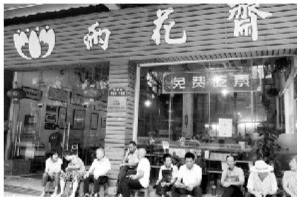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