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比较富于幽默感的。这种幽默在不同场合与形势下,有不同表现。
就比如走路吧。毛泽东并非总是庄严或稳重,他非常喜欢晃肩扭腰,手舞足蹈,全身活动着走路,很有些像公园里某些活动着的老人。你想,他办公常常一坐十几个小时,走路时还不想活动一下全身吗?每当他从卧室出来去颐年堂参加会议时,短短一段路也要晃肩扭腰,手舞足蹈地走路,一旦到了广众之下,才改成庄严或稳健的步子。
当他手舞足蹈时,还要略显夸张地呼吸,并且朝跟随的卫士递个眼色,那是无声的幽默:“发愣干什么?我也是人哪!”
“客人走了吗”
胡宗南进攻延安,几十架飞机轮番轰炸。王家坪被烟尘笼罩,燃烧弹在毛泽东的门前燃烧,弹片飞了一地。卫士们冲进毛泽东居住的窑洞,毛泽东依然在聚精会神地查看地图。
“客人走了吗?”毛泽东看着地图问。
“谁,谁来了?”卫士愣怔着。
“飞机呀,”毛泽东手中的笔朝天一指,“喧宾夺主,讨人嫌。”
于是,卫士们都笑了,紧张感全部消失。
这时,有人拿来一块落在窑前的弹片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接在手里掂量掂量,一本正经地说:“嗯,能打两把菜刀呢。”
这些话若非当时当地身临其境,是难以全部体会其中的幽默的,再加上毛泽东讲话时的表情和他那抑扬顿挫的湖南口音,效果就更强烈了。
转战陕北时,从小河村出来,走到一个光秃秃的山上,向导迷了路,大雨倾盆,五六万敌人就在山下的沟里运动,时时响起零落的枪声。同志们又饿又冷又紧张,紧紧靠拢到毛泽东周围。毛泽东忽然笑了一声:“嗯,真是铜墙铁壁,风雨不透了。”
于是,大家的心便安定下来。
“金缸”和腌菜缸
沙家店战役获胜后,毛泽东首先表现出的不是大笑和欢呼,而是替胡宗南遗憾,带着同情悲怜的语气叹息:“唉,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哪样想,他就哪样办……”
于是,毛泽东把胜利后的开心大笑送给了同志们。大家尽情笑过之后,毛泽东扳着手指数:“青化泛、羊马河、蟠龙、沙家店……整个凑起来我们吃掉它六七个旅。”
胡宗南说他有四大金刚,毛泽东略一停,摇摇头:“我看他的‘金缸’不如老百姓的腌菜缸。”
同志们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他们四口缸被我们搬来三口:何奇、刘子奇、李昆岗。只剩下一口缸。叫什么……”
会场活跃起来,后面有人喊:“叫李日基!”
毛泽东吮吮下唇:“对了,叫李二吉。这次没抓住他,算他一吉;下次也许还抓不住,再算一吉;第三次可就跑不了啦!”
会场里又哄声大笑起来。毛泽东就像一名幽默大师,大家越笑,他越能忍住不笑;他越忍住不笑,就越将更多欢笑送给了大家。
“有件事我想不通”
毛泽东日常生活中,与我们卫士和警卫人员相处随便,更是不乏幽默。
记得第一次游长江时,我照顾毛泽东换好游泳裤后,自己也脱了衣裤,换游泳裤。我发现毛泽东在打量我。
“银桥啊,你已经比较伟大了,发展下去就比我伟大了。”毛泽东一本正经说。
我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这样说?甚至有点不安。毛泽东忽然拍拍我的肚皮:“你肚子大了啊,快跟我媲美了!”
我笑了,往回收肚子。毛泽东又拍我肩榜:“你直起腰来,背不要驼着。也快随我了呢……”
毛泽东有些驼背,我也有点驼背,忙挺胸收腹说:“岁数不知不觉就大了,可我是做不出主席的贡献了。”
“才而立之年就这么泄气?我老了,你还是大有前途。”毛泽东说着,走了出去。
毛泽东在连续工作时,常需我们一再提醒才肯到室外散步,每次散步,他常交待:“看看表,十分钟。”为了让他多活动活动,我总是瞒时间。可毛泽东身上总像装了一座生物钟。每到十分钟左右必要问:“怎么样,到钟点了吗?”我便说:“还差2分钟。”“你那个表总是犯路线错误,要改也难。”毛泽东嘀咕着,不再问时间,自己数着走百步,便回屋继续办公。
有一次,我指挥几名卫士利用毛泽东散步的机会,准备将他书房里的大沙发搬到另一房间去。试几次,搬不出门,只好又放回原处。
毛泽东回屋来,见沙发仍在原处,便问:“怎么没搬出去?”
“门太小,出不去。”卫士封耀松说,“干脆留在屋里吧?”
毛泽东看看我们,又看看沙发,作严肃思考状:“唉,有件事我始终想不通呢……”
毛泽东在与专家或领导干部谈论国策之后,常有踱步到警卫人员那里,就同一问题听听战士们意见的习惯。我们也乐于在他面前发表见解,便问:“什么事啊?主席。”
毛泽东皱眉作不解之色:“你们说说,是先盖起这间房子后搬来沙发呢?还是先摆好沙发再盖这所房子?”
我们都红了脸,这还用说吗?我们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将沙发搬出门去。
(摘自《我所知道的毛泽东》 权延赤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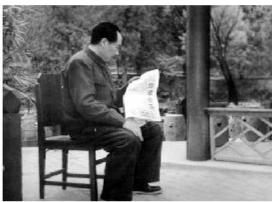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