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10月1日,这个国家的欢乐像泛滥的水灾湮没着大城小镇时,我一连接了几个电话,催我赶快回老家,说我69岁的四叔不在了。到这时,我惊冷地意识到,在我父亲这一辈,他们亲弟兄三个,终是都丢下这世界,丢下我们这些晚辈们,到另外一个界地求着清静去了。在某一瞬间里,我明白了父辈们在他们的一生里,所有的辛劳和努力,不幸和温暖,都是为了活着中的柴米与油盐、生老与病死。
■阎连科
这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各家都还有自留地,与此同时,也还允许在荒坡河滩上开出一片一片的小块荒地,种瓜点豆,植树栽葱。我家的自留地在几里外一面山上的后坡,地面向阳,然土质不好,全是褐黄的礓土,每一锨、每一镐插进土里去,都要遇到料礓石。为了改造这土地,父亲连续几年冬闲都领着家人,顶着寒风飞雪到自留地里刨刨翻翻,把礓石从土里翻捡出来,大块的和细小瘦长的,由我和二姐抱到田头,回家时担回家里,堆到房下,到有一日翻盖房子时,垒地基或表砌山墙所使用。
初上山时,父亲的腰骨,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笔直的腰杆儿,到了午时,那腰杆儿便像一棵笔直的树上挂了一袋沉重的物件,树干还是立着,却明显有了弯样。然而到了日过平南,那棵树也就彻底弯下了,仿佛再也不会直了一般。
我说:“爹,日头落了。”
每次我这样说完,父亲似乎不相信日头会真的落山,他要首先看我一会儿,再把目光盯着西边看上许久,待认定日头确是落了,黄昏确是来了,才最后把镢头狠命地往地上刨一下,总结样地,翻起一大块硬土之后,才会最终把镢头丢下,将双手卡在腰上向后用力仰几仰,让弯久的累腰响出特别舒耳的几下嘎吧嘎吧的声音,再半旋身子,找一块高凸出地面的虚土或坷垃,仰躺上去,面向天空,让那虚土或坷垃正顶着他的腰骨,很随意、很舒展地把土地当做床铺,一边均匀地呼吸,一边用手抓着那湿漉漉的碎土,将它们在手里捏成团儿,再揉成碎末,这样反复几下,再起身看看他翻过的土地,迈着匀称的脚步丈量一番,又用一根小棍,在地上笔算几下,父亲那满是红土的脸上,就有了许多浅色粲然的笑容。
也许是父亲的劳作感动了天地,那一年风调雨顺,那块田地的红薯长势极好。凡从那田头走过的庄稼人,无不站立下来,扭头朝田里凝望一阵、感叹一阵。这时候如果父亲在那田里,他就会一边翻着茂如草原的红薯秧棵儿,一边脸上漫溢着轻快的欢笑。
阳历10月8日、9日,是霜降前的寒露。那天,大队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说各家各户的自留地,必须在文件传达之后的三日之内,全部收归公有。
那个寒露的中午,父亲从会场上回来没有吃饭,独自坐在上房的门槛儿上,脸色灰白阴沉,无言无语,惆怅茫然地望着天空。
母亲端来一碗汤饭说:“咋办?交吗?”
父亲没有说话,看看母亲端给他的饭碗,没有接,独自出门去了。我们都知道父亲去了哪里,很想去那里把父亲找回来,可母亲说让他去那里坐坐吧。那一天直至黄昏消失,夜黑铺开,父亲才有气无力地从外边回来,回来时他手里提着一棵红薯秧子,秧根上吊着几个鲜红硕大的红薯。把那棵红薯放在屋里,父亲对母亲说:“咱们那块地土肥朝阳,风水也好,其实是块上好的坟地,人死后能埋在那儿就好啦。”
孤独的大伯
大伯的人生与愿望,就是把他的子女们送到这个世界上,而后倾其所力,倾其所为,负责着让他们个个都成家与立业,男婚与女嫁。
为了这一切,他在六十多岁时,还东奔西波,到外地买苹果、买香蕉、买柑橘,把这些水果从外地运到当地,再一斤一两、一筐一篮地卖到别人手里去。他日日地劳碌和奔忙,赔了又赚了、赚了又赔了,直到一场灾难的到来,才终止了他这周而复始的日子,终止了岁月往复对生命空转的消耗。
有一天,是深秋的时候里,我在豫东开封部队军机关的家属院正走着,忽然有人告诉我,说我家里来人了,在我家门口等着我。慌忙地赶回家里去,看见大伯疲惫地坐在我家门口一棵冬青树下的水泥台子上。我吃惊地叫了一声:“大伯。”
大伯没应声,只是扭头对我苦笑了一下子。
我慌忙开门把大伯让进屋子里,依着我老家的习惯,以最快的动作,打开煤气灶,去给大伯煮了几个荷包蛋。将荷包蛋端在我大伯面前时,大伯望着我,以极平静的语气对我说:
“连科,你妹妹连云不在了,在灵宝县出了车祸啦。”
我愕然。
我脑里“轰”一下,呆在了我家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客厅里,望着我大伯,不知为何,我突然想在大伯面前跪下来,想要扑在大伯怀里呜呜呜地哭一场。那时候,我木在那儿没有动,许久没说一句话,泪像雨样挂在我脸上,似乎屋子里到处都充满了嗡嗡嗡的响。
大伯看我不说话,看我泪流满面了,就有意地在他脸上挂着把事情看轻看淡、风吹云散的笑。然而,他让我看到的笑,在他脸上却依然是掩饰不住的苦笑和苍黄。大伯笑着说:“你妹妹连云不在了,我在家里闷得很,想到你这儿走一走。”然后他端起那碗荷包蛋,没有吃,只是端在手里说,“这都是她的命,是她的命让她这么小就离开我们的。”过了一会,大伯又补充着刚才的话:“走了好,其实人活着也是活受罪。吃不完的苦,受不完的罪。”说到这儿时,忍不住悲痛的大伯也哭了,泪就掉在我给他煮的那碗金黄白亮的荷包蛋碗里,像不间断的房檐滴水砸在凡俗世界的水面上。
到晚上,我和大伯在家把话说到深夜才睡觉。主要是大伯说,说他们弟兄间的事,说我们姊妹兄弟间的事,说他的父辈,我的爷爷弟兄间的事。大伯说得很流畅,像他把大半生郁积在心里的话全都给我说了。大伯说他已经有两年心里没有那么轻松顺意了。说他心里轻松了,就想回家了。
“一头沉”的四叔
四叔爱喝酒。日常间,来陪四叔或四叔去陪人家喝酒的,都是他们车间一同进厂的几个老工人。那几个老工人和四叔有着共同身份——都是自己来自乡村,而妻儿老小都还在乡村守着田土耕种的那种俗称为“一头沉”的人。
这种“一头沉”,使他们回到农村被人视为“工作在外”的人,到了那所谓的“外头”,城市或城郊,又被城里人或同厂的工人们称为“农村人”。“一头沉”的人,在工厂和城里是被人鄙视的,因为你是要进城摆脱身份又没有彻底摆脱的人,要到城里去争夺一种幸福又没有彻底拿到幸福的人。因为这身份的不彻底,你就必然会为了多挣那么一毛、几毛钱,把工厂最脏最累的活儿,都敞开胸怀揽在自己的心胸里、搁在肩膀上,到头来又被人耻笑你为了那丁点儿蝇头小利,连做人的脸面和尊严都不要。真正的城里人,会在墙上吊一份挂历,是为了看哪一天是星期天和节假日,以期早些安排周末的活动和休息。可“一头沉”在桌上摆的是台历,那台历最大用途,是提醒你今天“芒种”了、明天“春分”了、后天“夏至”了。到了农忙你就必须要千方百计回到农村去。还有一点不能不说的,就是“一头沉”们在厂里下班后,可以物以类聚地邀在一块喝些酒,品尝一下在乡村无法品尝的生活的幸福和快乐。我四叔就是这样爱上了酒。
有一次,他们车间的一个工人的弟弟要结婚。四叔为了随礼,一个月前就到市里去给人家买了一床羊绒毯。可是到了人家婚礼的那个星期天,四叔迟迟不出门。我以为是钱不够,就把我一个月的工资拿去放在了四叔面前的桌子上。
四叔朝我苦笑一下子,抬头看了一眼门口铁丝上挂的一件“的确良”白衬衫,轻声说:“昨夜儿洗了的,现在还没干。”
就在这一刻,我触摸到了四叔的幸福和窘迫,仿佛看到了他人生中一扇光鲜的大门后边的杂乱样。迟疑一会儿,我拿来了三年前四叔送给我的“的确良”的绿格儿尖领花衬衫。那一天,沉郁中四叔就是穿着三年前脱下来给了我、三年后我又洗好叠好给了他的那件衬衣去参加人家婚礼的,去喝了那场他准备了许久的喜宴酒。那一天,四叔喝醉了。
醉酒的四叔半夜回来后,忽然哇哇哇地哭,哭着反复地说着一句话:“人活着咋这样辛苦哪!人活着咋这样辛苦哪!”
到了第二天,我还睡着时,四叔却醒了。他来叫我起床和他一块到新乡市的百货大楼去,说要去给他、给我和我书成哥哥各人买一套新衣服,说豁上不过日子啦,只要看上,再贵也要买。说豁上了,一定要给每个人买套新衣时,四叔脸上的笑,灿烂明快,充满信心,仿佛有一种真真切切的坚定幸福挂在他脸上。
(《我与父辈》江苏人民出版社)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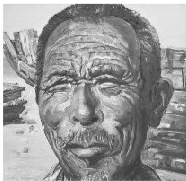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