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评论家解玺璋至今清晰记得,“文革”期间他在工厂阅读俄罗斯文学的狂热劲儿。有一次从朋友那儿借到一本俄罗斯小说,人家只允许借阅一天,当晚他挑灯夜战一口气读完。
在那个精神食粮极度匮乏的年代,解玺璋感叹大家是逮到什么书就看。他还记得,普希金的诗在年轻人当中很流行,很多朋友会在日记本里抄诗,尤其是爱情诗。他有机会去王府井内部书店买一些“灰皮书”,大多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文学作品,供当时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所用。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俄罗斯文学在年轻学生中也很盛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就是在那时读了大量俄罗斯文学作品,并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
“年轻时很苦闷,觉得人生很灰暗很没有意义。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穷人》《白夜》,感到非常震撼。小说里小人物的生活也很灰暗,过得那么惨,却能够把人生意义建立在对他人的爱的基础上。”张柠动情地回忆,这对自己的心理影响很大。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飞觉得那是一个疯狂阅读的时代,“整个社会都有一种饥渴感,去新华书店买书经常要排队。几年之间出了数千部外国文学,其中一半是俄罗斯文学作品。”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辉煌的时期,俄罗斯文学已悄悄走下坡路,西方现代派文学更加受到年轻人的喜爱,他们觉得俄罗斯的古典作品太长、太沉闷。在张柠看来,现在的年轻人跟世界的关系不像自己当年那样紧张,即使有点不适感,听音乐、看电影之类就能治愈。他们喜欢优雅、闲适的东西,可选择的文化产品太多,不喜欢沉重的俄罗斯文学。
在国内外国文学出版社中,上海译文出版社曾是一个重镇。最兴盛的时期,上海译文有七八个俄语文学编辑,如今相关编辑已是空白。这种情况在国内出版行业并不鲜见,类似人民文学出版社还能保留一个俄语文学编辑,已经非常罕见。
俄罗斯文学出版行情式微,但类似张柠这样的读者,对俄罗斯文学依旧钟情。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重读或补读一些俄罗斯文学作品。“回过头来看,俄罗斯古典文学建立了世界文学的一个标杆,具有中国文学缺少的精神高度、灵魂深度。”他赞叹道,跟那些现代派文学作品相比,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更有永恒的魅力。
(《北京日报》11.19 周南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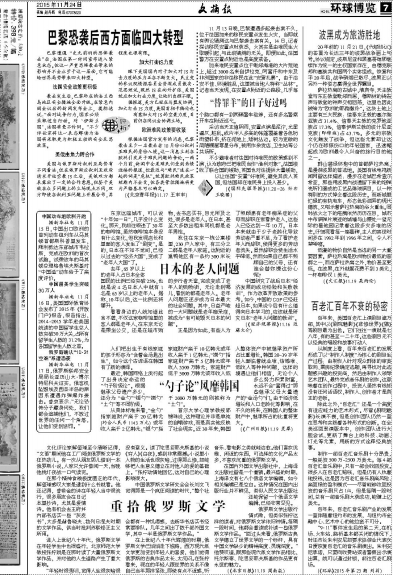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