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胡适初为人父,却写了一首很奇怪的诗,题为《我的儿子》,里面有几句怪异的话:
树本无心结子,
我也无恩于你。
但是你既来了,
我不能不教你养你。
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
并不是我待你的恩谊。
将来你长大时,
这是我所期望于你:
我希望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不要做我的孝顺儿子。
为孩子付出很多,
就有安排他们命运的权利?
孔融也说过:“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物寄瓶中,出则离矣。”最终他因言获罪而被杀,其“跌荡放言”与胡适“离经叛道”的诗同样引得时人不满,因为有悖父母恩情。
当下许多父母以孩子恩主自居,倒不一定要物质回报,而是粗暴认为,自己付出甚多,就该有安排孩子命运的权利。胡适正是这种意识的受害者。
胡适对母亲可谓言听计从,“我的母亲既不能读又不能写,可是她却是我所知的一个最善良的女子”,在婚姻大事上,虽不满意母亲订下的未婚妻江冬秀,却依然乐观,“母亲对我的深恩无从报答。我长时间离开她,已经深感愧疚,再不能硬着心肠来违背她”。
1890年,17岁的冯顺弟嫁给49岁的胡传,胡适曾写到父母姻缘初起,冯顺弟作为贫家长女,以做填房的彩礼,给家园在战火中焚毁的父母盖一座新房。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胡传去世,老二(二儿子)当家,小到吃一块豆腐干,大到让胡适外出求学,冯顺弟都须看其脸色,更不用说夹在几个媳妇中受不完的夹板气。
这样苦境,胡适必然成为她唯一的指望,她苦心孤诣地培养他,极其难堪地帮他争取读书费用,后来胡适出国读书,她得了重病,还特地不要让人告诉胡适。胡适自觉那么地对不住母亲,若再拂逆她的想法,就是没良心。但胡适却告诉儿子“我也无恩于你”,这何尝又不是说给母亲听的呢。
对于胡适被“恩情”绑架命运的抵抗,多年自居服从之后,他潜意识里的一种反弹:孩子你可以有反刍之心,但我绝无想要得到回报之意。
@民国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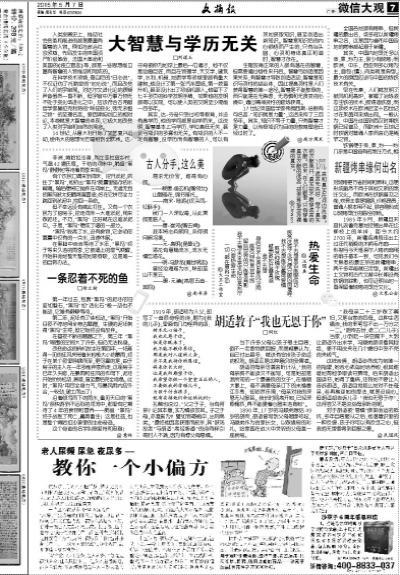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