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二字弥觉珍贵,我只希望能以独立学人的身份立于世。
不知从何时起,我在公共场合被介绍身份时,主持人常提到“曾为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做过翻译”,有时还要加上“参加过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工作”。起初我还不以为意,后来越来越感到不是滋味,于是有机会就要说明:我年轻时在外事单位工作,由于专业学的是外文,主要工作之一是翻译,重头是国际会议的同声传译,间或也为一些官员包括国家领导人见外宾做翻译,但只占工作的一小部分,临时应命,绝非专任。那时候国家领导人并没有专门的翻译,只是有关部门掌握一个相对固定的各种语种的翻译名单,以便随时需要,临时召唤。在1959年至“文革”之前一段时期,看来我被列入了这个名单,所以不时应召接受任务,平时就在本单位工作。如此而已。另外,既然做对外交流工作,接触的人中包括外国名人、要人,这也不足为奇。
最近做客“人民网”,关于我的介绍中又突出这一点。“天涯网”的介绍干脆把这作为我唯一的身份。我更感到有必要郑重说明,以免被误以为曾经是“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我所处的年月,无论为谁翻译,只是一项普通的工作,最多说明在业务水平上得到一定的认可,何况此类工作只不过“用其一技之长”,不会因此显赫起来。
另外还有一层,我年轻时被分配做了十几年翻译,并非初衷。那时,工作不是自选的。后来越来越感到厌倦,对因工作关系而得以见“大场面”,接近“大人物”,兴趣索然。旁人看来也许以为值得羡慕,我却有庄子寓言中的“腐鼠”之感。所以改革开放之初刚可以有一点选择权,我就赶忙申请调到研究单位,以读、写为业。不论如何,总算有一点独立性。
我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只有短短的五六年中有过为领导人翻译的经历,难道其他都不足道?特别是后半生虽然碌碌无大成就,但也多少有所思考,形诸文字,还不至于要凭借曾为大人物服务来抬高自己。所以,对此类介绍产生逆反心理。
无需讳言我曾有此工作经历。幸好,本人在“文革”开始后入了另册,与红墙之内绝缘,于是在我的翻译经历中没有“四人帮”成员以及当时任何一位新贵,这是值得庆幸的。在那个特殊年代,为“首长翻译”确实只限于极少数特殊人物。但是假设(只是假设)我当时竟然也被召去执行为某人翻译的任务,当然是无法拒绝的,那么今天“曾为……翻译”该如何介绍呢?
所以,我今天对“独立”二字弥觉珍贵,只希望能以独立学人的身份立于世,也希望世人以此知我。
(《士人风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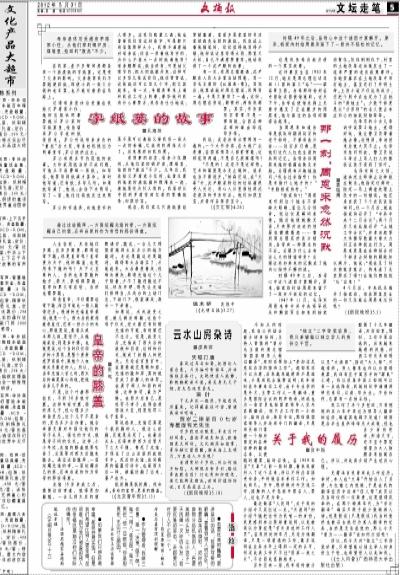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