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不让跟他玩,怕传染艾滋病。”
这个家庭留下的记忆躺在一只带“喜”字的红色皮箱里。如果只是翻看这些照片,很难在其中找到异样的蛛丝马迹。
那时,小峰的父亲在外国渔船上做海员,举止做派像个十足的城里人。照片中,他戴着当时流行的茶色蛤蟆镜,穿着黄色圆领T恤衫站在美国街头,潇洒地摆了个叉着腰的姿势。
第一次出国打工回来,他带回了10万元人民币,娶了外村的姑娘,换了新房子,还买了彩色电视机。在1992年的农村,这让邻居羡慕不已。
结婚没多久,他又出海了。海上生活孤寂,渔船几个月才能靠一次岸。几年后他回国时,在机场入境抽血检测时被查出感染艾滋病毒。那是1996年,他成为丹东市第一例艾滋病患者。
当宽甸县防疫站接到这份化验单时,已经是3个月后了,这对夫妻此前毫不知情。工作人员急忙去为他的妻子采血化验,血样送到市里检测后,结果也是HIV阳性。
这对夫妻却没把它当成什么大事,还打算偷偷要一个孩子。
1997年11月,小峰出生了。他从母亲那里得到了一对单眼皮,还有艾滋病毒。
不知从什么地方得知这一消息的某媒体,报道了这个故事,并在文章中提及真实的个人信息。恍然大悟的村民们这才如临大敌。
村庄往日的秩序不复存在。首先消失的是朋友,他们很少再去串门。接下来是工作。擅长泥瓦匠活的父亲在附近打零工,风言风语很快就传到工地上,老板第二天就把他的工钱结算了。
还不懂事的小峰也成了村民眼中的“危险人物”。几年前电视台来采访,呈现了这样的画面,系着红领巾的同村女孩一板一眼地说:“我妈不让跟他玩,怕传染艾滋病。”
小峰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在亲戚们的记忆里,幼时的他爱说又爱笑,跟现在完全两个模样。只是,他从来也没有朋友。
2004年,小峰7岁了,他时常到村小的铁栅栏门前张望——村里几十个小朋友都在那儿,他想和他们一起打弹珠、摔烟卡。父母也希望他能像正常孩子一样,去学校读书。
“你彪(傻)了?别人不干你干呀!”
小峰入学第一天,村里许多人就从教室里领走了自己的孩子。学生越来越少。到了集体罢课的第三天,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校长让小峰母亲把孩子先领回家,然后向防疫站和乡政府反映了这件事。
最后,家长们妥协的结果是:小峰到村小上学后,要安排老师单独为他授课,家长接送,并且与正常上学放学时间错开。可一个月过去了,学校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授课人选,找的两个老师都声称“身体不好”。
最后,分管教育的副乡长刘晏清在协调会上提出,只能在学校对面的村委会里开设“爱心小学”,聘请一位退休老师单独授课。
王立军是刘晏清找到的第五个人。
王立军黑且精瘦,额头上横着5条深深的抬头纹,手上还有被玉米杆割破的紫色伤痕,看上去像个十足的庄稼人。他当过十几年小学老师,后来调到乡文化站工作。乡镇事业单位改革时,他符合工龄30年的条件,只能提前退休。
王立军在电话里爽快地答应了刘晏清。他不是本村人,但也听说过这家人的事。他看过宣传册,知道艾滋病是可防的。
“不是说咱思想境界高,一开始我是冲着钱去的。”他一摆手,半开玩笑地说。其实他并不知道政府能给他开多少钱。
回到家,王立军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我明天又要上班了,还去学校当老师,就教一个学生。”他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说,“一个艾滋病小孩。”
“你彪(东北方言,傻的意思)了?别人不干你干呀!”妻子急了。
那天晚上,王立军和女婿说起这件事时,妻子仍在旁边不依不饶,“你看,他是不是有病?”女婿倒挺开通,“没事,这个病就那几个传播途径,别听他们瞎说。”妻子没再说什么,王立军就当她默许了。
2004年11月20日,“爱心小学”在村委会里开学了。学校里只有两个人,操场是村委会的院子,唯一的教室不足10平方米,篮筐是绑在电线杆上的一团铁圈,只有村小那个标准篮架一半高。
见到小峰第一面时,王立军有些意外,这个被母亲领来的小男孩,瘦小得不像已经过完7岁生日的样子。在母亲的提醒下,小峰叫了声“老师”,又鞠了一躬。王立军伸出胳膊,一把将他搂在怀里。
“别听他们的,他们都瞎说,咱不是那种病。”
村里有了两所小学,相隔仅百米,坐在村委会的这间教室里,能听见对面学校清脆的上课铃声。
小峰的学校没有铃声。这里也没有考试和作业,而且只上半天学。每天早上,母亲用自行车载着他,尽管步行的路程还不到10分钟。王立军故意让小峰的到校时间和对面学校错开,晚到、早退。这样,即使沿着同一条路上学,他和村小的学生也很少碰见。
小峰知道自己和其他孩子“不一样”,他几乎没再去过对面的学校。
一天下课,小峰突然跟王立军说:“他们都说我有病。”
“他们是谁?”
“就那帮小孩呗。”
“什么病?”
“艾滋病。”小峰轻描淡写地说。
“别听他们的,他们都瞎说,咱不是那种病。”王立军撒了谎。
王立军和小峰在一起的时间,比和自己的外孙女都长。每天早上,他骑50多分钟的自行车,到教室后先烧一壶水,倒水都不让小峰动手,因为怕他烫到。铅笔,是王立军削好的。连手纸,他都撕好了叠成块。
从一开始,王立军就想让小峰在这间特殊的教室里体验到一个正常学校所能拥有的东西。贴在教室墙上的课程表里,标注着教师到校时间、学生到校时间和升旗仪式时间。尽管教室里只有一个学生,但他总是站得端端正正地讲课。除了语文和数学,他还开了体育、音乐和美术课。他带着小峰春游,最远的一次坐车去了100公里外的丹东。小峰在游乐场里开了碰碰车,他记得那里的羊汤好喝极了。
今年六一儿童节,王立军试探着给隔壁村的小学打了个电话:“你们哪天开运动会?俺们不参加,我就领我学生去看看,开开眼界。”那所小学的教导主任很痛快地答应了,检录组还特别增加了小峰的名字,让他参加60米短跑。
“我就说,把我的病都治好。”
自打村小合并到乡里后,没有上课铃的早晨变得缓慢而宁静。
7点50分,村里剩下的最后一个小学生来了。“上课。”王立军在办公桌兼讲台前喊了一声。对面椅子“哐啷”一响,小峰半应付似地站起来。
“同学们好。”老师对教室里唯一的学生说。
“老师好。”小峰含混地应了一句。
小峰也是这个村庄里最后的艾滋病患者了。
2008年12月,小峰母亲艾滋病病发又感染上脑病去世了。
小峰被吓得眼泪也没有了。可是在火葬场,当母亲被推入火化炉时,他哭了起来。
十几天后,父亲突然说不出话了。在床上躺了19天后,他永远闭上了眼睛。
小峰带着家里的彩电、装着照片的红皮箱还有一床军绿色的铺盖,吸溜着鼻涕住进了姑姥姥韩玉君家。这是他在村里最后的亲戚,也是唯一愿意接纳他的人。
韩玉君家没有小孩,村委会答应每天支付60元工钱后,她把小峰领回家,给他做饭、洗衣服,每年还给他过生日。这个男孩刚来时很听话,也很少提起自己的父母。只是在夜里,他常常哭醒。
“想我妈。”在韩玉君怀里,他哭着说。
小峰父母去世后,每季度去防疫站抽血的工作落到王立军身上。这个孩子对他相当依赖。
“我俩感情挺深。”王立军说。家里的红富士苹果,小峰挑出最大的送给王立军。有一年,王立军骑车上班时滑倒在雪地里,小峰看他一瘸一拐的,非要让他坐下来讲课,还“闹劲儿不喝水”,因为怕老师打水要走来走去。
这两件事,王立军给不同的人翻来覆去地讲,“我真挺感动的”。
小峰记得别人对他的好。尽管韩玉君会抱怨,他这一年长得“又高又胖”,吃穿比以前费了不少,可小峰知道,村里对他最好的还是姑姥姥。
“姑姥,要是有人欺负你,你告诉我,我把手割破了,把血往他身上抹!”他放了这样的狠话。
对于艾滋病,他还没有显出太多畏惧。在小卖铺里碰见害怕他的外村小孩,他使劲解释:“没事,我出血、你出血,伤口碰一块才感染呢,平常接吻都不会传染。”
他的话把成年人逗乐了。有人忍不住逗他:“你怕死不?”“我不怕。”他飞快地回答。
但他曾跑进村里蓝色屋顶的教堂,跟着大人们一起唱圣歌。祈祷时,他闭上眼睛,“我就说,把我的病都治好。”
“算了,他还能活几天,抽就抽吧。”
因为吃药的事,韩玉君这天早上动了气,“人家想买这个药都买不到,国家白给,你还不吃。你爹妈要是吃这个药,不见得死那么早。”小峰歪在炕上不吭声。他本该在早饭前吞下3片半白色的抗病毒药,可这一年来,他渐渐拒绝吃了。
面对进入青春期的孩子,韩玉君很发愁。
吃药同样也是王立军和小峰之间通常的话题。正式上课前,师生之间总要重复这样的对话:
“吃药了吗?”
“吃了。”
“真吃假吃?”
“真吃。”
“可不兴骗我,那是害你自己。”
这天早上,小峰不说话了,其实他并没吃药。“我忘了。”他承认时缩着脖子一笑,有点不好意思。
奈韦拉平、拉米夫定、齐多夫定,这些读起来拗口的抗病毒药,应该早饭前3片半、晚饭后两片半,每天如此。别人告诉王立军,如果不持续服药,身体可能会产生耐药性,“到时就麻烦了”。
听到小峰又没吃药,他皱着眉头直叹气,“跟他说了,没用。你说怎么办呢?咱们也就只能起个监督作用。”
比起吃药,小峰自己更上心的是,这个下午能不能在池塘边找到刘立宝,那是他今年才认识的新朋友,和他同岁。
7年来,村里人已经接受了这个“特殊”的孩子。有人在路上碰见他,还问一句:“上学啦?”可他依然交不到朋友。大多数时候,他只能到废弃的鱼塘边看老头儿钓鱼,或者跑到大桥边看火车。
刘立宝是邻村的孩子,俩人在广场跳舞时认识的,两个男孩在这里成了搭档,小峰跳男步,刘立宝跳女步,尽管小峰比刘立宝还矮半头。
起初,刘立宝的爸爸并不同意自己的儿子和小峰来往。可刘立宝觉得,小峰比那些拔掉他的自行车气门芯的男孩强多了。趁父亲不在家,他带小峰回家打游戏机。
小峰还偷偷学会了抽烟。他走进小卖铺,假装帮别人买烟。老板本来不想卖给他,可有人在旁边劝:“算了,他还能活几天,抽就抽吧。”
“像他这样的情况,到了18岁怎么办?”
按照防疫站的检测,小峰已经是艾滋病人了。病毒破坏了CD4免疫细胞,他的身上开始经常长出疱疹。在最近的检查中,这项免疫细胞指数又下降了,防疫站怀疑小峰对正在服用的药物出现了耐药反应。
王立军并不清楚防疫站都检查了些什么,他只是按时带着小峰去那里抽血。
王立军很少再提小峰回正常学校的事情,他明白,这已经不大可能。关于小峰成年后学校还会不会开下去的问题,他也是盯着提问者沉默了半天才说:“这就不知道了,没有想过。”
但姑姥姥韩玉君必须考虑这些问题。小峰现在每个月的开销,是由留在村里的那部分遗产支付的,加上韩玉君的工钱,每月2300元左右。物价再这么涨下去,伙食费就不够了。她找过村委会,可村委会也发愁,这笔遗产只够支撑一年多了,以后只靠每年2600元的农村低保补贴,更不够负担这个孩子的开销。
“你说,像他这样的情况,到了18岁怎么办,国家还管不管?”韩玉君问。
为钱头疼的还有副乡长刘晏清。本来,王立军每年1万元的工资是由县财政、乡政府和县防疫三家共同支付的。但防疫站改为疾控中心后,没有这笔专款了。刘晏清打算跟县财政争取一下,“实在不行乡政府想办法,无论如何保证王老师的工资。”
说起这些,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连抽了两根烟。更让他发愁的是,“爱心小学”不可能一直办下去,这个毫无技能的孩子成年后,走向社会该由谁来管。
没人把这些事告诉小峰。他刚刚找到好朋友,还有了新宠物——姨夫抓来的刺猬。他更关心过生日时,刘立宝会不会像答应的那样,送他一份礼物。他还有很多梦想,盖房子、当警察、上“星光大道”。
他14岁了,已经和艾滋病毒共处了14年。成年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一件那么确定的事情。
(《中国青年报》11.2 王晶晶)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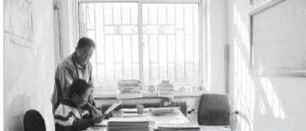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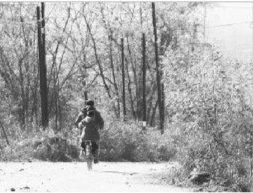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