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这一辈子,有一项任务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的。大体上,一到两日内,至多不出三日,必须入厕卸货。次数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不然肯定是皮囊出了大问题。
由此算来,若以人寿七五,每日一番,一番耗时15分钟计,则人生需以蹲姿或坐姿,在厕所里度过7000小时上下。我们这时只能在孤独中与异味相伴,西人雅喻大小便为“自然的召唤”,非常传神,也很能传达此时的无奈。
不过,即使厕所被彻底现代化了,通体光亮如鉴,灯火辉煌,仍是没有多大魅力可言的。人体的进出口两个环节,颇能反映人性的两面:每有美食,大家便喜欢相聚而餐,这反映着人的社会性;入厕者则多孑孑而行,成帮结伙的甚少见。不管厕所盖得多么富丽堂皇,尚未见过引来公款消费的热潮,可见厕所不是个能够享乐的地方。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这项差事不管多么无趣,却有个莫大的好处:你只管坐着就成。所以,为消磨这新陈代谢夺去的时光,自打粗通文字起,我就养成了一种如厕阅读的习惯。
因为时间有限,这样的阅读面是极受限制的。最适宜此种场合的,要首推小时候到处可见的“小人书”了。回想起来,至今犹能记得“三国”中一些情节,并不是年近弱冠时读三大卷正本的结果,倒要感谢光着屁股看画的经历。收获之一便是看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话,居然让曹操“闻言大喜”,使我后来很顺畅地领悟了看问题为何要有“辩证眼光”,对一些不明就里的迂阔分子,老想还曹操在《三国志》里的清白,也就不太在意了。其实,歪曲不光是渲染夸张的修辞手法之一,更是一种潜意识的流露。作恶的冲动,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灵魂深处,曹操的形象,一向就有不知多少人暗自倾慕。所以《三国志》的读者群才远不及“三国”,更遑论社戏中的《捉放曹》了。此乃民族心理发育史的题目,遵循时下的犬儒精神,不便多讲。不过,常听见有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却对宋宰相赵普“臣有一部《论语》”的原话从不再提。我一直就纳闷,为啥从未听人说出此种现象的正解呢?为防继续谬种流传,不妨本着“明言与未明言者同样重要”的原理,把它的心理重组机制说破罢:以整部《论语》治天下是要出麻烦的,故只可用半部,另外需以半部“三国”补充之。而没了白脸曹操,补了岂不是也白补么?
有这么点儿见识,自然要感谢当年离我家不远处那个砖砌的小屋。
再往后,马齿见长,不好意思翻小人书了,于是把诗歌散文小品之类渐渐请进厕所。我知道人粪在《本草》中还有个“人中黄”的雅号,便是厕所里“讽诵”周作人的成果。他也有篇写厕所读书的应景文章,记一日本诗人把寺庙的方便处刻画得风雅无比,拿来跟中国寺院周围的污秽斑斑做比较。读到这里心里打鼓,人家老爱骂他,是不是真有道理呀?不过最令我感动的,当是在钱锺书的《七缀集》里看到的,中国也有个无比美丽而我闻所未闻的雅号——“繁花似锦的故土”(the flowery land),钱先生直来直去地把它译为“华国”,虽略显会通中西的功夫,却未免有些扫人的兴。当然聪明如钱锺书者,也给我留下不少感佩。他曾借用以赛亚·伯林的大作《俄国思想家》中“狐狸多智巧,刺猬只一招”的著名隐喻,意不在突出执著与圆滑的对立,而要说明风格迥异之人也可相互“爱好”与“仰企”,这比故意制造紧张气氛的伯林厚道多了。至于他讲到有些令画家无从描绘的状态时,是以《拉奥孔》中地狱“没有光,只有无碍于观察的黑暗”为例,这种淡漠阴阳两界的说法,让我在好久一段时间里,无法摆脱不知生活在何处的惶惑。
钱著我读得不多,但脑子里有这本《七缀集》的只鳞片爪的印象,对于后来仰慕钱氏者要创“钱学”的计划,也着实捏着一把汗。因为以我的感觉,他不但是个狐狸,而且狐狸得一塌糊涂。对于现今的学术门类,他是从不入套的,只身一人悠然穿行于故典(或古典)丛中,不但让脚注和文中注充斥着英法德拉数种洋文,且把伯林与苏轼和司空图置于一起讲论,以休谟讥讽中西诗歌交流史上的荒唐事,还能拿荣格去声援林琴南。对于那些把钱先生当“国宝”的人,他之不好对付的程度,可想而知。
这样的阅读得来的,也只能是以上这些鸡零狗碎的小感悟。入厕求学的范围,大致也以此为界,不能再求更愉悦更高深的东西了。看小说不可以,这容易导致废寝忘便。海德格尔更是万万读不得,就如纯金锻造的马桶不会给屁股带来丝毫富贵相,在厕所里读这个,等于把数千时辰的人生全瞎了。
不过这种经历中,也有增长我不少见识的。刘勰的《文心雕龙》过去是粗读过的。作者从中撷取只言片语置于各篇之首,然后调动古今中西的大量史论资源,发微掘幽,专在“殊语一义、貌异心同”处下工夫;下笔虽潇洒肆意,文脉却紧凑得很。只要有耐心读文言的人,不需水平多高,这书很容易为你带来中西一家、其乐融融的美感,尽管那可能只是一种幻觉。对此,书中所引法儒波德莱尔的名句:“美者未必真,真者未必美”,倒是可以引为警策。这让我大有感悟:看书要看出大门道,缺了眼力与学识是不行的。
近些日子在厕所里看的,恰好便是这位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收入了作者称为散文诗、“总之,还是《恶之花》”的千字文。确实,那调子依旧阴暗得很,把艺术家追求美的努力称为失败前的哀号。但书中也有两件让我高兴的事。有一段讲到中国的文字,以“青翠的木叶”和“精美的花草”来形容华夏大地,这与前面“繁花似锦的故土”之说出于同一时期,既可印证“华国”之译欠缺时代意识,又提醒我们欧洲左派于“文革”时表现出的东方朝圣情结,病根是在百多年前就种下的。另外书中有数十幅木刻插图,每看一页,便有重温儿时入厕读小人书的感触——只是在那细腻而僵直的刀工中,古典与浪漫时代必备的优雅曲线已踪迹全无,与波氏颠覆真善美统一性的用心倒是十分相契。
话说到这里,便想起一件不时遇到的事情。与朋友交杯换盏时,常有些在座而不相熟的人问:“先生曾在何处就读?”以我这种从未就读于某学府的人而论,若不怕倒了人家胃口,倒是大可以说:“在下不才,只能如厕就读。”地方是寒碜了点儿,但说句良心话,现在的就读条件,比看小人书那阵子,可有天壤之别了。
(摘自《我书架上的神明:72位学者谈影响他们人生的书》,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版,定价:5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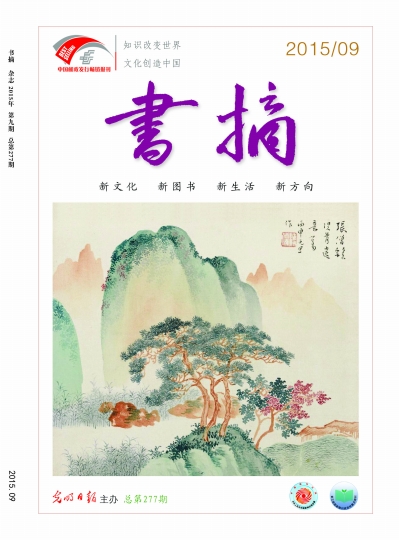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