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们以为“东亚病夫”是西方人刻意用来侮辱中国人体质的词,以至于在各种场合力图雪耻。从《精武门》等影视剧,到奥运会收获颇丰的金牌,我们使劲证明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不过,“东亚病夫”真是西方人造出来耻笑中国人的吗?
台湾政治大学副教授杨瑞松认为,“东亚病夫”乃是中国人“ 自我东方化”的结果。后殖民理论认为,西方人出于偏见和某种需要,塑造出一个模糊地、含混的“神秘东方”,将中国、日本、朝鲜等国家混在一块儿,然后肆意扭曲。所谓“自我东方化”,就是我们认同西方的看法,从西方那里借来概念,然后加工加料,自我丑化。
1896年10月17日,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转载伦敦某报一篇文章,次月被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转译成中文,标题为《中国实情》。文中首次提到“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但不是谈中国人身体素质不行,而是谈清朝官场腐败导致军事改革和政治改革失败。作者虽然说中国是“东方之病夫”,但本意不是侮辱中国,而是希望“北京执政之臣,若果以除旧弊、布新猷为急务,势虽汲汲,犹未晚也”。原来老外眼中的“病夫”是隐喻,意指中国的政治不行。
在西方,“病夫”是形容一个国家欲振乏力的惯用语,最初是指奥斯曼帝国曾经那么辉煌,到了近代却腐朽不堪。甲午战争令全世界很惊讶:大清帝国竟然斗不过小日本,而且一败涂地!于是西方人将原本形容土耳其的“欧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套用到中国身上,改成“东亚病夫”(Sick man of East Asia)。后来“病夫”这个词在中国很流行,但谈得最多的并不是西方人,而是中国人自己。
严复、梁启超经常用“病夫”来形容中国:政治不民主,甘于为奴,改革速度缓慢,官场积习太重,致使国家变成“东亚病夫”。严复曾提到鸦片和缠足影响身体健康,但他并未用“病夫”来形容国人的体质。后来严复引介社会达尔文主义,梁启超深受影响。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民说》,首次用“病夫”来形容国人的身体。他认为一个国家要强大,首先人种要好,而中国男子手无缚鸡之力,以文弱为美,还吸食鸦片,“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
梁启超可能是首位将“病夫”与国人体质相勾连之人。鉴于他在中国舆论界的影响力,“病夫”从专指无力振兴的国家,逐渐指向身体孱弱的国民。谭嗣同曾言:“且观中国人之体貌,亦有劫象焉。试以拟诸西人,则见其萎靡,见其猥鄙,见其粗俗,见其野悍。或瘠而黄,或肥而弛,或萎而伛偻,其光明秀伟有威仪者,千万不得一二。”国人体质成为突出的问题,推动了清末的天足运动和鸦片禁政。当时中国人编了很多故事,说西方人如何耻笑我们的身体,然后说西方人卖鸦片给我们,还骂我们是东亚病夫,这是“二次侮辱”。其实,与其说是西方人攻击我们,不如说是中国人自我刺激。
尽管当时中国破败不堪,被西方人瞧不起,但中国人总觉得有识之士会了解中国的潜力。我们认为拿破仑曾经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着的狮子,一旦被惊醒,世界将为之震动。奇怪的是,这句话似乎找不着出处。后来,杨瑞松查阅了英国《泰晤士报》的原始文献资料库,仅发现1936年有一条拿破仑与中国沉睡论相关的文献,但文中并未提及狮子。澳大利亚学者费约翰在《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一书中也做了地毯式考察,发现所谓的拿破仑中国沉睡论并无确切文献证据,该说法可能是建立在19世纪一则谣传之上。
当时西方舆论界常说中国是睡着的巨人,但不是说中国醒来后会多厉害,而是说中国昏睡不醒,停滞不前。清末外交大臣曾纪泽用英文写了一篇很漂亮的文章叫《中国先睡后醒论》,似乎在回应西方的批评,认为中国终究会醒来。不过,他没说中国现在是睡狮,醒来后是雄狮。在“睡狮”这个民族意象的建构过程中,担任重要角色的人仍然是梁启超。1899年,他在《清议报》发表《动物谈》一文,将中国形容为一个状似狮子的机器怪物,说它就是曾纪泽所说的睡狮。梁启超可能记错了,硬生生将“睡狮”这个说法归于曾纪泽名下。梁启超并不是欣喜于中国的潜力,而是担心中国再不醒来就将万劫不复。甲午战争后,各项改革在进行,但梁启超非常悲观,觉得国家并无起色。在他笔下,“睡狮”其实是负面形象,跟今天的“睡狮”含义不同。
有趣的是,“睡狮”曾经牵涉满汉斗争。清末有人就用“睡狮”来形容汉人,说汉人本是雄狮,只是被异族奴役后睡着了。“睡狮”的说法现在很受中国人欢迎,但起初很多知识分子并不喜欢它。胡适宁愿把中国比作“睡美人”,清醒之后倾国倾城。胡适认为,中国文化应以软实力令世界倾心。然而,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说,“睡狮”很对备受欺凌者的胃口。
(摘自《我读:陪你读到世界尽头》,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年5月版,定价:3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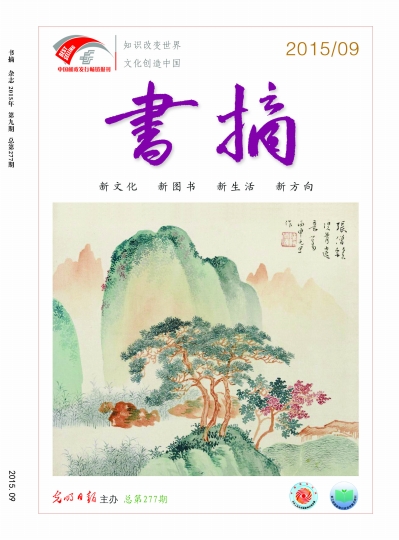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