鹌鹑记
如果单说世间好吃的标准,你不要参照《圣经》,上帝不吃菜。我姥爷有一句美食格言:“论吃飞禽,鹁鸽鹌鹑;论吃走兽,猪肉狗肉。”此言一出,就框定了味蕾愉悦的范围。对于村里多数人家来说,猪肉是熬一年到春节时才能吃一次,我们恭称“大肉”(却没有“小肉”一说)。对于我,里面四种之一的鹌鹑却可以不时飞来飞去实现。
我姥爷另外还有一格言,曰:“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不过此时不能跑题说驴,必须来说鹌鹑。
鹌鹑予人以智慧。我二大爷当年在傅作义手下当排长,兼炊事,兼背黑锅。他也说:“吃鹌鹑可以使人聪明。”
我在乡村上小学,成绩不佳,我就想聪明,我想讨好老师。一放假我就怂恿姥姥到离我村五里开外的张堤村走亲戚,要找我姑姥爷,他有一张鹌鹑网,他会玩鹌鹑。
我姥爷概括这世间人类的癖好,是“好者好,恶者恶,玩鹌鹑的不打兔”。
一年四季,我姑姥爷就腰挎鹌鹑布袋,每次斗鹌鹑必出场,他是方圆十里一雅士。雅士说:鹌鹑以清炖为最好。
譬如,鹌鹑可以和枸杞、和人参、和冬瓜、和栗子、和山药、和萝卜等元素结合。总之,一只鹌鹑它和啥都能同炖。
我家那时囿于条件,只能白水清炖鹌鹑。这是一道荤菜素制。
下面才进入鹤鹑主题。
历来哪有百姓不缴皇粮的?我姥爷撇开猪肉又说过去。
那些年,我们村里年年缴公粮,人民公社美其名曰“爱国粮”。一年下来,打下来的麦子最后剩下百十来斤。除了够喂鹌鹑,还剩下了一颗“爱国心”。
这天下晌收工,我姥爷有闲,给我讲过一首元人散曲小令,说的是世间如何尖刻相。忽然,就翻出来了一只鹌鹑。
“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得手。”
准确说是里面说到了一个鹌鹑嗉。
这时我二大娘来送一张簸箕,恰恰听到,簸箕放下了,却听得半明不白,疑问道:“你说的这老先生是李书记吧?”
那一年,李书记带领滑县“革命工作委员会”在我村驻队,在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喝酒前,他让我逮过鹌鹑。
吧嗒杏
杏仁是一味中药,能治咳嗽,但杏仁有毒。童年时我家养了一匹小羊,羊龄两岁。那一年春节前,误饮了几口姥姥泡过杏仁的苦水,然后,踢蹬了几下,小羊就倒下了。
那匹小羊生前还抵过我。有一次,我刚进厕所,它就急急地也跟着冲进来,吓得我当时都来不及提裤子,就跑了出来。
有一种杏仁无毒,我们叫它“吧嗒杏”。杏仁是甜的,不浸泡直接也可生吃。
我小时候生活在北中原的一个杏乡,叫留香寨。就凭这村名,你可以想象杏花开放时的程度,花的密度容不下最细的炊烟和鸡啼。村里人靠卖杏过生活,或用杏换麦子。我跟着大人们卖杏,至今还记得用楝树叶垫杏可保鲜的乡村秘诀。
我们村子里的人到外村卖杏时,常被别村的小孩子起哄吆喝,他们唱即兴自创的民谣:
吧嗒杏,苦的仁儿,
卖杏的,是俺侄儿。
这歌词的中心思想是编派骂人的,专骂卖杏的。
我们村卖杏的人机智,马上随口吆喝出另一种版本的歌谣,以示反驳:
吧嗒杏,苦不苦?
买杏的,叫我叔。
这样,一曲歌谣就把辈分扯平了,一来一往,势均力敌。几近国共舆论上的战争宣传。让我能想到部队文工团阵前喊话的重要性。
关于杏仁,我童年时还有一种说法,近似乡村秘籍:
把一颗杏仁小心耐心地去揉软,然后,放到自己的耳朵眼儿里(男左女右),呵护着,一星期之后,可以孵出小鸡来。
这曾是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告诉我的,当时,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
这方法我曾试过,最终也没有孵出来小鸡。而且有一次杏仁掉进耳朵眼儿里,险些掏不出来。我就问姥姥,姥姥笑了:那是专骗你们这些小孩子的。
不过现在我还存有一丝幻想,要是当年再揉软一些,是不是还真能孵出来一只小鸡?我是相信着。
正因为我一直心存如此幻想,长大后,我才能当一位诗人。
吃过大盘荆芥
荆芥和薄荷都传列我的《异味志》里。
但是荆芥特异。荆芥与见识成正比。
我们北中原有一句俗话,形容一个人见识广博,经历过大世面,就会拿来荆芥,称这人是“吃过大盘荆芥”。荆芥一时成为一种成功与否的标准。
此为我村之见。亦如我见。
可见,吃小盘荆芥的都是一些凡人、小人物。要想出人头地,你必须改成大盘。
还有更多人是不吃荆芥的。
荆芥在其他地方不食用,多当中药材晒干使用,用于煎服治疗感冒、发烧,祛风解表。只有我们北中原乡下这一带采叶用于生食,凉调,或拌黄瓜或拌捞面。一千多年前的中原人就嘴馋,宋代苏颂《本草图经》说它“辛香可啖,人取多生菜”。这“人”就是河南人。它多有一股怪味,一般人承受不了。就像政府官员听到批评一样。
吃荆芥,你得胆大。
我曾经说过,荆芥、芫荽、薄荷,这些都是菜蔬中的异己分子,风格独行且为数不多,不俗。我自认为,张岱、八大、傅山,都是一身的荆芥味道。
荆芥本来就不宜多吃,一小碟,一捏,一棵,一叶,尝一下味道而已。荆芥价贵,过去一般是买菜时多趁机捎带上几棵。
如果一旦染上嗜荆芥之好,就百吃不厌,走火入魔。会拍案叫道:操,不过了,再来一盘荆芥。
在我们那里,荆芥的播种带有点乡村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秋后,姥爷将荆芥棵拔出,捆成一束束,吊在屋檐或窗棂,像“荆芥手札”。第二年谷雨时节揉碎,撒籽。姥姥说过,种荆芥时,撒籽不可离地太高,荆芥籽受惊还能跌死。
我都是呵护着荆芥,拌上土粒撒籽的。
【补记】:原以为天下只有我村才独吃荆芥,满口异味,走入社会后,知道豫东、豫南、菏泽、襄樊等地的人民也吃,且情有独钟,才知道自己眼界果然狭窄,真是没有“吃过大盘荆芥”!
(摘自《说食画》,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年5月版,定价:4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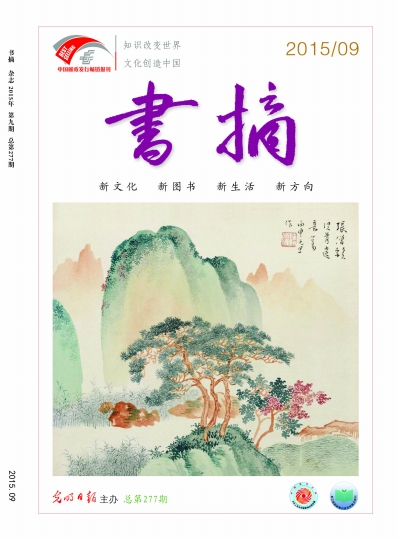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