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越然有一个生年,两个卒年。一说(一八八五至一九四六),一说(一八八五至一九六二)。现在确定后一个是正确的,但是网络上排在最前面的周氏生平介绍,还是沿用错的(一八八五至一九四六)。这也难怪,周越然这个名字及其藏书事迹被提起被读者了解,仍是年头未久呢。最早(八十年代末)公开提到周越然的是知名藏书家姜德明先生,他在《言言斋谈书》里写道:“现代藏书家中,喜欢写书话的,其中有一位言言斋的主人周越然。他长期生活在上海,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担任过英文科长,因编辑《英语模范读本》、《英文造句法》等工具书而闻名,同时也给出版家带来不小的利润。他熟悉海上书林掌故,喜欢收藏线装古版书及英文版本。又有人说,在他的藏书中有不少中外文学的禁书,如明版《金瓶梅》等。在他写的书话里,果然有《西洋的性书与淫书》、《外国〈金瓶梅〉》等类似的题目,证明外界传言之不假。”
周越然之所以成为富甲一方的藏书家,他的第一桶金来源就是上面说的《英语模范读本》。周越然拿的是版税,此书越畅销,他得的钱越多。凭着版税,周越然盖得起藏书楼,“言言斋”既是他的斋号,也是藏书楼的名字。周炳辉在《琐忆祖父周越然》里写道:“祖父的藏书楼,名曰‘言言斋’。那是一栋中西合璧的建筑,原位于上海闸北天通庵路三省里,前有花园,后有菜园,两旁植树,全地占二亩半。”
周越然于“言言斋”之深情,好比丰子恺于“缘缘堂”之厚意。这两座书楼有共同之处,均为主人亲绘图样,监理施工;落成后均未多及享用,皆为日寇炮火所毁。丰子恺悲愤不已,写有《还我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周越然在日记中写道:“一个月前车夫小虎往闸北窥探视,见三省里房屋尚未全毁。入门,见书桌上余常用之《牛津袖珍字典》尚无人盗去,即取之而出。今日(言言斋已证实全毁矣)静坐无聊,余在其封面后,护页上作一短跋如下:‘余藏西书约二千余种,内有绝版者数十册,闸北之战,余家首当其冲,所有三省里五号自建房宇,中西书籍,及一切日用之品,均被焚毁。此仅存之西书也,留之以作纪念。’”(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
当时的报纸也对言言斋遭轰毁作了报道:“英文专家周越然先生,在商务印书馆供职,任函授学社副社长及英文编辑主任。其著作尤以《英语模范读本》为当世所传诵。居恒俭朴无嗜好。二十年辛勤从事于著述,所集酬资悉数采办中西典籍。近数年来,所得中西名贵古书尤夥,收藏于闸北通庵路五号自建寓所。据闻沪变后,全寓被炮火所毁。该寓占地三十九方六,其藏书出名言言斋,藏有宋元明清精本约二千数百种,计一百六七十箱,西文三千余册,内有绝版者百余种,古玩二百余件,及太平天国文件等,悉付劫灰。”(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时事新报》)
言言斋被毁,却留有少少残值,周越然在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记有此事:“闸北三省里焚馀墙壁及铁门、铁栅等,由庄百俞君经手代为售去,得价六百五十元。承购人先付二百元,其馀言明月底付清。言言斋为余半生心血所成,其房屋及其内容,共值十余万元,而收回者只此细数,真烦闷亦可笑也。”
周越然的藏书尽付一炬了么?好像言言斋尚存有相当烬余之物。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一日,上海,《杂志》社举行“掌故座谈会”,出席者有:内山完造、包天笑(六十九岁)、松平忠久、周越然、徐卓呆、福间彻、钱芥尘。另有《杂志》社人员鲁风、吴诚之、吴江枫。三位日本人中,内山完造不必介绍大家都知道;松平忠久在广东岭南大学读过书,能说广东话、北京话和上海话,对于中国各种戏剧尤有研究,时任上海日本使馆事务所报道部长。福田彻居上海多年,曾于上海同文书学院读书,时任上海日本使馆事务所副领事。
包天笑乃在座最年长者,由他作开场发言,谈清末的作家和文坛掌故。包老说清末最享盛名的四大小说《孽海花》《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曾孟朴、刘鹗、李伯元、吴趼人四人,“只刘铁云先生不相识”。若说摆老资格,这就是了。包天笑说到李伯元编辑《绣像小说》,这撞到周越然强项上了,他接着包的话茬道:“说起《绣像小说》,我还藏着全部,共七十二期。现在外间很少见,弥足珍贵的了。它是用拷贝纸印、铅字排的,绘图非常精致,每月出版一本,仿佛月刊的样子。我知道商务印书馆倒没有这样全部的绣像小说了。”好一副藏书家惯用的口吻。商务印书馆及东方图书馆于“一•二八”损失惨烈,计算金额高达一千六百万元。
周越然接着说:“我去年到日本去(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年会),看见他们的东方文库,藏书极丰,我国各地的府县志,几乎搜罗俱全,但是我故乡湖州的《武康县志》却没有,《武康县志》在我国图书馆里也找不到的,一共只有二部,由我收藏着,可是一部已经烧掉,现在只剩一部,真可谓硕果仅存了。”《武康县志》烧了一部,还有一部未烧遂成海内孤本,可知周越然不只言言斋一处存书。
《杂志》社见周越然面有得色,也凑趣道:”周先生藏着许多名贵的孤本,将来有机会可以开一次小规模的文献展览会,给熟人看看。”
周越然也不怕露富:“是的,我还有二百多张宋版的叶子,宋版的部头书,难免是赝鼎,这些单张的叶子,倒都是真正的宋版。”按照古已有之“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算法,周氏这二百两黄金,是另一种摆老资格。谢希平在《记周越然》中写道:“廿一年闸北大火,损失不知多少,但是现在到过他的藏书室里的人,还是叹为观止,尤其是经史子集的单页宋版和明本的《金瓶梅》一类的伟大收藏。”
周越然还有一种光荣,他做过胡适的老师,尽管只教了两天,古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周越然说:“胡适原名胡洪骍,曾在中国公学读书,我教的是近代史。当时在中国公学教书很不容易,教师要讲两种话,一种是北方话,一种是广东话,因为一半是北方学生,一半是广东学生。我因为讲得太快,一口气教了几页,学生们吃不消,便请我不要教下去了。所以,胡适只做我二天学生,呵呵。”
诗僧苏曼殊与周越然做过同事,周越然大揭诗僧老底:“民国二年光景,我在安徽高等学堂教书,与苏曼殊同过事,他性懒,专拣轻松的功课教,有时听得上课钟声,反拥被而卧,不高兴起来去上课。他喜欢吃蜜枣、雪茄烟,还喜欢嫖堂子吃花酒,到了妓院里,一个人自顾自酣睡,性情非常怪僻。”教过两天的学生胡适之,同过事的苏曼殊,现在的名声远胜周越然。周越然以藏书为胜事,勉勉强强今天还有极少的人记得他,出版他的书。周越然几本谈藏书的旧著有人出很高的价钱来收买,尤其是《书书书》印数仅一千,更为珍罕。
周越然的酒量也很有名,谢希平说“他每顿必需喝啤酒呢,每饮起码要近一打,黄酒呢,也要五六斤,‘醉’字在他的字典里是没有的。可是现在酒价太贵了,周先生不但顿数改少,喝的时候,也加以统制了,有时竟可不喝”。
本来藏书之事与政治,风马牛不相及。可是非常时期,藏书家欲洁身自好,也难。周越然在日据时期,发表了很多文章,抛头露面,没有像别的文人那样学会韬光养晦。最致命的是周越然参加了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中的两届,难免招来众人的非议。虽然战后周越然没有遭遇像陶亢德、柳雨生等入狱判刑的更坏命运,但从此隐姓埋名,“藏书家周越然”无人再提。
“儒冠多误身”,周越然太多书生气,太少政治敏感。日据时期风头极健的张爱玲,于政治却最为清醒,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邀请张爱玲,你看张爱玲怎么回答的:“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
对待特殊历史时期文人的言行,“同情之理解”是比较恰当的态度,另外两种极端的态度和手段实不可取。事情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人们更加理智,更加客观地审视历史,但是另一种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十几年前,当年参加过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当事人自导自演了一出“南玲北梅”的闹剧,当事人的心态既滑稽又是可以理解的。近来,又有关于周越然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绑架说”盛传。《琐忆祖父周越然》称:“直到祖父去世以后,我才从姻亲王履模前辈(上海文史馆馆员)的口中了解到原委。据王老说,那年祖父去日本参加大会是被迫的,此前他被日本宪兵于深夜从家里绑架到虹口的新亚大酒店,关了多天,威逼他领队往东京,如不服从,后果可以想象。这真是生死的抉择,他屈从了。”日本宪兵不把周越然往宪兵队关押以威逼,却往大酒店里绑架,这个情节真像电影里演的。
笔者存有当年出版的画报,上面载有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东京举行)的多幅照片,全体中国代表合影一张,周越然与日本代表握手一张,周越然大会发言一张。另有一张周越然手迹“我今天到了东京,我很快乐,我很欢喜……”下面是非常之不堪的话,恕不录。尽管如此,周越然——民国时期一位藏写俱丰的杰出的藏书家是主流,那些逆流是历史带给个人的无力违抗的伤害。
(摘自《佳本爱好者》,海豚出版社2015年1月版,定价:4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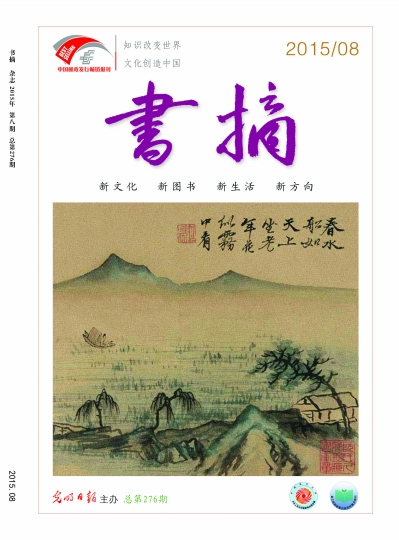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