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烧烤
在我的故乡那个土家山寨,木柴除了烧火做饭之外,再就是用于烤火取暖。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备有大大的火屋,他们选择靠墙的一方,用三块长长的条石一围,再用泥土压紧,就便形成了一个矩形的“火塘”,我们叫它“火坑”。
土家人的“火坑”,既是全家人生火取暖的地方,也是用于来客烧水泡茶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烧烤”食物的地方。
冬日里,大雪封山,什么事也干不了,全家人就一起围着“火坑”,一边取暖,一边拉着家常,打发寂寞的日子。 “火坑”中柴火烧得旺旺的,吊在柴火中央的炊壶“扑哧扑哧”地冒着热气,男人们不时地涮了茶罐,就着新鲜的开水,一遍又一遍地泡着罐罐茶,将一罐浓酽的苦茶喝得有滋有味;女人们坐在靠窗的地方,借着窗外的雪光,不停地做着农忙时遗忘的针线;喜烟的人们不紧不慢地裹好了山烟,将长长的烟锅伸入火中,连火带灰地只一刨,白雾般的浓烟就从口中徐徐地喷了出来……火小了的时候,自然是忘不了再添上一两块薪柴。就这样暖暖地坐着聊着,坐困了,聊困了,有茶有烟;坐饿了,聊饿了,“火坑”里有着香喷喷的烧烤。三餐并着两餐开,倒是省去了雪天里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土家“火坑”里的烧烤,大多是一些红苕、洋芋之类的食物,尤其是以红苕为最多。这些山里生产的平凡了不能再平凡的粗粮,倘若要来将它烧烤得有滋有味,有模有样,不论是从食物形状、品种的选择上,还是从烧烤的技法上,都还必须得有一番讲究。烧烤的食物太大,太圆,往往外面烤焦了,里面还是夹生半熟;烧烤的食物若太小,还未等你回过神来,就已变成了焦炭。单从食物的形状来看,自然是以不大不小的条状物为最好。洋芋烧烤过后格外地香,红苕烧烤过后特别地甜。沙坡地的红苕性干,烧烤过后吃起来有着一股栗子般的味道,平地里的红苕水汽重,烧烤过后吃起来就像秋天打霜后的柿子一样甜软。同为红苕,就因生长的泥土不同,烧烤出来后,便可吃出两种不同的味道来。
土家烧烤的火,既不是熊熊燃烧的明火,也不是烧得红通通的炭火,而是一种热灰中夹杂着细小木炭的“灰火”。烧烤之前,得先以“火坑”中的火堆为中心刨一个半圆形的沟,然后依次将食物埋入沟中,再用火堆中烧残的灰火加以覆盖,静心等候。待正面熟软后进行打翻,以新的灰火重新加以覆盖,如此几遍,待食物正反两面全部熟软后,便可从灰火里刨起进行食用了。灰火的好处在于即便是误了时间,也不至于将食物烧成焦炭。这样烧烤出来的食物,不仅皮好剥,而且剥掉外皮,里面还有一层焦黄的锅巴,撕掉一块,热气腾腾,送嘴里一嚼,喷香喷香!虽然,后来我在城里也吃过街头瓮缸里用煤炭或木炭烧烤出来的诸如红苕之类的食物,可总觉得不及家乡用灰火烧烤出来的食物地道,一想起家乡里用灰火烧烤出的食物来,就时常禁不住要流口水。
当然,土家烧烤的品种也不全是光红苕,洋芋之类,譬如冬腊月里杀了年猪,火屋的房梁上挂着有薰好的香肠,时逢家里的长辈或男人又好喝两口,女人也会拿刀割下两节,放在火里烧烤好了,拿给长辈或男人下酒。香肠的烧烤不同于薯类,必须得先洗净用厚厚的火纸层层裹了,再放入灰火中去烧,直到烧得外层的火纸成灰,里层的火纸焦黄变脆,香肠“汩汩”地冒油,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气后,方可刨起食用。自然,烧烤的香肠比起水煮的香肠来,香气要浓郁得多,味道要绵长得多。烧烤香肠万万不可乱翻,翻烂了火纸,染了灰尘,经过水洗之后,其香气和味道可就要大打折扣了。烧烤香肠乱翻为大忌!
土家罐罐茶
中国人的民族特征是崇尚自然、朴实谦和、不重形式。体现在饮茶上亦是如此,而山里老家的土家罐罐茶就更是如此了,泡饮起来总是显得是那么自然与朴实。不像日本茶道,饮上一口茶,还需具有那么严格的仪式,带有那么浓厚的宗教色彩。
土家族是好客的民族。即便是荒山野岭,有人打门前路过,不论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只要相互一招呼,主人便都会热情地挽留客人歇上一会,喝了茶后再走。
土家人饮茶,说不讲究也真不算讲究,瓷杯瓦罐的,普普通通,甚至有的茶罐盖还是一只断柄的铜勺,或一只破损的碗底,就论其茶具,说讲究也还真的讲究不到哪儿去,但倘若要说完全不讲究那也是假,一罐浓酽的罐罐茶泡出来,要让它香气扑鼻,或多或少还是有着它自己那么一点讲究的。
或许是因为山里的寒气太重,土家人再窄的房屋也都会有宽大的火屋。尤其是冬天,客人一来,迎进火屋,然后架起熊熊大火,用一把烧得黢黑的铜炊壶打来清澈的山泉,往火塘中央特制的铁钩上一挂,烧水泡茶的架势一拉开,茶还未喝,客人的心里倒就先暖和了一大半。
在土家人看来,要想泡出一罐好茶,就得先烧出一壶新鲜的滚开水。接下来,主人是不急不缓地一边不停地给火塘添加薪柴,一边与客人东家长、西家短漫无目的地拉着家常。待火塘里的红火烧得那黢黑的炊壶开始在“吱吱呀呀”地唱歌,主人也就忙着开始做泡茶的准备了。先是倒尽早前茶罐里的残茶,涮净茶罐,然后是去找来家里上等的茶叶,连同洗净的茶杯拿到临火塘的小桌凳上一字摆开。待这一切做完,炊壶里的水也就“咕咚咕咚”地开始冒横气。炊壶里的水变成了滚开水了,主人也不急,只是拿着茶罐将罐底伸到火堆里,翻转着手腕烤水气。待手中的茶罐水汽散尽,主人这才拿出上等的茶叶放入罐中,并再次将茶罐伸入火中不停地簸动,一边不时凑到鼻前闻闻其香气。土家人谓之“炕茶”。这“炕茶”的学问可大着呢!茶叶里的水汽不炕干,泡出来的茶不够香;茶叶放在茶罐里炕过火了,泡出来的茶又会有一种难闻的焦煳味。是否刚刚正好,全靠主人凭多年的经验掌握。待茶叶炕好,主人便一手拿起一把硕大的火钳,夹住还挂在铁钩上的炊壶提把,一手平端起茶罐,握着火钳的手只稍稍用力一抬,“扑哧”一声,一线白亮的水柱就激入了罐中,顿时芳香四溢。不过,这时的茶还不能够喝,因为主人的第一次续水往往不会太多,只是发开茶叶而已,即便是喝,亦太酽太苦。待茶罐里的茶叶浸润散开,主人续上第二遍水后,又拿起一只茶杯将新泡的茶从茶罐里酌出倒入反复冲过几遍,然后才会酌入茶杯恭恭敬敬地敬给客人。
这样的土家罐罐茶,喝一口下肚,顿觉止渴生津,消困解乏。遇上冬天,便觉全身暖和。若再碰上这家里有个上了年岁的老爷爷、老太太拉着你“讲古讲经”,更是笑声不断,乐趣无穷。
(摘自《那些温暖的乡野物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版,定价:3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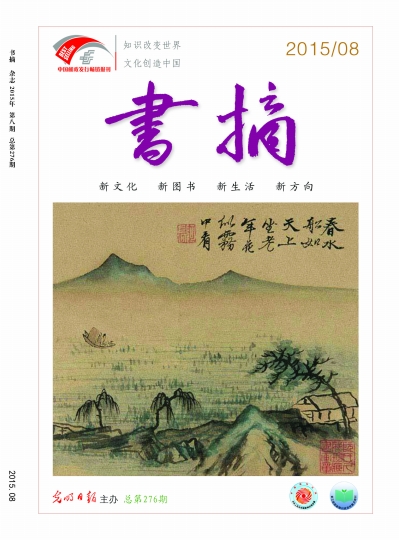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