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野光雅,生于1926年,是备受世界瞩目的绘本大师,19岁时,参加了二战。在这本人生回忆录中,他以温柔、自然、平淡的文字讲述了日本百姓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经历的苦难和战后的艰辛,波澜不惊地叙述着国家大事和个人的跌宕人生。安野光雅说自己是一位反战者。
七月七日,战争开始了
升六年级后,火灾时敲的铜钟换成了汽笛,在空袭中派上了用场。但形势还没那么严峻,大家还有兴致模仿警报的呜呜声。
然而风云莫测。我一直记得,那个七夕(日本的七夕节是阳历7月7日),竟成了卢沟桥事变的纪念日(1937年7月7日)。
驻扎在当地的日本军,不等政府指令便迅速将部队从北平推进到了太原。
津和野的长峰钟表店门口,竖起了一块写着“太原陷落”大字的牌子。我记得当时望月穿着件斗篷,所以应该是冬天了(查了一下,准确日期应是11月9日),真是相当神速。望月说:“看,太原陷落了!你们快喊万岁!万岁啊,太原陷落万岁!太原陷落万岁!太原陷落万岁!——”他连喊了三嗓子。日中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却没人知道这场战争到底遂了谁的心愿。
战争开始了。没有一个国家阻止——毕竟,日本已经退出了国际联盟。
国际局势的变幻令人不安,但对我们而言,更迫切的是近在眼前的升学考试。
父亲说,就算念完中学也找不到工作,倒不如报考工业学校可能还有出路。就这样,我报了山口县的宇部工业学校。可放榜时我却名落孙山。
从那时起,防空演习总是伴着灯火管制,学生们只能在黑色罩布透出的微弱光线下苦读。终于,防空警报不再是演习,整个日本彻底陷入了黑暗。
宇部的青春时光
落榜后,我不得不进入津和野高等小学一年级就读。正在这时,一纸征兵令发给了我住在宇部的哥哥。哥哥家是开鱼铺的,他入伍后店里就没了男子,仓促间我只得搬去他家帮忙,从此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
我觉得自己像是无根的浮萍顺水漂流。森鸥外写过类似的句子:“如水草般漂浮着,水草尚有根须,能在某处立足。”
到了宇部,我发现之前没考上的那家的工业学校还在招生。现在想来,可能是战争局势瞬息万变,学校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扩大招生,培养劳动力——我去报了名,这次考上了。
帮哥哥做生意听来很了不起,却是我与生命中至亲之人分别的时刻。家,这个亲人们长久以来生活在一起的庇护所,总会有离散的一日,这是人生的许多必然之一。从小一起长大的弟弟,似乎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与我聚少离多。离别是一种必然,却依然令人悲伤。出征时士兵们挥舞着旗帜道别,大家都知道,即便有幸从沙场生还,此生也再难相见。
在宇部的明治大街住了大约两年后,哥哥从战场回来了,我无须再扮演守护者看家护院;我搬到藤山区的山本家借宿。
时局更加紧张了,学校不得不让我们提前毕业。无论如何,不用再念书算是喜事一桩,18岁的那个元旦,我们毕业了,一股脑儿被推向职场,这几乎就是派遣令了,我们毫无选择的余地。再一次如那无根的浮萍,我被时代大潮推向了九州的煤矿。
到矿山去
我住进了名叫“诚之寮”的单身宿舍,那儿住的都是准备出征的年轻人,洗澡水都用蒸汽加热,拧开龙头出来的不是热水,而是蒸汽热风。蒸汽是从别处锅炉通过来的,烧的是煤,要多少有多少。
我被安排当爆破员,还要管理人事、发工资单,是个重要角色,被唤做“洋棒”。这是句朝鲜话,意思是日语里的“老大”,我还纳闷为什么自己年纪轻轻就能做“老大”,后来才发现这里几乎没人比我年长,年龄够当“老大”的都上战场了。
我们这群在工业学校什么都没学到的无知无畏的年轻人,就这样成了爆破员。
能在矿山工作还算走运的,虽然与危险时刻相伴,但至少不愁温饱。如果没分到矿山,谁知道我又会在哪里呢?预科练习生、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少年航空兵……都有可能。
那时举国上下大兴煤炭和钢铁生产,一门心思地造兵器。整座矿山忙到不可开交,竟有将近20名讲外文的战俘也被送来干活,没人知道他们是哪国兵。当时还征用了大量朝鲜劳工。一群好吃懒做的不良少年也从东京征调过来。按官方说法,这些孩子本来是该进少年院的,政府念及他们年轻,应以保护为主,才下了教育征调令,希望他们能改过自新。
弟弟当了学生兵
这时,我弟弟进了熊本的陆军幼年学校。那里有别于普通学校,不但不收学费,还发零花钱,学习内容也非常充实,过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旁人难以想象。还有一本书专门介绍这间学校,名字就叫《典范在陆幼——真正的人性教育》。
入学那天,校长向一排排监护人宣布:“这些孩子是以战士的身份入学的。一旦敌人登陆,他们立刻就得端起枪迎击。哪位家长若是有疑虑,请您立刻把孩子带走吧。”站在人群中的我险些就要上前一步。
弟弟换上和军装差不多的学生制服,在校舍的阴影里向我挥手,我目送他走进教学楼。要是日本没有战败,那或许就是我们兄弟的永别了。
不多时,我也被征兵入伍了。
船舶兵
同宿舍楼的前辈出征的前两晚,我们都在抱着酒杯痛饮,为他们饯行。酒是上头分下来的。送走前辈们,我也收到了征兵通知书,通知书上写:“请于4月23日下午一点赴山口县柳井的晓部队报到。”那年我19岁。
那时,父母和亲戚的孩子都被疏散到父亲的老家——山口县德山市的四熊。家里的旅店关门了,大家用店里的浴衣和宽袖棉袄换取食物,维持生计。
我家门上挂起了“出征士兵之家”的牌子。这在当时算种荣耀,没有亲人出征的家庭会觉得脸上无光。
“亲子别离”是每一种生灵的宿命,也是生命中极为珍贵的时刻。也有些“别离”是值得祝福的,就像毕业。没有不经历别离的生命。但我的这一时刻不过是正巧和出征赶在了一起。
我就这样入了伍,换上军队配发的军装,从一介平民变成了士兵。当时眼看就要入夏,我们却还穿着冬装。
我们是船舶兵,平时不和敌人正面交锋,只负责给登陆艇做掩体,方便舰队藏身、伏击。每支小队分到三把九九式短步枪,却没给配子弹,但比起食物紧缺来,这也不算什么了。
“衣食足而知礼仪”,这话确实不假。饥饿让人只关心如何吃饭,如何摆脱恐惧,其他的一切能力都退化了,女子挺身队的姑娘们来帮我们干活,我们也毫无兴致。
入伍4个月后,迎来了8月15,战败之日。我堪堪保住一条命,9月回到了父母身边。冲绳已成废墟。
农民士兵的信
日本战败,我拎着分到的一点大米回到父母身边。说句题外话,当时有长官运走足足两只柳条箱的东西,这还算拿得少的。那时有个词叫:“隐匿物资”,意思是隐藏大量军队物资,之后拿到市场上卖。
战后的混乱局势中,活着的人还是聚到一起庆祝自己捡回一命。
还有人靠考入理工科大学延缓征兵,后来跟朋友中易一郎(哲学家,毕业于京都大学哲学系)聊起这事时,他竟说:“这只怪你无知,那时这个政策没有人不知道啊。”不过想想反正当时我也交不起学费,还是不知道的好。
当然,延缓征兵也总有个期限。1943年10月21日,学徒出阵壮行会在雨后的明汉神宫外盛大举行,这场悲壮的出阵仪式被收入了战后的纪录片,我才从中得知当年的情景——那时的我准是在矿山干活呢。
战后,出阵学徒的手记《听啊,海神的声音》大为畅销。对家国的忧心和对战争的回忆,都在这本红极一时的作品中原原本本地得以呈现。
在这里,我要引用东大理学部学生、25岁的中村德郎的一篇日记。
5月18日
听说上头成立了一个什么“美术报国会”。(中略)似乎不管什么事,只要加上“报国”两个字就是好的。这个“美报”估计也就是把战争中的事画下来就可以了吧。我必须要说,现在的每件事都走偏了,偏得过头了。
这里提到了画画,我便引用一下。书里的手记还包括很多其他内容。还有一本我一直珍藏着的书,叫《死于战争的农民士兵的信》,书页已经褪色,纸张也已破烂不堪。书里没有尼采也没有康德,却关心稻子的收成,关心家里养的牛和年迈的母亲。
我反对战争,更反对在战争中将学生和农民区别对待。那延迟征兵的主意,真不知是谁想出来的。
战败后的混乱
我退役了,分到一点大米——一只袜子就能装下。我翻过出征时承载了万千感慨的山岭,回到父母避难的破屋,一起避难的那些亲戚家的孩子也都回到了父母身边。
我让大家“先别碰我”,把脱下的衣物煮沸,除净虱卵,这才觉得自己真正退伍变回了普通人。
退伍返乡后,当然不能一直游手好闲,我四处给人帮忙,做些测量被战火烧毁的废墟之类的活计。
那时今宿有家做招牌的铺子,铺子里有个爱画画的年轻人。尽管他是个不良少年,跟我却出乎意料地聊得来。他说:“我们店现在得为驻日盟军做一大堆交通标识,价格谈好了,一张80日元。”我觉得这人挺有意思,记不清帮他写了多少张,反正是赚了一笔普通兼职赚不到的大钱。世道混乱不堪,和平烟卖到10日元,雪茄卖到15日元。吉普车满街窜,整个德山市被烧成一片焦土。车站前的空地上开起了黑市,战争孤儿们扎堆过活,在乱瓦堆上风一般来来去去。近乎绝望的混沌中,只剩下对未知新生的渴望。
那时有个词叫“无可奈何老师”,意思是说,既然别的都干不了,那就凑合当个老师吧;没别的出路,只好当个老师了,颇有点儿自嘲的味道。我年轻时没听过这种说法,倒觉得只能当老师也没什么不好。
我成了一名老师,月薪150日元。但父亲完全不知道当时的通货膨胀是怎么回事(过去一栋两层的民居能卖500日元,可到了战后,500元只能换回50盒香烟),听说我一个月能挣150,乐得合不拢嘴。不料,这竟成了我对他最后的孝行。
一天夜里,母亲叫醒我,父亲已经咽气了。父亲享年72岁,在他生前住的茅草屋里过世,也算是落叶归根……
(摘自《绘画是一个人的旅行》,新星出版社2015年4月版,定价:4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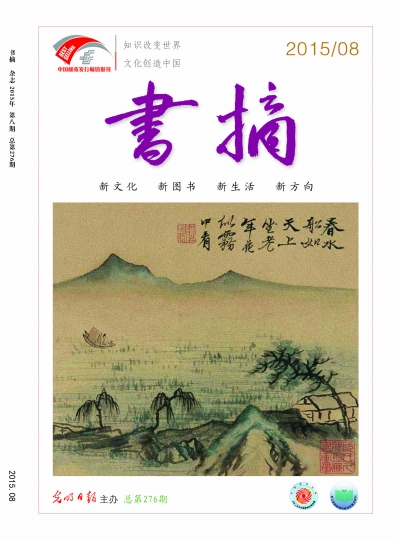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