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有一个遗憾:他从中年就想写一部关于知识分子的命运的长篇小说。他至死没有实现这个计划。起初是因为党把他布置在文学战线的一个领导岗位上;后来则是下放劳动和社会动乱,剥夺了他的健康和时间。
我记得他说过,初衷大约是要写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照党的面貌完成思想改造的历程。
然而,他也无须遗憾。假如有谁写一部传记,记述何其芳走过的道路,就会有同样启示性的意义。这是解答文学上所谓何其芳现象的钥匙。
我是曾经把何其芳的道路看做前行者的典范的。我少年时代沉湎过《画梦录》的意境,后来像何其芳那样,从“珍爱自己的足迹”,到“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厌弃了“轻飘飘地歌唱着的人们”,包括其中的自己。我清清楚楚地意识到,何其芳这个上世纪30年代的青年,从《预言》出发,经过《夜歌》和《还乡杂记》,走到《燃烧的北中国》,这就是我应走的道路。
还是许多年前读过《还乡杂记》的片断了(不知为什么,我总记得那总题是《还乡日记》)。今天重新翻开其中的《街》,那里记述了他十四五岁初入县里中学读书时经历的一次风潮。
那次风潮,不是我们后来在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学生运动,它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背景,而又不可避免受到当地权势者在背后的操纵,利用了学生(其中不乏诚实的人)中的盲目的宗派情绪,帮助了争夺一个校长职位的倾轧,不惜演出了一场丧失理性的武剧:把新任校长的行李箱子打碎了,腰斩了白绸衫,撕毁了木版的大本《史记》、《汉书》。
以十五岁的孩子的心来接受这种事变,我那时虽没有明显地表示愤怒或憎恶,但越是感到人的不可亲近。对于成人,我是很早很早便带着一种沉默的淡漠去观察、测验,而感到不可信任了。
几年以后,当他已经从大学毕业,回到这个县城,这个“凄凉的乡土”的长街上踟蹰时,他已经总结了比较成熟的思考:
这由人类组成的社会实在是一个阴暗的、污秽的、悲惨的地狱。我几乎要写一本书来证明其他动物都比人类有一种合理的生活。
这是他向往人类应有一种合理的生活的自觉。然而他怀疑在世间能找到如书籍写下的那些“金色的幻想”:
理想、爱、品德、美、幸福以及那些可以使我们悲哀时十分温柔,快乐时流出眼泪的东西,都是在书籍中容易找到,而在真实的人间却比任何珍贵的物品还要希罕。那些悦耳的名字我在书籍中才第一次遇到。它们于我是那样新鲜,那样陌生,我只敢轻声说出它们的名字。真实的人间教给我的完全是另外一些东西。当我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已完全习惯了那些阴暗、冷酷、卑微。我以为那是人类唯一的粮食,虽然觉得粗粝,苦涩,难于吞咽,我也带着作为一个人所必须有的忍耐和勇敢,吞咽了很久很久。
何其芳正是带着对“理想、爱、品德、美、幸福”这些东西的追求,而又不知道怎样在人间实现它们的茫然心情发问:
现在叫我相信什么呢?我把我的希望寄放于人类的未来吗?我能够断言人类必有一种合理的幸福的生活,那时再没有人需要翻开这些可怜的书籍,读着这些无尽的诳语吗?我们必须以爱、以热情、以正直和宽大来酬答这个人间的寒冷吗?
在不久以后的日子里,何其芳终于走向陕北的新天地。在那里开始了“一叶崭新的功课”,他从他所相信的人那里听到了、相信了“断言人类必有一种合理的幸福的生活”,并且当然也听到了、相信了“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于是他必然检视着自己身上的“阶级的烙印”,那些属于封建士大夫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可笑又可悲的遗产。我猜想,他会把往日在书籍中找到的那些“使我们悲哀时十分温柔,快乐时流出眼泪的东西”,都当做“可怜的书籍”中的“无尽的诳语”给抛弃了吧。
何其芳在《关于〈还乡杂记〉》中说过:“一个诚实的人只有用他自己的手割断他的生命,假若不放弃他的个人主义。”他说这话时是在1937年6月,他还没有投身到一个自觉的集体中去。而何其芳在民族危机高涨的时分,参加到党所领导的军事化的队伍以后,他会不仅是诚实地而且是虔诚地放弃他的个人主义和他自认为或别人指称的个人主义。他会诚实地以至虔诚地捍卫他所归属的集体和这个集体所宣称信奉的原则。
当我读着有关胡风案件的实录,在记忆中重现这一幕“阴暗的、污秽的、悲惨的”文字狱的时候,我又看到了何其芳的名字、何其芳的身影,并且仿佛听到了他在揭露、驳斥和控诉什么的声音。我相信他也还是虔诚地自觉作为一个集体的发言者,才有了这样一往无前的理直气壮的气魄。
然而,那被宣判为反党和反革命的小集团头目的胡风,也是不满于旧日中国“阴暗的、污秽的、悲惨的”生活,并且为着人类、为着中国人民能有一种合理的幸福的生活而奋斗的。
其实,在《街》这篇情调低沉的散文里,作者已经说过:
对人,爱更是一种学习,一种极艰难的极易失败的学习。
一个社会的人,如果只爱自己,当然是应受谴责的,实质上这根本谈不到什么“个人主义”,而沦为一种动物的本能。然而,如果提倡只爱自己所从属的利益集团,那仍然没有超出爱自己一家一姓的褊狭,与“可怜的书籍”中呼唤我们的爱人民、爱祖国、爱人类的美德是不相干的。
何其芳早年向往的“理想、爱、品德、美、幸福”,至今仍然是悦耳的名字,珍贵的东西,当它们同并非抽象而是具体的人民、祖国、人类相联系时,不但不该摒弃,而且应该成为我们的出发点。
(摘自《柔日读史》,作家出版社出版,定价:3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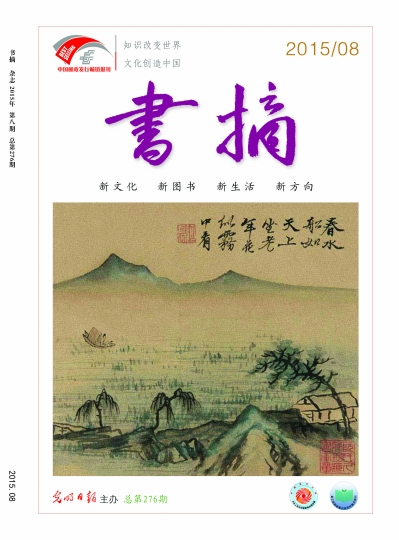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