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在本书序中认为,这部《荒漠的旅程》 “已经超越了小莲的前作《他们的岁月》”。如果说,《他们的岁月》是彭小莲以她父亲遭遇追问了“胡风冤案”的悲剧形成和可怕后果,那么,本书的两位作者——彭小莲和刘辉,则是以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刘辉一家的前世今生,对着百年中国历史提出了严峻的诘问:百年来的中国人是怎样过日子的?
本刊选取了刘辉(即小莺)大姨和大姨夫动人爱情的悲剧结尾,以展现老一辈革命者用血汗谱写的生命悲歌。
天,突然变得非常热,四周的颜色也刹那间被红色替代,连树叶都成了红色的。于是,就凭着这颜色,空气被点燃了。灼热,灼热,感觉从来没有这么热过。1966年的8月,大姨已经开始挨整了,他们也会感受到这份灼热,于是到了夜晚,大姨父匆匆忙忙从单位回家,在人渐渐少去的时候,陪着大姨跑去离家不远的“杨浦公园”散心。
在树影下,在黑暗中,他俩手挽着手,大姨用手勾着大姨父的手臂,默默地走着。我真为他们的亲密担惊受怕。那是什么年代啊,任何异性的接近都被看成是一种不正当的行为……可是,他们依然沉浸在自己的情感里。晚风,把大姨的头发吹乱了,大姨父转身,用手梳理了一下她的乱发,然后低头看着她。他们都不再年轻,他会从她的脸上看见什么?他轻轻地对她说着什么?
大姨劝小外婆上交了全部积蓄,却惹来了更大的麻烦。
外公死后,大姨和妈妈,还有舅舅去整理外公留下的东西。结果,在外公的保险箱里发现了黄金。那时候,国家规定,私人是不能储存黄金的。另外还有美金和股票,甚至有一块土地和整整一条弄堂的地契。大姨当时就提出:要全部交给组织!
妈妈和舅舅都赞成大姨的决定,可是小外婆沉默着。
都交上去,我老了,可是我也没有单位,病了,就要花大钱的!
大姨拉住小外婆的手,握得紧紧的:
小孃孃,我们不会让你吃苦头的;侬一定要相信阿拉!我们会养你的。
听了子女的话,小外婆主动交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和一点外公留下的财产。其实,不交,也不见得有什么事情;一交,造反派反而更加疯狂。1968年春节一过,大姨单位——华东电管局,联合了公用局彻底地把小外婆家给捣毁了。他们在沙发弹簧里抄出了外公藏的美钞、手枪、国民党党证,又在厨娘阿喜那里抄出了一盒钻石珠宝首饰。小外婆被扫地出门,房子和所有家产全部被没收。
他们紧接着冲进大姨家,在逮捕大姨前把她的家又抄了一遍。大姨是一个聪明人,那只是在科学和知识上;在“阶级斗争”“权力斗争”面前,她几乎和妈妈一样单纯。家被翻得乱七八糟,结果没有抄出任何东西,造反派恼羞成怒,把大姨推到屋角:
你必须老实交代!
没有,就是没有!
两个年轻人一下子冲上去,一人一边拽住大姨的手臂,把它们反扣在背后,再用手按住她的后脑,用脚踢她的背;只听咕咚一下,大姨朝前跪了下去,眼镜被踢飞,头发全乱了。随后一声嚎叫:
再叫你回嘴!
我没有做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我是用生命加入共产党、参加革命的,我妹妹、弟弟都在为党工作。
你妹妹关进去了,她还想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
那你就告诉她:不能死,坚持活下去,死了就没人为你讲清楚了!
你还想让她讲清什么,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
造反派在阿喜的屋子里搜出一个首饰盒。他们放在大姨面前:
你不是交代说把你父亲全部财产都上交了吗?这是什么?你欺骗组织!
大姨诧异地看着那盒首饰。这是小外婆藏在女佣阿喜那里的。大姨解释不清,就这样当晚就被造反派带走关起来了。小舅舅被大学的红卫兵拖出来,也剃了阴阳头。
我为大姨和妈妈担忧。她们怎么就搞不明白?那是讲道理的年代吗?为什么就不能妥协一点?
不久,大姨被放出来了。可是,她老了很多,但只要有一点可能,她还是把自己打扮得清清爽爽、端端正正的。她对我说:我搞不懂,让群众斗群众,这是革命吗?
大姨夫突然去世了
1971年的夏天,大姨突然接到电厂的通知,说是大姨夫在吐血,已经送到电力医院了。大姨掉头就往医院赶,到了那里,医生把拍的片子举在大姨的眼前——胃癌晚期。
五个月后的一天,大姨要我把表妹带到医院,她对女儿说:
你害怕吗?去和爸爸说再见!
我不怕。
女儿上前拉起已经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的大姨夫:
爸爸,爸爸,我来看你了。
大姨夫一看到自己最心爱的女儿,突然又开始大喘起来。医生们立刻推着急救床,“哐当哐当”地冲进病房,大姨完全失控了,大声叫喊着:
不要再让他受难了!你们出去吧,让我一个人留下!
我们都退出去了,她顶住了病房的门,留给她最后的空间,单独和大姨夫在一起,她要亲自送走她最亲爱的人。我想象不出,大姨是怎么面对这最后的时刻的。当初,大姨和大姨夫在家关着门,偷偷放着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大姨夫搂着大姨的腰翩翩起舞。当我耳边还萦绕着那舞曲的旋律的时候,唱片突然被狠狠地砸碎了。华东电管局的领导来了,站在姨夫的尸体边上说:
苏铭適的案子没定性结案,作为党的叛徒和特务,不能给他开追悼会!
大姨夫的大出血就是他们给打的,但是没有人追究打手和陷害者。当时大姨夫已经得了胃癌,胃痛得咽不下饭。造反派用黑巾蒙住他的双眼,让他跪在食堂的长条板凳上:大姨夫忍着疼痛跪在上面,最后昏倒了,从条凳上翻倒在地上,造反派用他们穿着的工装大皮鞋去踢、去踩他:
不许你这个叛徒装死!
起来吃饭,你想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突然,大口大口的鲜血从大姨夫的嘴里喷射出来,他们这才感觉事情不对,把他送到医院的。大姨听说以后,伤心透了: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实话?他一直跟我说,在基层好,了解了不少生产中的实际情况。
周围天天有人死去,这些人近得让我随时都可以闻到他们身上的体味。可是突然就会有一天,不是他,就是她,消失了、死去了!我们常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最终已经不知道恐惧意味着什么。可是,每一次亲人死去的时候,我依然惧怕得无以言表。报纸、政府与领导们告诉我们说“我们的道路是前人没有走过的,难免会犯一些错误。跟伟大的前景比较,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共产主义是我们人类将要到达的最终目的地”。我越听越害怕,但我不敢说出口。
一开始,大姨挺着,你们不给开追悼会?我自己开!她很能干,立马去龙华火葬场租了一个小厅,把事情办妥。然后,自家举办的追悼会如期召开。我赶到那里的时候,大姨夫正躺在木板上,被殡仪馆的人缓缓地推出来。站在边上的大姨一滴眼泪都没有,只是默默地注视着他,像要把对大姨夫的所有记忆铭刻在眼睛里、心里。那是1971年的年末,大姨夫还没有来得及赶上他五十一岁的生日。
妈妈主持追悼会。小厅外面已经站满了自愿来参加追悼会的老同事、老同学、老战友,还有杨浦发电厂的老工人。很多人都戴着他们自己做的黑纱,静静地等在那里。妈妈大声地读着大姨写的悼词:
苏铭適同志,是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儿子……
冯秉麟阿姨——当年一起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那时正在受监督和审查——听到这句话,突然不顾一切地推开人群,冲进小厅,抱着大姨号啕大哭起来。冯阿姨一带头,外面站着的人一齐涌进追悼厅,挤得小厅水泄不通。那是1971年的寒冬。人们裹着寒冷,在大姨夫的遗体前久久不愿离去。
大姨夫和大姨的为人
回家后,大姨挺不住了,开始失眠,也不愿意见朋友,她把自己关在房里,只有妈妈可以进入她的房间。她重复地说着:
我就是想哭。
那就哭出来吧。
大姨在那里喘息着,但没有眼泪!
大姨夫的人缘是谁都没得比的,他技术高超、业务精湛,还有就是他的为人,一副绅士派头。他总是先替别人着想,再难的问题到他这里,他都是微笑着,轻轻地、不紧不慢地说着话。我实在是不明白,怎么有人要这么整他?大姨说:
是北京的那个张某,一口咬定看见苏铭適走出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还说出何年何月何日何时,像真的一样。除了她说自己看见,没有任何其他的证据。
张某是什么人?
她在解放前是上海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现在是国家科委副主任。
他们为什么那么恨大姨夫?为什么要整大姨夫?
她咬人就可以保自己啊!
可是,大姨夫这么好的人,她还咬得下去?
良心都泯灭了,还有为什么?她无所不为!
大姨的脾气和大姨夫截然相反,人缘就更不能比了。她打扮是有个性的,不愿意随潮流。最糟糕的是,大姨中饭不吃食堂菜,都是从家里带去,只买二两清汤面,也从不在午休时间和人聊天——她最讨厌的就是说三道四。似乎从大学时代起,她始终相信知识就是力量。一说到民族资本家、工商界的事情,她就很直接地表态:
政策反反复复,让人不能理解。现在都是外行来领导内行。
1957年反右,大姨被定为“严重右倾”,留党察看两年,下放劳动。工资也由十三级降为十五级,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才恢复了她原来的级别,但是多年扣发的工资,分文不补,大姨倒也不追究。
这样的个性,在我们的社会里,必然就成了“老运动员”。她总是不肯放弃自己的主见,不要行政级别,认定自己是工程师级别。大姨什么都可以放下,但是只有两件事情是永远放不下的:一个是党籍,还有就是对大姨夫的爱。在两年的留党察看期间,她把自己关在屋里写检查,大姨夫为了不打扰她,在门外走廊上背着手踱方步,只要我们发出一点吵闹声,他就把食指竖在嘴前,发出很轻的嘘声。她经常被罚到基层车间去劳动改造,开车床,制图纸。虽然她“派头”很大,可是基层的工人们居然都蛮喜欢她,说是:咯个人,有真本事嗷!
大姨夫为爱加入了共产党
在交大念书的时候,党组织交给大姨的第一个任务——教育、培养、发展苏铭適为党工作。大姨现在不愿意提这些事情了,如果不是她的原因,大姨夫是不会入党的,但是他太喜欢大姨了,所以只要大姨介绍他去交大地下党的活动,像读书会啊,学习《社会科学基础教程》《论政党》啊,他都会去参加。1943年,苏铭適正式入党,他和大姨一起加入了中共上海地下党控制的“中国技术协会”。那时候,他们都喜欢看好莱坞电影,还有中国的左翼影片。大姨弹钢琴,大姨夫就会坐在一旁,一边听着一边深情地看着她。
党组成员碰头,要讨论下一步计划及具体的实施,大姨就把外公家的客厅作为会议地点。她弹着钢琴,苏铭適和另外几个男的拉着小提琴。这是妈妈最开心的时刻,她跟在大姨身后,也要弹几首流行小曲。看到一群充满朝气的年轻人,外公也很高兴,说:
欢迎你们来阿拉窝里开音乐Party啊!
在楼上,外公欣赏着《小夜曲》《月光奏鸣曲》,全然不知自己在掩护地下党的活动。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大姨夫争取了大批技术工程人员留厂,没有跑去台湾。当时台湾的飞机来了,杨浦电厂被轰炸。又是大姨夫亲自领导着护厂、恢复供电工作、抢救设备。美国飞机连续轰炸,大姨夫整整一个星期没有回家。那时候也没有电话,听不到他的消息,大姨急得竟然跑到停尸间去找他的尸体。
“答谢”之路
1972年的一天,大姨重新走到镜子前,开始在镜子前烫她的头发。
大姨,你烫给谁看啊?
烫给你大姨夫看。我们要为他出门答谢,就要弄得体体面面的。
谢谁啊?
第一个谢的是汪家的人。汪德方,也是上海地下党的,“文革”前他是华东电管局党委书记。
为什么要谢他啊?
你大姨夫去世的时候,汪伯伯刚刚得了鼻癌,才从隔离室放回家治病。追悼会是让他大儿子东东去的。他自己生病,还在帮你大姨夫找药!
晓得了。
于是,我和大姨开始在不同的日子里,一家一家地去回谢!
汪伯伯住在延安路靠近江苏路上一栋小洋房里,汪伯伯的夫人薛阿姨一开门,看见我和大姨站在门口,一把拉住大姨的手就抽泣起来。大姨说:
不进去啦,谢谢侬,谢谢你们一家人啊!
小颐(大姨的小名),阿拉晓得铭適是被冤枉的。侬保重啊!
谢谢侬和老汪了!
说完这话,我和大姨就退出了小洋楼的大门,没想到汪伯伯跌跌撞撞赶下楼来,他们夫妇俩又一起紧紧地握着大姨的手说:
小颐,对不起,我让儿子给铭適送的药没能帮上他。
我看见大姨的眼泪马上就要出来了。她不断地掩饰着,硬拉着我的手说:
阿拉走了,你们多保重!
我转身看见汪家夫妇站在门洞里,向我们挥着手,直到我们转弯看不见为止。大姨一直是挺着腰板往前走,她不敢回头。如果不是大姨夫的死,我不会知道大姨有这么多朋友。在我的记忆中,他们不大和人有什么往来。大姨说:
阿拉上海地下党的人,跟瑞华(上海市委宿舍大院)的部队里的南下干部不同,我们一直是被人家压着的。开始我们都不知道,其实内部早就定下了,对我们这些地下党干部是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这是解放后对全国地下党员的政策。
大姨,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地下党的人?
大姨大口大口地喘息着,一时说不出话来,停顿了好一会儿,她说:
所以,我们互相也不是经常来往,干什么最后要被人淘汰呢?但是,我们之间有一种默契,只要一个眼神、一句问候,大家都会明白对方的意思。困难的时候,彼此都是会出来帮忙的。
友谊变得如此沉重,这里隐瞒着很深的秘密,而这秘密我至今也找不到根源。我看着大姨的脸,她没有表情,也许在思考自己为什么会走上这条道路,为什么拖累了大姨夫。我多么希望他们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多么希望他们的内心一直充满着快乐,多么希望我和大姨不要走在这样“答谢”的路上。没有想到,大姨又对我说:
你知道吗,解放前,我们接到的指示是什么?
不知道!
也是十六字方针。
怎么说的?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以待什么时机呢?
逐步淘汰!
说了这四个字,大姨发出轻声的冷笑。我紧紧抓住了她的胳膊。我是真的害怕,但是,我表述不出自己怕的是什么。
我和大姨走到淮海路“上海新村”去敲冯纯贞阿姨家的门,是他的弟弟(就是上海的话剧演员,他好像比冯阿姨小二十来岁,后来演《陈毅市长》里的陈毅,非常成功)开的门,他一见我们就对楼上大叫:
大阿姐,吴家大姐来了!
我们还站立在原地,准备打个招呼就走,没有想到,冯阿姨站在楼梯口上,中气十足地喊着:
让吴颐上来!阿拉不怕他们!
后来大姨告诉我:
侬冯阿姨啊,从来就是这样胆大泼辣的。她的继母,是冯阿姨自己介绍给父亲的,这个继母原来也是我们务本女中的同学。
她们这一代人,多么相像,不仅是那么开明,还是这么浪漫。
有时,大姨知道有些朋友不便在家“见”我们,于是敲开他们的家门,我和大姨就站在门口对他们说声“谢谢”。大姨转身离开的时候,我看见他们的眼眶里都含着泪水。
“文革”结束以后,闵阿姨对我说:
那是什么年代啊,我有时都不能原谅自己;和你大姨、大姨夫当了这么多年的朋友,在最恐怖、黑暗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并肩战斗,都挺过来了,却在“文革”的时候不敢和朋友来往。1970年,你大姨夫已经被冤枉、挨整了,有一天,他还和你大姨来看我,站在门口就为了跟我说两句话:我们都很好,你们好吗?坚持就是胜利。他们夫妇俩是站在昏暗的路灯下说的,说完就转身走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苏铭適……
我们是老派人,是心和心的约会
大姨的床头,永远挂着她和大姨夫结婚后的合影。他们都戴着眼镜,姨夫英俊的绅士派头,大姨文静高雅,真是天生绝配。这就是大姨一直会跟我说的话:我们是老派人,是心和心的约会。
从小,大姨就告诫我们:
一个女人在经济、个性上不独立,依赖男人,再聪明、再有本事都会失去尊严,没有自由和幸福可言。我跟你们说,绝不要靠任何男人来养活你,自己的自由是最可贵的。钱要靠自己去挣,要有独立谋生的能力,这样女人才会幸福!
可是,等到大姨夫去世以后,大姨却痛心地跟我说:
光是经济上的独立也是不够的,还要有精神上的独立,但这竟是如此艰难!
这是老派人的认识,到底是落后呢,还是新派?如今我回到国内,小报、杂志、网络上都在公然讨论如何嫁个有钱人;有些人还在交流做“小三”和“二奶”的经验。怎么会变成这样?我重新迷失在这个世界里。
(摘自《荒漠的旅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月版,定价:3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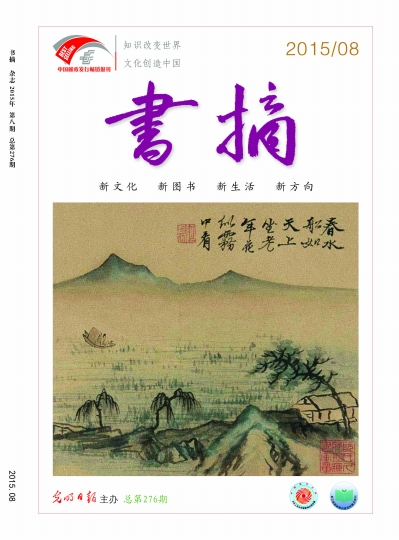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