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德国
柏林那道令人恐惧的墙没了,这早已经不是新闻,谁都知道的。有关柏林墙的这页历史和任何大事情一样,断然无情地被时间翻了过去。
我和徐去德国是2001年夏秋,大多数时间住在西南部,远离柏林,起初,也没有特别地想到去看柏林墙。提示了我的是一场小型演出,不是在剧场,选在一个半弧形的长廊里,在周末的晚上,演出带实验性,媒体记者们多,几乎和观众对半。剧情大致是两对男女纠葛在一起的感情冲突。语言不通,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我能够看得懂的部分,是由一部幻灯机打在长廊最深处墙壁上的影像,它始终作为全剧的贯穿背景,不断地重复着柏林墙的倒塌:狂喜的人爬上了勃兰登堡门,人的身体,拳头,大铁锤,撬棍,起重机,七零八落的履带和墙上涂鸦。整场演出,只有这个我懂。
我很想去看看那曾经惊心动魄的柏林墙。
柏林
在旅游局取了中文柏林地图,搜索这个大城市可以看的地方,马上看到“查理检查站展览馆”,地图上有文字注明:以柏林墙为展出主题:某区某街某号,每天九点到二十二点开放。很快决定搭地铁去看“墙”的展览馆。
查理检查站展览馆分两个部分,室内和室外。
室外部分,是设在街心的原柏林墙查理检查站,在道路中间平地而起的一座只有几平方米的简易建筑,现在看像间玩具屋似的,但是,这“玩具屋”前堆了接近一人高的沙袋。正对着检查站,立有一个高大的标牌,两侧各有一个巨幅的全副武装的军人半身照片,胸前佩戴各式功勋章,一侧是苏联军人,背对着苏联人的是美国军人。他们比真人大几倍,两个绝对端庄严肃的军人在半空里,各自面向着东西柏林,象征着他们曾经的职责。跟随着“墙”,从1961年9月22日起,这里是东西方“冷战”的最前沿,剑拔弩张之地。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自1945年后德国的强大占领者,在检查站两侧部署坦克士兵,荷枪实弹日夜对峙。
曾经在西柏林一侧,有美军设立的警示牌:“你已离开了美国管辖区”。
查理检查站哨所在同样跟着“墙”的倒塌,在1990年6月22日被完全摧毁,十年后,2000年8月13日它重建。据说新建的哨所完全保持原貌,包括涂成白色的小屋中所有摆设,包括其中的卫生用品和电源管线的埋设。
这间孤立于街心的著名检查站,引来很多游人,想和它合影,可要耐心等待。
展览馆的另一部分,是临街的三层小楼。有德国青年学生这么形容它:“在废墟中,一个协会办了个小小的博物馆,回忆成功的和失败的越墙逃亡行动,那是一个阴沉的地方,一个混合着各式各样的啤酒瓶盖、发黄的报纸碎片和上面刊载着悲剧的大杂烩。”
这是一家私人机构,像进入一个普通德国人的家,每个展室空间都不大,比起重视展览馆文化的德国其他众多展览机构,它狭小局促,但是,每个进入者都会惊叹,这里集中了多么沉重而不同一般的“大杂烩”。
柏林墙,我原以为我对它够了解,老远跑来看展览,不过是重温,不过是来柏林的一路上惊讶于东西德原来存在这么大差异的一次印证。仔细看了“墙”,才重新理解了,人们对一个历史事件的了解局限是绝对的,那大大小小的苦难和幸福,连亲历者都没可能完全体会,何况旁观者,何况柏林墙这样重大的事件。看“墙”,想到小时候记住的一句列宁的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柏林墙
柏林墙,早期只是铁丝网,后来逐渐改造,最终成为那道高四米满身涂鸦的水泥板,又荒诞地由最恐惧最不可逾越的“铁幕”,一夜之间被砸碎,成了引人收藏的艺术品。从结果到结果,这之间的过程在今天看来似乎并不复杂。而跟着“墙”发生的故事每一件都惊心动魄。
离开查理检查站展览馆,我们沿着被保留下来的一小段柏林墙走,它已经不能随意接近,有约两米高的铁网隔离开行人,无名艺术家的涂鸦都在那些兴奋过度的日子里被“自由向往”的冲动破坏,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被敲凿得千疮百孔的水泥拼板,有些地方已经凿穿,暴露出弯曲的钢筋。印象最深的一处,凿出一个人形,正好够一个成年人来来回回不断地穿越。徐总想最接近那堵墙,他想试试它有多高。我说四米,他还是不甘心,总想试试这堵墙所代表的四米有多高。
一些旅游车路过,却不停车,只是缓缓减速慢行,让游客草草看一眼它。
柏林墙倒了
看过了“墙”再去看柏林,总感到它是支离破碎的。墙没了,空旷地带当时都还在,东半个城区有个别建筑还裸露着断壁,有人把墙消失以后出现的空地称作“欧洲最大的工地”。坐车出勃兰登堡门向东走,经过一站一立的马克思恩格斯二人像,那是中国游客最爱照相的地方,再向东,越走越寂静萧条,有许多中国人熟悉的苏联式水泥板楼。
在德国,有人形容移民问题说:当初,我们要的是劳动者,但是“人”来了。
上世纪40年代后期,战争使德国国内男人数目骤减,当时允许土耳其人入境,他们担任了最繁重肮脏的劳动,没想到他们来了就不再回去,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就在这种时候,“墙”一夜间倒了,一千六百多万东德人可以自由出入封闭了四十四年的界限,虽然都是日耳曼民族,但是这是完全不对等的融合,工作职位社会福利都是有限的。曾经,一个冒死逃亡者落地西柏林,他受到的是英雄式的拥抱欢呼,这些镜头现在还在“墙”的展览馆里,现在看了仍旧激动人心,但是现实已经变了。摆在德国人面前的是紧跟着自由蜂拥而来的东德人,事情不是合二而一那么简单。
从墙的倒塌起,再没有什么东西让所有德国人耿耿于怀,同仇敌忾,四十四年中形成的差异很难在短时间里变成同心同德。有一个外国人说:这儿不再东西对峙,却依然南辕北辙,它是个搞不到一起的历史半成品。
1999年,德国公布的官方数字是:柏林墙倒塌后的十年间对于原东德地区的拨款,每年一百亿马克用于公路,一百亿马克用于铁路,一百亿用于电话网络。这十年里,东德地区的私营企业家由起初的一万名增加到五十万名,汽车由三百九十万辆增加到七百万辆,电话由一百八十万部增加到八百万部。巨额开支使原西德人要付出更多的税款。仅仅1998这一年,柏林市的文化预算就是十亿美元,即使这样投入,在柏林街头仍旧感觉它还有太多的事情没做,千疮百孔的地方随处可见。何况有些东西即使是钱也难以改变。
离开柏林后,经过德累斯顿回德国西南部,它的中心火车站广场成了一片工地,正在拆除列宁纪念碑,易北河边发黑的古老宫殿都在等待维修。而莱比锡火车站附近的建筑让人想起中国1967年“文革”武斗过后的狼藉。
东西两边的一部分人,沿袭着惯性,继续吸着不同的香烟,喝不同的酒,看不同的电视节目,读不同的报纸,有人渐渐感觉那座四米高的“墙”还无形地隐隐存在。这哪里是当初彻夜欣喜狂奔的人们可以预料的。
柏林墙倒得太仓促,来不及销毁的东德安全部门卷宗遗落世间,有人形容这些曾经绝密的资料,暴露了人在专政制度下的屈辱、低贱、胆怯和卑微。谁会乐于和多年来潜在暗处对自己的生活窥视告密的人待在一起?直接死于墙的人数以百计,而多年里受到“墙”的荫蔽恩惠者却以几十万,甚至百万计,这些人的突然暴露显现,又难免不带来更深更长久的内心嫉恨与咄咄不安。
离开
在德国最南端进入阿尔卑斯山区的小城菲森,是去新天鹅堡的路上,我们坐一个老人赶的旅游马车,他的毡帽上别满了各种各样列宁或者镰刀斧头或者红旗的纪念章,高头大马转弯时听到他用俄语夸他的马说:好!
是俄语,在上世纪60年代最后一年,我上了中学,第一天就知道要学俄语了,很快学了几个词:同志,无产阶级,毛主席万岁,缴枪不杀,还有“好”。所以,多年之后,在德国,听懂了马车夫的俄语。而在科隆大教堂前,两个正表演缓慢协奏曲的艺人看到我和徐向他面前的小盒子里放了几马克,其中那拉手风琴的年轻人突然快速又极热情地转向我们,几乎是跳跃着奏起了《喀秋莎》,围观的人们也随着节奏鼓掌,难道东方面孔就一定喜爱前苏联的歌曲?
临离开德国前,在南部城市奥格斯堡遇到了一场雨,避雨时,看见一家花花绿绿的儿童玩具店隔壁是一间主题酒吧,门口张贴着大幅的切·格瓦拉,那张看了无数遍的红黑相间头像。
有个德国朋友说:切,你们知道他吗,他在德国很红啊!
我说:知道,在中国,他也很红。
德国人有点惊奇地看我们。
切·格瓦拉,这个被塑造成为游击而生的家伙,第一次知道他,是看了一本传记,时间1975年,当时的格瓦拉传记以内部参考的形式出版,书在扉页后附一照片:穿制服和穿便装的人们围着他的尸体在担架上,指指点点,格瓦拉赤裸上身,眼睛半睁。而就在柏林墙最后筑成的前一年1960年的10月到11月,两个月的时间,他率领古巴经济代表团访问了中国、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朝鲜,民主德国就是曾经的东德。这陈年旧事恐怕五个被访国的新一代们都不太知道也不关心了,被各种新媒介和大众消费的切·格瓦拉是另外一个了。
柏林墙倒了,当初筑它的人或者只是简单地想到强行阻断,谁会想到一堵墙的起落涉及的问题会多复杂。造墙用时一夜,拆墙用时一夜,而由“墙”带来的“墙思维”“墙空虚”“墙依恋”久久不散。
(摘自《看看这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4月版,定价:3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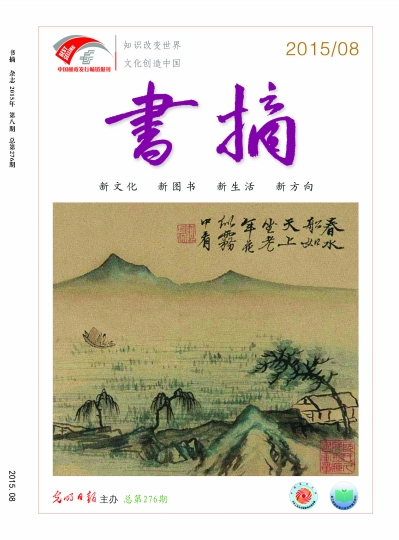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