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益商业化功利化的环境中保留一份学术的尊严。不为某些时尚的标准或实利化的风气所左右,能够沉下心来做学问,与拜金主义保持必要的距离,这就是一种学者的定力。
•现在中文系文学教育用心最多的就是文学研究,学会如何分析处理问题以及如何写出像样的规范的文章。但“文学”的味道似乎越来越淡了。学生刚上大学可能还挺有灵气,学了几年后,悟性与感受力反而差了。
•现在全国大多数中文系都“翻牌”叫“某某学院”,北京大学中文系,至今没“翻牌”,因为我们很看重“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个名字连在一起的“文脉”。
•“守正创新”,我想还是靠“老本钱”,在“守正”上下了些工夫,所谓创新仍然是要有“守正”作为基础的。
◎温儒敏,北京大学教授,原北大中文系主任。
●张晓玥,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讲师。
安静的八十年代
●您作为新时期首届硕士研究生,是这段历史的重要参与者。能否说说您年轻时的读书生活?
◎我读大学本科二年级时就碰上“文革”,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但当时“停课闹革命”,还是有“逍遥派”的缝隙。“文革”毁灭文化,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个人阅读思考的空间。你们可能不知道,“文革”时期系统整理出版了“二十四史”,还有许多西方现代作品都组织同步翻译,说是内部发行,可是发行量也在五六万册以上。像《麦田的守望者》、《多雪的冬天》、《第三帝国的兴亡》、《拿破仑传》、《西方哲学史》,等等,那时我都想办法找来读过了。和那种目的性非常强的“职业性阅读”比起来,当初这种“漫羡而无所归心”的“杂览”,似乎更能积淀下来,形成自己的思维与写作的能力。这种习惯延续到后来读研究生。现在我指导研究生,也主张有些“杂览”。一上来就直奔主题,想着如何考试,如何完成论文,或者就是顺着导师的路子走,关注面太窄,是不利于积累后劲的。
我们这一代如果说有“优势”,那就是人生历练多一些,与学问联系比较紧密,不是两张皮。我大学毕业后曾经在中共广东韶关地委机关工作过八年,大多数时间都下乡下厂,当过“生产队长”,耙田、插秧什么活儿都干过,对“国情”和“民情”是有切身体验的。这种切身体验是别人代替不了,书本也难以提供的,对自己做学问肯定有影响。如果有过较多的人生阅历,特别是基层的生活经验,就可能会“调和”一点,有时会反躬自问,怀疑自己的角色定位可能遮蔽什么,思索自己的学问是否脱离实际。我觉得人文学者最好还是有些社会实践经历。我知道自己的局限,外语水平不够,传统之学的底子不厚,和新一代学者比,又可能方法比较单一,眼界不够开展,等等。我自知不可能在学问上成就大手笔,不过顺着自己的路子来做,尽量做好就是了。
●能说说你们当时是怎样进入学术之门的吗?
◎我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正赶上80年代的思想解放,各种思潮汹涌,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但作为研究生学习,我们是比较扎实的,也比较静心,外界没有很多干扰,是一生非常难得的一心问学的好时光。那时课不多,不用攒学分,不用考虑什么核心期刊发表文章,主要就是自己看书,寻找各自的兴趣点与可能的发展方向。那时也较少考虑毕业后找什么样的工作,起码不像现在那么焦虑,不会刚入学就打赚钱的算盘。这种自由宽松的空气,很适合个性化的学习。老师也没有指定书目,现代文学三十年,大部分作家代表作以及相关评论,都要广泛涉猎。我被推为研究生班的班长,可以直接进入书库,一借就是几十本,有时库本也可以拿出来,大家轮着看。研究生阶段我们的读书量非常大,我采取浏览与精读结合,起码看过一千多种书。许多书只是过过眼,有个大致了解,主轴就是感受文学史氛围。看来所谓打基础,读书没有足够的量是不行的。书读得多了,旧期刊翻阅多了,历史感和分寸感就逐步形成了。
读书报告制度那时就有了,不过我们更多的是“小班讲习”,每位同学隔一段时间就要准备一次专题读书报告,拿到班上“开讲”。大家围绕所讲内容展开讨论,然后王瑶、严家炎等老师评讲总结。老师看重的是有没有问题意识以及材料是否足以支持论点,等等。如果是比较有见地的论点,就可能得到老师的鼓励与指引,形成论文。这种“集体会诊”办法,教会我们如何寻找课题,写好文章,并逐步发现自己,确定治学的理路。记得当时钱理群讲过周作人、胡风和路翎,赵园讲过俄罗斯文学与中国,我讲过郁达夫与老舍,等等。
导师的影响很大。我们的导师王瑶先生的指导表面上很随性自由,其实是讲究因材施教的。我读研究生第一年想找到一个切入点,就注意到郁达夫。那时这些领域研究刚刚起步,一切都要从头摸起,我查阅大量资料,把郁达夫所有作品都找来看,居然编写了一本二十多万字的《郁达夫年谱》。这在当时是第一部郁达夫年谱。研究郁达夫这个作家,以点带面,也就熟悉了许多现代文学的史实。王先生对我这种注重第一手材料、注重文学史现象以及以点带面的治学方式,是肯定的。
新中国建立以来,各种政治运动不断,“土改”呀、“四清”呀、“文革”呀,等等,大学很少能完整学习的,到现在,自由度大了,可是物欲膨胀,竞争加剧,干扰也不比以前少。倒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能够比较静心学习的难得的时期,我们幸运赶上了。应当说研究生三年,加上后来做博士论文几年,是很专心问学的,为我后来的学术发展打下比较好的基础。
提出警惕“汉学心态”
●您曾提出要警惕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在学界反响较大,也有一些争论。您能否就这个问题再发表一些看法?
◎我的主要观点都在《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那篇文章中表述了。后来有些反响,也有不同的意见。首先我不是针对海外汉学来说的,我一直认为汉学很重要,汉学家一般都做得深入专注,往往“穷尽”某一课题。汉学家的研究主要是面向西方读者的,这是他们共同的特点,也就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而以西方为拟想读者的汉学,也可以作为我们观察研究本土文化的“他者”,是可供本土学科发展借鉴的重要的学术资源。但借鉴不是套用,对汉学盲目崇拜,甚至要当作本土的学术标准或者摹本,这种心态并不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我提出警惕所谓“汉学心态”,它主要表现在盲目的“跟风”方面。这些年来,有些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和评论家,甚至包括某些颇有名气的学者,对汉学、特别是美国汉学有些过分崇拜,他们对汉学的“跟进”,已经不是一般的借鉴,而是把汉学作为追赶的学术标准,形成了一种乐此不疲的风尚。所以说,这是一种“心态”。人文学科包括文学研究其中民族性、个别性、差异性的东西可能很重要,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把西方汉学成果拿来就用,甚至就以此为标准,问题就出现了。许多“仿汉学”的文章,看上去很新鲜、别致,再琢磨则有共同的一个毛病,就是“隔”,缺少分寸感,缺少对历史的同情之理解。而可笑的是有些“仿汉学”的文章并不掩饰其“仿”,连语气格调都很像是翻译过来的,可以称之为“仿译体”。所谓“汉学心态”,不一定说它就是崇洋媚外,但起码没有过滤与选择,是一种盲目的“逐新”。我主要是针对学风而言,带有学术反思的意思。有些学者没有领会我的本意,以为我是搞闭关锁国,排斥外来的东西,这就把我的观点拧了。我主张尊重汉学,引进汉学,研究汉学,只是不宜把汉学当成本土的学术标准。现在有所谓“汉学心态”,其实是缺乏学术自信的表现。
●那么,您认为现代文学研究有哪些今天特别值得珍视的经验与传统?
◎你这个题目很大。我只想特别提到,现代文学这个学科有两个特点很突出,一是和现实结合紧密,二是和教学结合也紧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革命“修史”,现代文学自然受到重视,地位很高。80年代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现代文学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几乎成为“显学”。好处是每一阶段都受到格外重视,集合了一批实力强的学者,对社会影响也大。这形成了现代文学研究富于现实感的特色。当然,过去这门学科和政治关联太过密切,甚至受政治的过分支配,丧失了学术的自主性,给学科发展造成很大伤害。直到80年代之后,才逐步恢复了学术自主及规范。另外一个传统是和教学的结合。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奠定了学科基础,这本书就是教材,是教学的产物。但是这些年来我们对于现代文学教学的关注是很少的。每年召开各种类型的学术会议很多,关注教学的能有几次?这也无奈。现在几乎多数学校都奔着“研究型”方向发展,老师晋升和考评都主要看发表文章,很少有精力放在教学上了。这是很大的问题。
现有的学术生产体制,很不利于做学问,对于人文学科伤害更大。学术泡沫的出现跟学术生产体制是有关的。现在常见的评什么博士点呀、重点学科呀、基地呀,还有这个奖那个奖的,也许初衷是为了促进学术竞争与发展,教育和科研的规模大了,有些量化也是一种必要的管理手段。问题是如果一刀切,用理科的规范来约束文科,学术评价全都主要看量化指标,就一定出偏差。这种状况短时期是难以好转的。我们要正视这种情况,就当成是一种我们还难以摆脱的生存环境,要与之共存,而又尽量减少精神上受其困扰,也许这样才能在日益商业化功利化的环境中保留一份学术的尊严。不为某些时尚的标准或实利化的风气所左右,能够沉下心来做学问,与拜金主义保持必要的距离,这就是一种学者的定力。当然,对于学术量化要求,年轻学者不可能不面对,我们有些无奈,必须应对,只是千万不要形成习惯,以为这就是学术之正道了。最好能保持一点平衡,给自己留一点“自留地”,也就是真正自己喜欢做的,能作为“志业”来追求的那些研究。在这个浮躁的年代,谁能潜心学问,只要方法对路,多年后可能就有结实的成果出来,终究会得到社会的欢迎的。
中文系文学的味道越来越淡
●您大概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在不止一篇文章中提到要重视文学研究的本义,重视文学教育和审美教育,并对文学研究远离审美表示焦虑。
◎现在文学研究不太注重文学自身,存在以思想史、文化史研究取替文学研究的趋向,所以我提出要重视文学研究的本义。那么本义是什么?可能有不同的解析。我认为审美的研究是比较核心的,创作的个性、独特性,也是文学研究所要重点关注的。文学创造是非常个人化的,是独特的想象力和语言创造力造就了各式各样的艺术世界,所以文学研究特别是作家作品研究,在许多情况下都必须发现艺术个性,也必须以经验性审美性的分析为前提,而不能停留于大的思想背景的考察或所谓时代精神同一性的阐析。
更大的问题是影响到教学。学生读了几年中文系,知道一些文学史知识,也学会用一些理论套式分析文学,但没有文学的感悟力,甚至没有文学的爱好。现在中文系文学教育用心最多的就是文学研究,学会如何分析处理问题以及如何写出像样的规范的文章。但“文学”的味道似乎越来越淡了。概论、文学史和各种理论展示的课程太多,作家作品与专书选读太少,结果呢,学生刚上大学可能还挺有灵气,学了几年后,理论条条有了,文章也会操作了,但悟性与感受力反而差了。结果“文学”不见了,“文化”又不到位,未能真正进入研究的境界。所以我担心现在的文学教育不能改变文学审美失落的趋向。
●那么,您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多年,您有何秘诀?
◎谈不上有什么“秘诀”,北京大学中文系自有其“系格”,是比较人和,也比较正气的系,这是传统,尽量保持就是正道。学术单位最重要的是人才,而真正能吸引人才、并且让大家安心做学问的,是自由思想的空气。我当系主任想方设法就是营造自由。现在学术管理对我们也有许多要求,但我们不会管得太死。我们比较看重的是“代表作”,是真本事,是学术生长的潜力。当然,系里也有少数学问不那么出色,或者不怎么出活儿的,你总不能为了限制这些少数人,而特别制定一个死板的条例,把整个气氛都搞得紧张吧。那就不值得了。现在全国大多数中文系都“翻牌”叫“某某学院”,当然也可能是发展的需要。按说以北京大学中文系现有的规模,也不是一个小学院的格局了,至今没“翻牌”,因为我们很看重“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个名字连在一起的“文脉”。我们讲文脉,讲传统,不是摆先前阔,而是要让文脉来滋养我们当前的教学研究,我提出了“守正创新”。我想还是靠“老本钱”,在“守正”上下了些工夫,所谓创新仍然是要有“守正”作为基础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有自己的传统和良好风气,相信今后一定还能再接再厉,守正创新,冠冕芳林。
(摘自《当代中国学人访谈录·文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10月版,定价:6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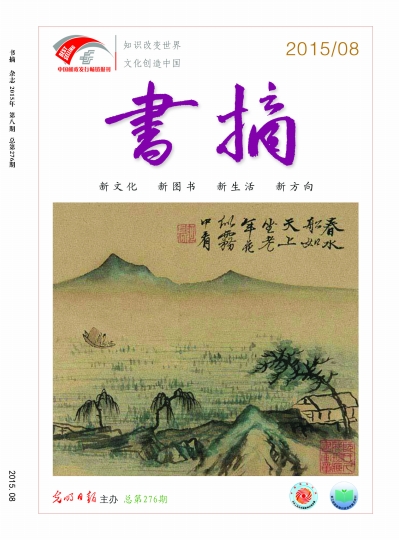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