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台湾诗人周梦蝶病逝。回上海前,我去了他的灵堂祭拜,那日正好头七。见门外写着“周梦蝶居士”,我心头一颤,堂内静谧安详。灵堂的角落里,放着一些他平日的起居用品,有脸盆、雨伞、鞋,和几件他见客时会穿的衣服,那便是一个老诗人清清白白的一生。
这是我到台湾的第四年。周老是我四年前就认识的前辈,那时我懵懵懂懂,随老师前往周老寓所访问,甚至连访问都算不上,就只是随行。我在台湾当学生的日子里,受长辈恩惠良多。却没想到,四年后还会站在这片土地之上,多少累积了一些世故人情。更没想到,会有幸目送他走,以这样的方式。看似毫无遗憾,其实心下惶惑得很。几度哽咽,也确切说不上是因为认识的人走了感到不舍,还是因为人间留下了我这样吊儿郎当的过客继续赖活而感到惭愧。我脑海中涌现他诗中所写的句子:
谁是心里藏着镜子的人呢?谁肯赤脚踏过他的一生呢?
一个月前,我帮沪上一家刊物约了周老的访问。我无知无畏,虽然知道今年他身体状况一直不稳,但谁想那会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个月。我以为一切如常,我可以在发稿之后寄几本杂志给他,没想到一别永别。那也可能是老人生前接受的最后一个访问。
回上海之后,我拿到了那期杂志,出刊时平淡得就如我迫于生活造次所亲采或约采的任何一则作家访问一样,若没有网站强势力推,不会引起任何注意。那一期访稿的按语是我写的:“周公于五月一日下午二时四十八分因肺炎并发败血症,于新北市新店慈济医院化蝶永远离开,享寿94岁,消息传出,台湾文坛悲痛不已。马英九在龙应台陪同下,亲自到已逝诗人周梦蝶灵前上香。痖弦先生当日忽然来电,原想帮忙询问周公是否愿接受美国中华人文砖基金会召集人王哓兰的访问,听到噩耗说,‘现在的加拿大是凌辰四点多,我今晚就是睡不稳。我去年底去见梦蝶时,我莫名其妙地想哭,这或许是前兆,他真的走了!’我们的采访在周公过世前一周,当日他精神出奇好,说了许多话,拍照也有神采。没想到采访未刊,一别永别。”刊载时碍于篇幅被砍去大半,这就是我的哀愁和现实人生之间的扞格。而我也不得不渐渐将之视若寻常。
开始是兼差,后来是迫于学费压力,我曾在台北兼任过许多报社的文化记者。这并不是我所喜欢的身份,蜻蜓点水似的相逢,带有强烈目的的闲聊,令生活与文学都尽失本来面目。然而人活着不能总为了顺心,我还是本本分分做了不短的时日,这些时间在我二十岁到三十岁的生命旅程中,日渐占有了巍峨的体积。
而周公离世,无疑是对我私人生活一个不小的打击,我好像忽然意识到了什么,想要终止一些什么,又不便言明。
五月在上海,我得知外婆得了胰腺癌,这个突然的消息令我这样一个奔跑于两岸并以此为乐的浅薄人,多少有了人之为人最古典的为难。如今我每天再焦头烂额,还是会依例查一下胰腺癌的护理讯息。我大概还是始终没相信外婆其实即将要走这件事。她自己是医生,很冷静地告诉我她生命最多只有一年,或者几个月,开刀最多两年,但要插六根管,她觉得自己挺不住。
去年冬天我从台北买了羽绒服给她。要知道在热带卖羽绒服可真是一个孤独的职业,我承认自己有一点陶醉于店员不吝夸赞我尊亲友孝的幻觉里,我还不知道这一次虚华的体会在我生命中的意义有多沉重。上个月我最后一次见到外婆,她正蜷在肿瘤医院的病房里,人已经瘦得脱形,她对我说,入院前她把所有的衣服都洗了,就这件没有,因为它还很新,她开春的时候,用干净的布擦了一下,只是不知道能不能穿到明年冬天了。她说这话的时候带着抱歉的笑,我从未见过她那么抱歉,从未见过她这样笑。
其实过了三月,羽绒服都打七折了,但我当时就是直觉老人不能等,没有那么多三年五载,但还是带有一些些一掷千金的虚荣感,我总觉得自己的情感远不如老人对我来得纯粹。我很怕老人问我还有多少时间毕业,在她得病以后,也不再问我。三年五载对年轻人来说弹指一挥,对老人,则是千万重远山。
如今我在微信给外婆发的讯息,她都会趁着有力气的时候回我。去年此时我就听出她似乎有气无力,和刚学会智能手机时候的兴奋不太一样。我提醒母亲记得问问她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于是大半年的时间里,她住院检查,暴瘦,也没查出所以然。此次我去看她时,多问了几句,如果去年就查出来会怎么样,她说也不会怎么样,照样是化疗或者开刀。原话是胰腺就是“顶顶讨厌”。上海话说“顶顶讨厌”就有点娇嗔的意思,这是我第一次听着觉得这个词居然有点凶险。她说,不信你自己可以查的呀,网上都有。
她还曾说在我毕业时要来台湾玩,未来大约也不会再提及。我略微有一些体会到蒋晓云在小说里写“爱人在不在比爱不爱重要多了”的感受。现在大概也是的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甚至有点想,夏天快点来,我要早一点回家看看她,握握她的手。还在心里有一点守望,最好还有下一个夏天。
我对外婆最深的印象,是十几年前,家里还有一个老太太。外婆常常说她坏话,就像我说很多亲人坏话一样,一开口就是三天三夜的气势,但该要料理的事情一件都不差。后来老太太走了,我才知道,那是她继母。她一点也不喜欢她,却养了她很多年。长辈们都死光了呀,只剩下她和她在一起。她送她走时,很难说没有难过,也很难说真的是难过,我觉得,人生的滋味就是这样的。
如今我有些明白,死亡是一个必须从个人层次因应的现象——唯有如此才会对死亡有所感觉。到台湾以来,我曾经好多次看到好友在脸书上写,祖父母过世而自己不在身边的遗憾。
如今回想起那些人、那些文字,我只记得自己曾犹豫过一分半秒是不是适合给他们按一个“赞”,还是书写一些隔靴搔痒的浅薄安慰。这令我感到痛心、愧赧,我居然是这样一个漠然的人。
王安忆曾回忆母亲过世时,自己冷冷面对外人的关心,无法显示出象征礼貌的感恩。一直到,朋友在电话里说,我父亲也走了,她才忽然柔软下来。就好像,那个隔海的人忽然看起来是懂她的。人心是多么细密又脆弱,唯有在这样的时候,才不惜曝露自己。
如今,我常常面对这种告别,并以不断增添告别的次数。远近八百里,行行重行行。我在大学的老师有一次在放课后对我说:“怡微啊,不要以为自己很年轻啊,一眨眼六十年就过去了。”我当然知道,一眨眼,我恐怕会与所有深爱的人,再没有更具体的照面。
(摘自《因为梦见你离开》,山东画报出版社2015年1月版,定价: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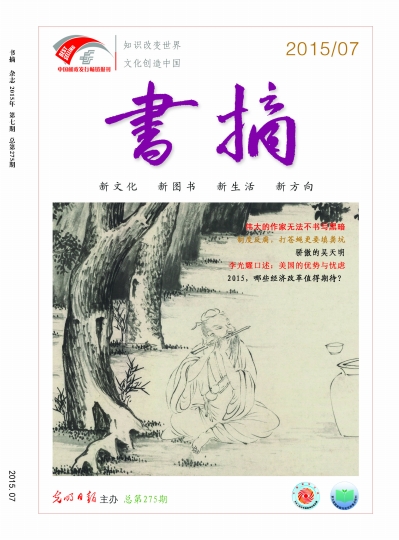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