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勃罗·聂鲁达,周游世界,足迹遍布亚洲、欧洲、美洲。197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是聂鲁达晚年撰写的回忆录,本文选摘其中关于中国之旅的描述。作者用真诚而自然的语言,娓娓道来,再现了那个并不太遥远的年代。
初访中国
我两次访问中国。第一次是在一九五一年,这一年碰巧由我和别人一起,承担把列宁和平奖授予宋庆龄女士——孙逸仙的遗孀——的使命。她获得那枚金质奖章是中国当时的副总理兼作家郭沫若提议的。
和我同行的爱伦堡也是国际评委会的成员,他是苏联人,一位非常有名的战地记者。我们乘坐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前往中国。踏进这趟传奇式的列车,就像登上一艘在大海上驶往无边而神秘空间的轮船。从车窗望去,我周围遍地都是金黄色的。在西伯利亚的仲秋季节,举目所见全是布满花瓣似的黄叶的银色白桦树;继而是无边无际的大草原、冻原或者西伯利亚针叶林带。不时出现新城市的车站。我同爱伦堡下车去舒展一下麻木的肢体。车站上,农民们带着包袱和手提箱,挤在候车室里等火车。
我们几乎来不及到这些小城去走走。这些城市都很相似,都有一尊斯大林的水泥塑像,塑像有些涂成银色,有些涂成金色,几十尊塑像都像是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
我觉得,火车日复一日在金黄色旷野上前进得非常缓慢,白桦树一棵连着一棵。终于,我们在伊尔库茨克下火车,乘飞机前往蒙古,再从蒙古转机到达中国。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笑的人。他们笑着经历过无情的殖民主义,经历过革命、饥饿和屠杀,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他们更懂得笑。中国孩子的笑是这个人口大国收获的最美的稻谷。
不过,中国人的笑有两种。一种是麦色的脸上自然灿烂的笑:这是农民和广大人民的笑。另一种是瞬息万变的虚伪的笑,可以在鼻子底下随时贴上,也可以随时撕下。这是官员们的笑。
第一次到达北京机场时,我们费了不少心思来辨别这两种笑。真诚美好的笑陪伴了我们许多日子。这是我们的中国作家朋友们的笑,他们是给予我们尊贵款待的小说家们和诗人们。就这样,我们认识了作家协会副主席、斯大林奖获得者,小说家丁玲,还有茅盾,萧三以及老共产党员和中国诗人中的佼佼者——令人心醉的艾青。他们会说法语或英语。
第二天,列宁奖(当时称为斯大林奖)授予仪式结束之后,我们在苏联大使馆吃饭。出席宴会的除获奖人之外,有周恩来、年迈的朱德元帅以及其他几个人。大使是个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英雄,典型的苏联军人,一而再地唱歌、敬酒。我被安排坐在宋庆龄女士旁边,她很高贵,也依然很美,是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女性。
我们每人都有一个装满伏特加酒的玻璃瓶,供自斟自饮。频频听到“干杯”的声音;这种中国式的敬酒迫使你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一滴不剩。年迈的朱德元帅坐在我对面,频频把他的酒杯斟满,大声笑着,不停地招引我干杯。
在一年的那个季节,中国人都穿蓝衣服,一种不分男女的蓝工作服,使他们具有统一的天蓝色外观。没有破衣烂衫;但是也没有小汽车。四面八方聚拢来的密集人群,挤满了所有的空间。
那是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年,各地肯定都遭遇了物质匮乏和困难,然而在北京城走马观花时却看不到这些情况。特别使我烦恼的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我们要买一双袜子、一块手帕,都会变成国家大事。中国同志为此进行了讨论。经过紧张商量之后,我们浩浩荡荡地从酒店出发了:打头的是我们坐的车,后面是保卫人员、警察、翻译坐的车。车队飞快启动,在永远拥挤的人群中间开路前进。我们在众人让开的一条狭窄通道中一阵风似地开过去。一到百货公司,中国朋友急忙下车,把店里的顾客飞快赶走,阻断交通,用他们的身躯构成路障,爱伦堡和我低着头从一条由人拦出的通道穿过,并在十五分钟之后同样低着头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小包,同时十分坚决地决定,绝不再出来买袜子了。
诸如此类的事情弄得爱伦堡恼火。酒店里给我们上的是中国从殖民者那里学来的糟糕透顶的英国菜。我是个中国烹饪的热烈崇拜者,便对我的年轻译员说,我极想享受一下驰名的北京烹饪艺术。他回答说他要去商量一下。
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商量过,而事实是,我们还得咀嚼酒店里那种难以下咽的烤牛肉。我又对他说了这件事。他沉默片刻才对我说:
“同志们已经开了几次会了解情况。这个问题马上就能解决了。”
第二天接待组的一位要员来看我们。他摆出一副彬彬有礼的笑容之后,问我们是否真的爱吃中国菜。爱伦堡断然对他说爱吃,我补充说,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知道广东菜了,我渴望品尝名闻遐迩的北京佳肴。
“这件事有困难。”这位中国朋友忧心忡忡地说。
他摇摇头沉默了,然后下结论道:“几乎不可能。”
爱伦堡笑了,是顽固的怀疑论者那种苦笑。我却大为光火。
“同志,”我对他说,“请替我准备好回巴黎的证件。既然我不能在中国吃到中国菜,我就到拉丁区去吃,那里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我的生硬言辞起了作用。四小时后,我们在一大群随行人员的引导下,来到一家著名餐馆,这里烹制烤鸭已有五百年历史。那是一道令人难忘的美味佳肴。
这家餐馆日夜营业,距我们下榻的酒店不足三百米。
再访中国
五年之后,开完科伦坡和平大会,我又一次造访中国。这次是和小说家若热·亚马多及其妻子泽莉亚一起。
这次首先到达的第一座中国城市是昆明,我的老朋友,诗人艾青,已在那里迎候我们。他黝黑的宽脸膛,他流露狡黠和善良的大眼睛,他敏捷的才思,又一次预示这次漫长的旅途将是愉快的。
艾青和胡志明一样,是在东方殖民压迫下和巴黎艰苦生活中造就的出身古老东方的诗人。这些声音柔和、自然的诗人一旦从监狱出来,就出国成为穷学生和餐馆侍者。他们对革命充满信心。在诗中柔情似水、政治上却坚韧如钢的他们都及时回国以完成自己的使命。
昆明公园里的树木都动过整形手术。形状都是矫揉造作的,时常可以见到敷泥的截除部位,或者像绑着绷带的受伤手臂那样扭曲的树枝。我们被带去看望园丁,那位统治着古怪花园的居心不良的天才。粗壮的老枞树长得不超过三十厘米,我们还看到矮小的橘树,枝头挂满小得如金色谷粒般的橘子。
我们还游览过壮美的石林。岩石有的伸长如整根钢针,有的翻腾起伏如凝然不动的海涛。我们得知,这种观赏怪石的爱好,已有许多世纪之久。古城的广场上装饰着许多外形令人费解的巨石。古代地方官员要向皇帝进贡时,就派人送去几块这种巨石。这种庞大的贡品由上百名奴隶推着走数千公里路,需要几年才能送抵北京。
我觉得中国并不神秘。相反,我甚至在它冲天的革命干劲中看出它是一个已经建立了几千年的国家,而且永远在巩固,在改进管理。它是一座巨塔,普通民众和传奇人物、武士、农民、极受崇拜的人物等在其古老的结构间轮番出现并消失。这里没有任何自发的东西,要是有人想到各处寻找朴拙的民间小艺术品,即那种不按透视原理制作而又往往接近于奇迹的艺术品,那是白费气力。中国的小玩偶:陶瓷娃娃、石雕娃娃,木刻娃娃,都是按上千年的模式复制的。一切事物都有按同一精美标准进行复制的印记。
我在农村集市上见到一种用细竹条编成的小蝉笼,感到万分惊奇。它妙就妙在按建筑学的准确度把一只笼子安在另一只上方,每只笼子里都装一只捉来的蝉,直至形成一座一米高的城堡。看着那连接竹条的一个个结和竹茎上的嫩绿色,我觉得具有能创造奇迹的天真品格的人民的手,已经恢复了活力。农民们看出我的赞叹之意,不想把那发出响声的城堡卖给我,他们要赠送给我。在中国腹地,宗教仪式般单调的蝉鸣就这样陪伴了我好几周。记得只有在童年时代,我才收到过如此难忘如此质朴的礼物。
我们乘坐一艘运载上千名旅客的轮船,开始沿长江旅行。船上旅客都是富有活力的农民、工人、渔夫。这条烟波浩渺的大河,帆桁如织,劳务繁忙,千千万万生灵、忧虑和梦想往来穿梭其中,我们沿河朝南京方向航行了好几天。这条河是中国的主干道。这条非常宽阔平静的长江,有的地方变得很狭窄,行船艰险万分,如同通过巨人的喉咙。两岸高耸的峭壁几可摩天,天空中不时出现一小片云彩,像是用毛笔娴熟地抹上去一般;在断崖峭壁间,有时隐约可见一间小屋。
这美得教人透不过气来的景色,人间少有,也许只有艰险难行的高加索隘道或我们荒凉静穆的麦哲伦海峡可与之媲美。
我发觉,在我远离中国的五年间,这里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随着这次深入这个国家,这种变化更为显著。
这种印象开始时是模糊的。在大街小巷,在人们身上,我能看出什么变化呢?啊,我发现蓝色不见了。五年前,在同一季节里我游览了中国的街道,那里永远挤满朝气蓬勃的人群。而当时不分男女老少,人人都穿蓝色工作服——一种用斜纹布或薄棉布做的工作服。我很喜欢这种不同色调的蓝色简便服装。看着无数蓝点穿过大街小巷,是很美的景观。
现在这种情况变了。发生什么事了?
只不过在这五年里,纺织工业已经发展到能够让千千万万中国妇女穿上用各种颜色,各种花卉、条纹、点的图案印的料子和各种绸缎制作的服装;甚至也可以让千千万万中国男人穿上其他颜色和质地更好的料子。
现在,许多街道已经变成一道道具有中国高雅情趣的美妙彩虹,这个民族根本不会造出任何丑陋的东西,这个国家连最原始的草鞋,都像是稻草制作的花朵。
沿长江航行时,我觉出了古老的中国画的真实性。在长江,隘道高处一株小塔似的盘曲松树,立刻使我想起富于想象力的古代版画。比凌驾于长江之上的这些隘道更不真实,更富于幻想色彩,更出人意料的地方实不多见,它们高入云霄,令人惊异,而在任何一处岩石裂缝间都会出现非凡人民年代久远的踪迹,五六米宽新种的植被,或是供人观赏,引人遐想的有五层顶的小庙。在更高处,在光秃秃的巉岩顶上,我们仿佛见到古老神话中描述的那种如纱如雾的烟气;那正是世上绝顶聪明的极老的微型画画家描画过无数次的云彩和应景的飞鸟。一首隽永的诗便产生于这种壮丽的自然景色;一首白描的短诗有如鸟的疾飞,又如岩壁间近乎静止地流淌着的河水发出的银白色闪光。
不过,这种景色中最奇特的莫过于看到在小方格里、在岩石间的小绿块里劳动的人。在极高处,在壁立的岩石之巅,一个褶皱里只要有点儿生长植物的土壤,就有中国人在那里耕种。中国的大地母亲是广阔而坚硬的。她训练并塑造了这里的人,使之变成不知疲劳的、细致的、坚韧的劳动者。辽阔的土地,人的非凡劳动,一切不公正现象的逐步消除,这三者的结合一定能促进中国人美好、宽厚而深挚的人性兴旺发展。
我在一九二八年到过香港和上海。当时中国处在殖民者的铁蹄之下;是赌棍、鸦片烟鬼、妓院、夜间出没的盗贼、假俄国公爵夫人、海陆强盗等的天堂。在这两个大都会的银行大楼前面,八九艘灰色装甲舰的出现,暴露了危险和恐惧,暴露了殖民者的掠夺,暴露了一个开始散发死亡臭味的世界的垂死挣扎。得到卑鄙的领事们的准许,中国和马来罪犯的海盗船上飘扬着许多国家的国旗。妓院附属于国际公司。有一次我受到了袭击,他们剥去我的衣服,抢光了我的钱,把我扔在中国的一条街上。
当我来到革命的中国时,这些记忆全都浮现在我脑海里。这已是一个崭新的国家,其道德之纯洁令人惊奇。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在广大土地上胜利地发生了变化。无数实验在全国各地开始进行。封建农业就要经历一场变革。道德风气如旋风过后般透明。
在重庆,我的中国朋友带我到该市的桥上去。我一生都爱桥。我父亲是铁路工人,他使我对桥产生莫大的敬意。领我观览大桥的中国朋友的热情,远远超过我的腿脚的承受能力。他们让我登上高塔,又让我爬到桥下低处,去观看奔流了几千年的那条河,今天,这条河被这件几公里长的钢铁作品跨越了。一列列火车将从铁轨上通过;公路路面供自行车骑行,大道供人步行。如此雄伟的景观把我镇住了。
晚上,艾青带我们到一家餐馆去吃饭,这是一家极具传统烹饪特色的老字号;我们品尝了樱桃肉、麻辣明笋丝、松花蛋、鱼唇。中国烹饪在其复杂性、惊人的品种、离奇的创造、不可思议的形式等方面,都不是笔墨所能描述的。艾青给了我们一些指点。一道美味必须达到的最高标准有三:色、香,味,三者均极重要。味道须鲜美,香味须浓郁,颜色须鲜艳和谐。艾青说:“我们用餐的这家餐馆又添了一项绝妙的特点:声响。”一个大瓷盘四周摆一圈菜肴,在最后一刻才加上一道小虾尾浇汁,倒到一块烧红的铁板上,使之发出一种吹笛似的悦耳声音——以同样方式一再重复的一个乐句。
在北京,我们受到丁玲的接见,她是被指派接待若热·亚马多和我的作家协会负责人。我们的老朋友诗人萧三及其德国妻子也在场,后者是位摄影家。一切都显得欢乐愉快。我们在开阔的人工湖的荷花之间泛舟,这个湖本是修造来供末代皇后游乐的。我们参观了工厂、出版社、博物馆和宝塔。我们在皇族后裔经营的一家世界上最专一的餐馆(专一得只有一张餐桌)里吃过饭。
(摘自《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4月版,定价:49.5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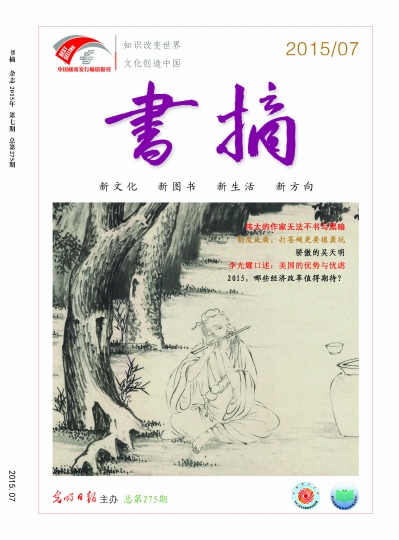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