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车辐一生,写、吃、玩、唱,四字可以概括完毕。我观其人,应是天上星宿下凡,游戏人间,还要饱享太太贤惠儿女孝顺之福,令人羡慕。
车辐先生年轻时乃是成都名记者,又任中华全国抗敌文协成都分会理事。我读小学,在报章上看见先生大名。读初中时想长大当新闻记者,也是由于看了先生写的《黑钱大盗李健》一文。后来成年,有幸与先生共事于四川省文联《四川群众》编辑部。时值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先生已入中年,穿一身褪色的灰制服,骑一辆脱漆的莱里车,用一支老式的派克笔,抽一包廉价的大前门,小心谨慎,沉默寡言。编辑部里尽是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青年,“思想觉悟”高得吓人,都把先生当做“旧社会”看待,时时警惕着他。他若不谨慎不寡言,便要挨批评做检讨。我头脑虽亦左,但好学,知他腹笥充盈,见闻广博,所以常去坐守他的桌前请教,听些文化掌故以及旧社会龙门阵。先生平时假小心装沉默,遇上我这样虔诚的听众,很快就现真相显本色,高谈阔论,毫无避忌。此时才晓得先生原来是胸无城府、绝不设防的人。四十多年后,我给他定性为“不可救药的老天真”,可见其为人之一贯如此,亦可推想他在旧社会时早已如此。
在编辑部,先生的办公桌左端靠窗,桌旁壁上挂一件晴雨计。他每日骑车上下班,关心天气变化。桌上大玻璃板,压有一九三六年谒鲁迅墓的照片和他手书的迅翁七绝一首:“大江日夜向东流,聚义群雄又远游。六代绮罗成旧梦,石头城上月如钩。”还压有老画报剪下的电影明星蓝苹(江青)的剧照。左壁上有一幅成都市大地图,谁都不去查看。唯有先生每星期一上早班时总要用笔在地图上划些符号。他说:“昨天去看东郊建设,这里新修了一条路,我来添上。”每逢星期一,他都要添划一些符号,表示工厂、桥梁、道路、医院、仓库等等。他哪知“阴暗的眼睛到处看见敌人”,竟将东郊一片划满各种符号,而竟浑浑噩噩不知祸之将至。有两个星期日,还带我去东郊看建设,一一指点,满怀豪情称颂不已。那时东郊沙河电影院尚未修,正在挖基坑打基础,我和他就坐在离基址不远处喝茶畅谈。谈完建设,他凝眸附近一座农家院,土墙竹林围绕,状甚一般,忽指点说:“日本飞机轰炸成都,我到这座院子躲过警报。”八年抗战的艰难岁月又从记忆里浮现出来。
在旧社会吃新闻饭,先生敬业十分,成名绝非浪得。衣袋内揣一个小本本,遇到一鳞半爪,立刻记下,以备采访之用。为人又好事,喜交游,管他三教九流,一混就熟。所以出去采访,每每旗开得胜,短消息,长特写,莫不精彩可读。脚板又翻得勤,车子又蹬得快,总是抢在同行之前,先拿到手。人勤快,饿得快,凡吃请,他都来。官方开新闻招待会,他也去坐头排,意在桌上摆的蛋糕点心罢了。成都餐宴行业几位巨擘有一个转转会,轮流请吃,他也每次跑去赶斋,大饱口腹,吃过许多稀奇古怪的极品佳肴。如今老了,轮椅岁月无聊,便一一写出来,还印成书,叫拙荆给他作跋。这类文章只要几篇,已足逗得读者食指大动,还给他招来了美食家的头衔,真是合算。我曾问他:“既是吃转转会,你就光吃不请?”他不好意思,说:“我也请他们来吃过牛肉碎臊烩凉粉。”此品花钱最少。巨擘们谅解他,新闻记者穷嘛。他到处吃请。未请他,也去吃。重庆杨钟岫年轻时去拜见他,时届中午,他问:还没吃吧?杨答未吃。他便带着杨去撷英餐厅,赴某家的婚宴。食毕出来,杨问主人是谁?他说:“不认识,白吃的。”杨大惊,不敢再开这样大的玩笑。他却泰然一笑,真是名士风流大不拘啊。
说到这转转会,又与扬琴有关系了。转转会的几位东家,其一姓蓝,是包席馆子荣乐园的老板,同车辐先生一样,都是打唱扬琴的票友,所以拉他去吃。其余各个东家也都知悉这位记者,乐意邀他赶宴白吃。他们吃毕,就要打唱扬琴玩了。车辐先生曾随扬琴大师李德才游,能打会唱。又靠一些古典诗词垫底,唱起来就有更深沉更细致的理解和感受,往往比肩专业人士。此种专业多系盲人,一如古之师旷,因目盲而耳灵,辨音识声优于睁眼仔。这些盲音乐家尽是贫民,地位低下。车辐先生敬爱他们,常与之游。此种异行不被世俗认同,称他为车老疯。你,一个文化人,大记者,有身份,跑来交游一伙穷瞎子,故称之曰疯。所以,疯在这里仅指性情,非指精神疾患。从前先生年轻,每见这些盲音乐家横过街道,便去搀扶。他们握一握他的手,便知晓这来者是谁了,问一句:“又是老疯吗?”不但扬琴艺人,那时各种民间曲艺人士,先生都去交游,结下友谊。十几年后,我和他拉车子街上走,背心短裤,满脸汗尘,仍有那么多曲艺界乃至川剧界的老朋友向他鞠躬问好,叫一声车老师。回想起来,他不是不拿架子,而是浑然忘却所谓身份高低,出乎真情,友爱他人。他曾引川戏唱词“好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以教我。当时我二人正在服苦役,印象特深,至今尚不敢忘。
说到交友,先生还有一群文化朋友,都是抗日战争时期来成都的,计有作家、报人、画家、演员各类,其数上百,后来多半成名,举国皆知。数十年后,他们到了成都,必来看他,音樽话旧,使人感动。回头瞧瞧从前那些蹋躞过他的人,如今一个个的门可罗雀,便知天理昭昭,善有善报。
我和先生不是朋友关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出第一部诗集时,送他那本上面写的就是“车辐吾师指教”。我戴上帽子后,承蒙先生不弃,乐意助我拉车,绝无恶语半句。派来助我拉车的人多矣,唯先生最卖力。较之某位学者,绳子从未拉伸,还要做脸做色,而为人之孰优孰劣,犁然自见。帽子戴二十年摘了后,又是先生骑车远道前来故乡看我,回去又写采访发表。近二十年,拙作被他青睐,又说些好言语鼓励我,始终不认我做学生。相反,颠三倒四呼拙荆为师母。此老身上原有帅克的诙谐与狡黠,晃眼一看,容易被误认为半瓜精。其实不是。
先生的趣闻,确实也不少。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他家中子女多。他说他太太是航空母舰,上面停了八架飞机,却不说飞机是谁制造的。工资不够应付家庭开支,他就翻出郭沫若给他的三封信,卖给公家,获二百元(相当于今日的四千元),自称“出卖郭老”。一九五五年反胡风运动来势极凶猛,他吓慌了,赶快交出抗日时期胡风来信两封。事后又遗憾没有卖到钱,多次说起。也就是这一年,大祸突降,被捕入狱。起初怕枪毙,吓得睡不着。三天后打听到同狱的“反革命”多达数百人,皆属省级机关干部,他就吃了定心汤圆,放胆做体操,能吃能睡了。送回省文联,红光满面,还长胖了。补领十一个月工资,大喜过望,买酒痛饮,而且赋诗。记得其中两句,一是“灵魂已压扁”,一是“一身肥尕尕”。想当初逮他,编辑部领导人指着壁上地图,拍桌大叫:“看这罪证!”送回来后,他才弄明白,自己被误认为“特务”了。从此再不提说东郊看建设,姑且偷着乐吧。一九五七年上头叫“鸣放”,他就设防,一声嗽也不咳,总算未上“引蛇出洞”的当。经此一吓,不敢再有趣闻,天天“夹住尾巴”。八十岁后,老还小,趣闻又回来。数举四例,以博一粲。一是红袍礼帽,扮新郎官过瘾;二是接受陈若曦啵他左脸,假作亲爱;三是当着黄苗子的面,赖倒在郁风怀里,放嗲装小;四是为女艺人哭灵,大放悲号。以上“失格”之举,全有多人旁证,而且照相留影。
纵观车辐一生,写、吃、玩、唱,四字可以概括完毕。倒起说吧。唱,除了扬琴,他还会唱川戏,快活时放几腔,还听得。玩,一是游山玩水,二是跳交际舞,三是高台跳水,皆能超乎常人,玩得心跳。近年老迈,跳舞跳水不可能了,唯山水之游玩,念念不忘,坐在轮椅上还想出夔门,看上海,耍南京,约我明年同去。吃,到老还馋。其言曰:“除了钉子,都能嚼碎。”夫妻肺片双份吃光,轮椅推上街,还要买两个蛋卷冰淇淋,边行边吃。一夜拙荆去他家,回来说:“看电视睡着了,手上还拿着半边桃酥,醒来再吃。”我观其人,应是天上星宿下凡,游戏人间,还要饱享太太贤惠儿女孝顺之福,令人羡慕。最后是写,写了一生,轮椅上还天天写信。拿太太的话说:“我就是不会写。除写以外,哪样都比他强,还绷啥名人嘛。”
(摘自《晚窗偷得读书灯》,新星出版社2015年1月版,定价:3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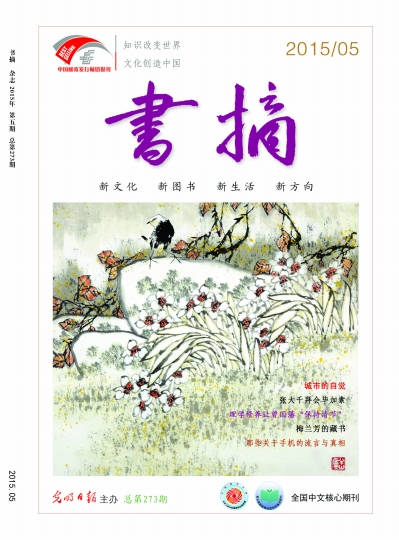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